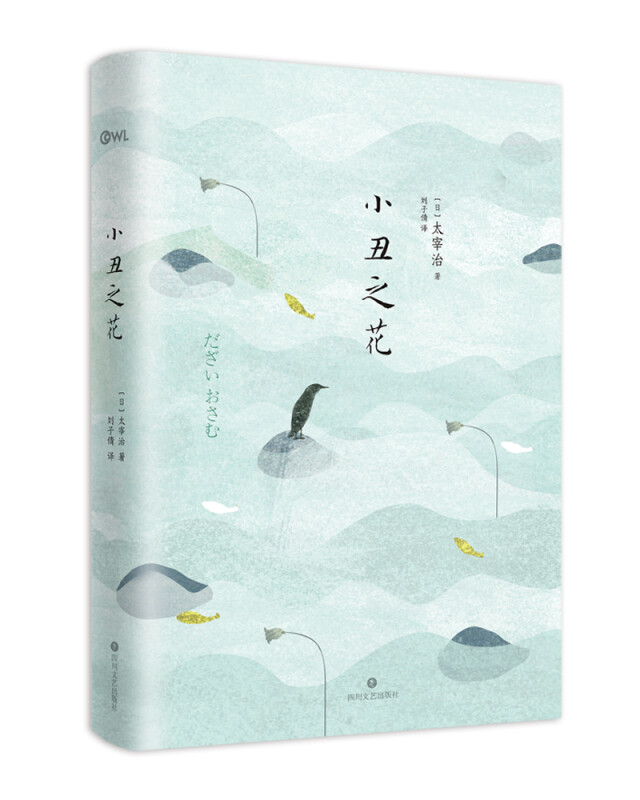
5分
包邮小丑之花
《人间失格》前传,太宰治“人生三部曲” 之一,呈现一个年轻、冲动又骄傲的大庭叶藏。

- ISBN:9787541146183
- 装帧:精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288
- 出版时间:2017-06-01
- 条形码:9787541146183 ; 978-7-5411-4618-3
本书特色
太宰治“人生三部曲”
《人间失格》前传,
带你重新认识太宰治
“我打从骨子里是个小天真。唯有在天真中,我得以暂时休憩。”——太宰治
太宰治以其自杀经历,向读者剖析真正的自我
全新译文,精装珍藏版,
专属颜色文艺刷边
读了这本书,才能读懂《人间失格》
“我正因不愿被人批评,才会率先往自己身上插钉子” ——太宰治
内容简介
太宰治二十一岁时,在银座咖啡馆认识一有夫之妇,同居三天后,他俩吞下安眠药,在鎌仓投水自杀。结果太宰治获救,年仅十八岁的女方死亡。太宰治因而被控“帮助自杀罪”,后虽被判不予起诉,但他基于相约殉情却让女人独自死亡的罪恶意识,创作了《小丑之花》。
n
《小丑之花》主角大庭叶藏与《人间失格》主角同名,描写的是叶藏殉情失败后进疗养院的事,但不同于《人间失格》中叶藏的自卑、怯懦、颓废,《小丑之花》里的的叶藏,年轻、冲动又骄傲。太宰治在这篇作品里,剖析了他日后的之作《人间失格》里看似消极颓废,实际上却在绝境中求活的主角大庭叶藏的心路历程,还透露了许多关于写作的秘密。
另收录有太宰治记录镰仓自缢未遂经历的《狂言之神》;
与《小丑之花》《狂言之神》同属“虛構的徬徨”三部曲的《虚构之春》;
届芥川奖入围作品《逆行》;
及《他已非昔日之他》。
目录
逆行
他已非昔日之他
狂言之神
虚构之春
节选
小丑之花 “过了此处便是悲伤之城。” 朋友全都远离我,以悲伤的眼神望着我。吾友啊,与我说话,嘲笑我吧。啊啊,友人空虚地撇开脸。吾友啊,质问我吧。我什么都会告诉你。是我用这只手,将阿园沉入水中。我以恶魔的傲慢,祈求着当我复活时阿园死去。还要我说更多吗?啊啊,但是吾友,只是以悲伤的眼神望着我。
大庭叶藏坐在床上,望着海上。海上烟雨蒙蒙。
自梦中醒来,我重读这几行,那种丑陋与猥亵,让我很想删除。算了算了,太过夸张。先不说别的,大庭叶藏算怎么回事。不是酒,是被更强烈的东西醉倒,我要为这大庭叶藏拍手。这个姓名,非常适合我的主角。大庭,恰好将象征主角非比寻常的气魄表露无遗。叶藏,又是何等新鲜。令人感到一种自陈旧底层涌现的真正的崭新。还有,“大庭叶藏”这四字排列起来的这种爽快协调!光是这个姓名,不已是划时代的创举吗?这样的大庭叶藏,坐在床上眺望烟雨蒙蒙的海上。这岂不更有划时代性?
算了。嘲讽自己是卑劣之举。那似乎来自痛苦受挫的自尊心。就像我,正因不愿被人批评,才会率先往自己身上插钉子。这才是卑怯。我必须更坦诚才行。啊啊,要谦让。
大庭叶藏。
就算被嘲笑也无可奈何。东施效颦。洞察者亦会为人洞察。想必也有更好的姓名,但对我而言似乎有点麻烦。索性就写“我”亦无不可,但这个春天,我才刚写过以“我”为主角的小说,所以连续两篇都这样也不大好。说不定,当我明日猝死时,会冒出一个奇妙的男子扬扬得意地声称:那家伙如果不用“我”为主角,就写不成小说。其实,仅仅只因这样的理由,我还是决定就用“大庭叶藏”这个名字。可笑吗?少来,你不也是。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青松园这间海滨疗养院,因叶藏的入院,掀起小小的骚动。青松园有三十六名肺结核病人。包括两名重症患者,以及十一名轻症患者,另外二十三人正处于恢复期。叶藏住的东**栋病房楼,算是特等住院区,共分为六间病房。叶藏这间的两邻都是空房间,*西边的六号房,住的是身材高、鼻子也高的大学生。东边的一号房与二号房,各住了一名年轻女子。这三人都是恢复期的病人。前一晚,有人在袂浦殉情自杀。明明是一起跳海,男人却被返航的渔船救起,保住一命。但女人,却未找到。为了搜寻那个女人,警钟刺耳地响了很久,村中的大批消防队员跳上一艘接一艘的渔船驶向海上时发出的吆喝声,听得三人心惊胆战。渔船点亮的红色火影,终夜在江之岛的岸边徘徊。大学生和两名年轻女子,那晚都彻夜难眠。直到黎明,人们终于在袂浦的岸边发现女人的尸体。理得很短的头发闪闪发亮,脸孔惨白浮肿。
叶藏知道阿园死了。早在被渔船缓缓送回时,他就已知道了。当他在星空下醒来,首先就问道:女人死了吗?一名渔夫回答:没死,没死,你放心好了。语气听来异常慈悲。原来她死了啊。他失神地想,然后再次昏迷。再次醒来时,已在疗养院中。白色壁板环绕的狭仄房间中,挤满了人。其中有人问起叶藏的身份。叶藏一一清楚回答。天亮后,叶藏被移往另一间宽敞的病房。因为叶藏的家乡接到消息后,为了好好处置他,特地打了长途电话到青松园。叶藏的家乡,远在二百里外。
东**栋病房楼的三名病人,对这个新病人就躺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感到不可思议的满足,他们对今后的医院生活怀抱期待,在天空与海面都泛白时终于睡着了。
叶藏没睡。他不时微微晃动脑袋。脸上到处贴着白色纱布。他被海浪卷起、撞上礁岩时弄伤了全身。名叫真野,年约二十的护士独自照顾他。她的左眼眼皮上方,有道略深的伤痕,因此比起另一只眼,左眼显得较大。不过,并不难看。她的红色上唇不自觉噘起,脸颊浅黑。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正望着阴霾的海面。她努力不看叶藏的脸,是觉得太可怜了不忍心看。
接近正午,两名警察来探视叶藏。真野离席避开。
两人都是穿西装的绅士。其中一人留着小胡子,另一人戴副铁框眼镜。小胡子低声询问他与阿园的关系。叶藏照实回答。小胡子在小记事本上写下。该问的都问过后,小胡子像要覆盖病床似的俯身说:“女人死了。你当时有寻死的意图吗?”
叶藏没吭气。戴铁框眼镜的刑警,肥厚的额头挤出两三条皱纹,露出微笑,拍拍小胡子的肩。
“算了,算了。怪可怜的,改天再说吧。”小胡子直视叶藏的眼睛,不情不愿地把记事本收回到外套的口袋。刑警们离去后,真野急忙返回叶藏的病房。但是,一开门,便看到呜咽的叶藏。她轻轻把门又关上,在走廊伫立片刻。
到了下午开始下雨。叶藏已恢复到足以独自去上厕所。
他的友人飞騨穿着濡湿的外套,冲进病房。叶藏装睡。飞騨小声问真野:
“他没事吧?”
“对,已经没事了。”
“吓我一跳。”
他扭动肥胖的身体脱下那件充满黏土臭味的外套,交给真野。
飞騨是个默默无名的雕刻家,他与同样默默无名的西画画家叶藏,自中学时代便结为好友。若是心灵诚实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把身边某人当成偶像崇拜,飞騨亦是如此。他一进中学,就憧憬地看着班上**名的学生。**名就是叶藏。叶藏在课间的一颦一笑,对飞騨而言,都非同小可。而且,当他在校园的沙堆后发现叶藏孤独老成的身影,不禁发出不为人知的深深叹息。啊啊,还有他与叶藏**次交谈那天的欢喜。飞騨样样都模仿叶藏,抽烟、嘲笑老师。双手在脑后交抱,摇摇晃晃走过校园的走路方式也是跟叶藏学的。他也知道艺术家为何*了不起。叶藏进了美术学校。飞騨在一年后,也设法与叶藏进了同一所美术学校。叶藏专攻西画,飞騨就故意选了雕塑科。他声称是因为被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所感动,但那只是他成为大师后,为了让经历看起来稍微像样一点才刻意捏造的说法,其实是对叶藏选择西画的顾忌,是出于自卑。到了那时,两人终于开始分道扬镳。叶藏的身子越来越瘦,飞騨却渐渐变胖。两人的差距不止如此。叶藏被某种直接的哲学吸引,很瞧不起艺术。而飞騨,却有点太过得意。他频频把艺术挂在嘴上,反倒让听的人都觉得尴尬。他不断梦想创造杰作,却怠于学习。就这样,两人都以不太好的成绩自学校毕业。叶藏几乎已丢下画笔。他说绘画只能用来画画海报,令飞騨很沮丧。一切艺术都是社会经济结构放的屁,只不过是生产力的一种形式。再好的杰作都和袜子一样,只是商品。诸如此类,他危险的口吻弄得飞騨一头雾水。飞騨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叶藏,哪怕是对叶藏近来的思想,他也怀有一种隐约的敬畏。但对飞騨而言,杰作带来的刺激比什么都重要。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他一边这么想,一边毛毛躁躁地玩黏土。换言之,两人与其被称为艺术家,不如说是艺术品。不,正因如此,我才能这样轻易叙述吧。如果看过真正的市场上的艺术家,各位恐怕读不到三行就要吐了。这点我敢保证。话说,你要不要写写看那样的小说?如何?
飞騨也不忍看叶藏的脸。他尽量灵巧地蹑足走近叶藏的枕畔,却只是认真眺望玻璃窗外的雨势。
叶藏睁眼浅笑,说道:“你吓到了吧?”
他大吃一惊,瞄了叶藏一眼,立刻垂眼回答:“嗯。”
“你怎么知道的?”
飞騨迟疑。从长裤口袋抽出右手抚摩自己那张大脸,以眼神悄悄向真野示意:能说吗?真野一本正经地微微摇头。
“消息上报纸了?”
“嗯。”其实,他是听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得知的。
叶藏对飞騨含糊暧昧的态度很不满。他觉得对方应该坦诚一点。一夜过后,就翻脸不认人,把我当成外人对待的这个十年老友太可恨了。叶藏再度装睡。
飞騨无所事事地用拖鞋在地板弄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在叶藏的枕畔站立片刻。
门无声开启,一名身穿制服的矮小大学生,倏然露出俊美的脸孔。飞騨发现后,呻吟着松了一口气。他一边撇嘴赶走爬上脸颊的微笑,一边故意慢吞吞地走向门口。
“你刚到?”
“对。”小菅一边留意叶藏那边,一边干咳着回答。
此人名叫小菅。他与叶藏是亲戚,正在大学就读法科,与叶藏相差三岁,即便如此,还是好友。现代青年似乎不怎么在乎年龄。学校放寒假他本已返乡去了,得知叶藏的事,又急忙搭急行列车赶回来。两人到走廊站着说话。
“你沾了煤灰。”
飞騨公然咯咯笑,指着小菅的鼻子下方。那里浅浅沾附了一些火车的煤烟。
“是吗?”小菅慌忙从胸前口袋掏出手帕,立刻擦拭鼻子下方,“怎样?现在情况如何?”
“你说大庭?好像没事了。”
“这样啊——冷静下来了啊。”小菅抿唇猛然伸长人中给飞騨看。
“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了。家里可是鸡飞狗跳吧?”
“嗯,鸡飞狗跳,像丧礼一样。”小菅边把手帕塞回胸前口袋边回答。
“家里有谁要来?”
“他哥哥要来。他老爹说,不管他。”
“看来闹大了。”飞騨一手撑着窄短的额头嘀咕。
“阿叶真的没事吗?”
“他倒是意外镇定。那小子,每次都这样。”
“不知他是何心情。”小菅像是很兴奋似的嘴角含笑把头一歪。
“不知道——你不见见大庭吗?”
“算了。就算见了,也无话可说,况且——我害怕。”
两人低声笑了起来。
真野自病房出来。
“房间里都听见了。请你们别在这儿聊天。”
“啊,那真是……”飞騨不胜惶恐,拼命把大块头缩得小小的。小菅不可思议地窥视真野的脸。
“两位,那个,午饭吃了吗?”
“还没!”两人一同回答。
真野红着脸忍俊不禁。
三人一同去了餐厅后,叶藏起来了。所以才会望着烟雨蒙蒙的海上。
“过了此处便是空蒙之渊。”
然后又回到*初写的开头。好吧,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差劲。首先,我就不喜欢这种时间上的安排。虽然不喜欢还是尝试了一下。“过了此处便是悲伤之城。”因为我想把这句平常朗朗上口的地狱之门的咏叹词,放在光荣的开篇**行。没别的理由。纵使因为这一行,把我的小说搞砸了,我也不会软弱地予以抹杀。顺便再打肿脸充胖子地说一句,要删除那一行,就等于磨灭我到今天为止的生活。 “是因为思想啦,我告诉你,是马克思主义害的啦。”
这句话很蠢,不错。小菅就是这么说的。他满脸得意地说着,又端起牛奶杯。四面贴着木板的墙上,涂了白漆,东边墙上,高挂着院长在胸前佩戴三枚硬币大小勋章的肖像画。十张细长的桌子在下方悄然并列。食堂空荡荡。飞騨与小菅坐在东南角的桌子旁,正在用餐。
“他之前闹得可凶了。”小菅压低嗓门说,“那么弱的身子,居然还那样四处奔走,难怪会想死。”
“他是学运行动队的带头者吧?我知道。”飞騨默默咀嚼面包插嘴说。飞騨不是在炫耀博学。区区一个左派的用语,这年头的青年人人皆知,“不过——不只是因为那样。艺术家可没那么简单。”
食堂暗下来了。雨势增强。
小菅喝了一口牛奶说:“你只知以主观看待事物,所以才没用。基本上——我是说基本上,一个人的自杀,据说往往潜藏着那个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客观上的重大原因。在家里,大家都认定这次的事是女人害的,但我说并非如此。女人,只是陪他共赴黄泉。另有重大原因。家里那些人不明就里。连你都胡说八道。这可不行喔。”
飞騨凝视脚下燃烧的炉火呢喃:“可是,那个女人,另有丈夫。”
小菅把牛奶杯放下回答:“我知道。那种事,没啥了不得。对阿叶来说,屁都不算。因为女人有老公就殉情,那未免也太天真了吧。”说完,他闭起一只眼瞄准头顶上的肖像画,“这人是这里的院长吗?”
“应该是吧。不过——真相,只有大庭才明白。”
“那倒也是。”小菅随口同意,瞪着眼东张西望,“怪冷的呢。你今天要在这里住下吗?”
飞騨急忙吞下面包,点头说:“要住下。”
青年们从来不认真议论。他们尽*大努力小心不触犯对方的神经,也小心保护自己的神经。他们不想平白受辱。而且,一旦受伤,总是钻牛角尖地认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他们讨厌斗争。他们知道很多敷衍之词。就连一个否定,起码都有十种不同的使用方法。还没开始议论,已经先交换妥协的眼色了。*后一边笑着握手,一边彼此却都在暗自嘀咕:猪脑袋!
话说,我的小说,好像也终于开始糊涂了。在此一转,展开全景式的多线并行吧。不用说大话。反正不管让你做什么都一样无能。啊啊,但愿一切顺利。 翌晨,天气晴朗。海上风平浪静,大岛火山喷发的浓烟,在水平线上形成白色雾霭。不好。我讨厌描写景色。
一号房的病人醒来时,病房里弥漫着初冬的暖阳。她与陪伴的护士互道早安,立刻测量晨间体温。三十六度四。然后,去阳台做餐前的日光浴。早在护士轻戳她的腰暗示之前,她已在偷窥四号房的阳台了。昨天的新病人,规矩穿着藏青碎白花纹的和服坐在藤椅上,正在看海。只见那人仿佛觉得刺眼似的蹙起浓眉,脸色似乎不太好看。不时还拿手背轻拍脸颊的纱布。她躺在日光浴用的卧榻上,微睁双眼专心观察后,让护士拿书来。《包法利夫人》,平时觉得这本书很无聊,看个五六页就扔开了,今天却想认真一读。现在,看这本书,似乎非常适合。她随手翻阅,自一百页的地方开始读。恰好看到这么一行:“埃玛想在火把的光亮下,在半夜出嫁。”
二号房的病人也醒了。她去阳台做日光浴,蓦然看到叶藏的身影,又跑回病房。莫名地恐惧,立刻钻进被窝。陪伴她的母亲,笑着替她盖上毯子。二号房的女病人,把毯子拉到头上罩住,在那小小的黑暗中两眼发亮,倾听邻室的说话声。
“好像是美人哟。”然后是低低的笑声。
飞騨与小菅昨晚留下过夜。两人在隔壁的空病房睡在同一张床上。小菅先醒来,勉强睁开细长的眼睛,起身去阳台。斜眼瞄了一下叶藏有点做作的姿势,为了寻找他摆出那种姿势的原因,把头向左一扭。只见*旁边的阳台有个年轻女人在看书。女人的卧榻背后,是长满青苔的潮湿石墙。小菅像西洋人那样耸耸肩,立刻转身回病房,摇醒睡觉的飞騨。
“快起来,有情况!”他们*喜欢捏造情况,“看阿叶的大姿势。”
他们的对话中经常使用“大”这个形容词。或许是渴望在这无聊的世间,获得某种足以期待的对象。
飞騨吓得跳起来:“怎么了?”小菅笑着告诉他:
“有个少女。阿叶在对人家展现他*得意的侧脸。”
飞騨也开始兴奋起来,两边眉毛夸张地猛然挑起问道:“是美人儿吗?”
“好像是美人喔,正在假装看书。”飞騨喷笑。坐在床上,穿上夹克,套上长裤后,高叫:
“好,看我狠狠教训他!”其实他无意教训人。这只是背后说坏话。他们连好友的坏话都照说不误。完全是看当时的情况胡闹,“大庭这小子,全世界的女人他都要。”
过了一会儿,叶藏的病房冒出响亮的笑声,响彻整栋病房大楼。一号房的病人啪地合起书本,狐疑地眺望叶藏的阳台那边。阳台只剩下一把在晨光中发亮的白色藤椅,空无一人。她凝视那把藤椅,昏昏沉沉打起瞌睡。二号房的病人听到笑声,蓦然自毯子露出头,与站在枕边的母亲交换一个温和的微笑。六号房的大学生,被笑声吵醒了。大学生没有人陪在身边照顾,就像住在宿舍一样悠哉。察觉笑声来自昨天那个新病人的房间,大学生黝黑的脸孔倏然涨红。他并不觉得笑声不敬,基于恢复期患者特有的宽大心胸,不如说是为叶藏的活力感到安心。
我该不会是三流作家吧。看样子,好像太自恋了。毫无自知之明地妄图什么全景式多线发展,结果搞成这样矫揉造作。不,慢着。我早料到会有这样的失败,事先便准备了一句话。秉持美好的感情,人们创造出丑恶的文学。换言之,我如此自恋过度,也是因为我的心没那么邪恶。啊啊,祝福想出这句话的男人!这是多么珍贵的一句话。但是,作家穷其一生只能使用这句话一次。似乎真是如此。只用一次,是可爱。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把这句话当盾牌,你似乎只会变得窝囊。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太宰治 译者:刘子倩
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岛修治,出生于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町的知名仕绅之家。其父虽为贵族院议员,但太宰治却从未享受到来自财富或权势的种种好处。他一生立志文学,曾参加左翼运动,又酗酒、殉情,终其一生处于希望与悔恨的矛盾之中。在短暂的三十九年生命中,他创作了五十余部作品,包括《人间失格》《斜阳》等。曾五次自杀,*后一次是在一九四八年,和仰慕他的女读者在东京三鹰玉川上水投河自尽,结束其人生苦旅。
刘子倩,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系毕业,日本筑波大学社会学硕士,现为专职译者。译有《嫌疑人X的献身》《第八日的蝉》等作品。
-

莫言的奇奇怪怪故事集
¥22.2¥59.9 -

2025读书月阅读盲盒——我独钟意命运角落的人
¥42.3¥168.0 -

悉达多
¥14.3¥28.0 -

2025读书月阅读盲盒——经常作案的朋友都知道
¥42.3¥168.0 -

死魂灵
¥16.3¥48.0 -

本森小姐的甲虫
¥18.7¥55.0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14.7¥39.8 -

1984-插图珍藏版
¥11.3¥29.8 -

鼠疫
¥14.4¥38.8 -

失去一切的人
¥19.2¥52.0 -

罗生门
¥11.9¥36.0 -

重生
¥14.7¥39.8 -

烟与镜
¥17.8¥48.0 -

未来的最后一年
¥18.4¥49.8 -

生死场
¥10.4¥36.0 -

山海经
¥21.1¥68.0 -

若非此时,何时?
¥11.8¥42.0 -

小小小小的火
¥17.7¥52.0 -

月亮与六便士
¥12.9¥38.0 -

我是猫
¥15.2¥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