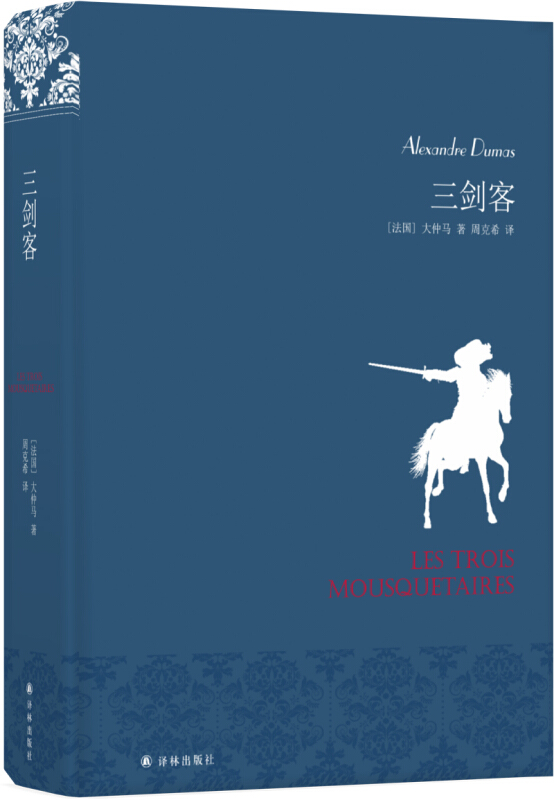
三剑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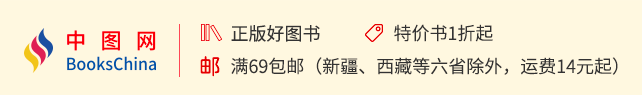
温馨提示:5折以下图书主要为出版社尾货,大部分为全新(有塑封/无塑封),个别图书品相8-9成新、切口有划线标记、光盘等附件不全详细品相说明>>
- ISBN:9787544773799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649
- 出版时间:2018-09-01
- 条形码:9787544773799 ; 978-7-5447-7379-9
本书特色
大仲马风靡世界的经典名作! 周克希先生全面校订本! 《三剑客》问世以来,流传着一句话:“如果此刻在某个荒岛上有个鲁滨逊,他也在读《三剑客》。”
内容简介
《三剑客》的故事发生在法王路易十三时代,红衣主教黎舍留权倾一时,宫廷内外的权力倾轧时时在上演。年轻的外省贵族子弟达德尼昂来到巴黎,投入火枪营统领特雷维尔先生的麾下,途中遇见火枪手阿托斯、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在一场冲突中结为生死之交。错综复杂的政治旋涡中,这四位伙伴遇到黎舍留的心腹密探——艳若桃李、毒如蛇蝎的女子米莱迪,双方反复较量,达德尼昂和伙伴们一次次绝处逢生,挫败了黎舍留的阴谋。
目录
译序
前言
**章 达德尼昂老爹的三件礼物
第二章 德.特雷维尔先生的前厅
第三章 晋见
第四章 阿托斯的肩膀,波尔多斯的肩带和阿拉密斯的手帕
第五章 国王的火枪手和主教先生的卫士
第六章 路易十三国王陛下
第七章 火枪手的家
第八章 宫里的一桩秘密
第九章 达德尼昂小试锋芒
第十章 十七世纪的捕鼠笼
第十一章 情节复杂起来了
第十二章 乔治?维利埃斯———白金汉公爵
第十三章 博纳修先生
第十四章 牟恩镇的那个人
第十五章 穿袍的人和佩剑的人
第十六章 在这一章中,掌玺大臣塞吉埃不止一次地又要像过去那样找钟来敲了
第十七章 博纳修夫妇
第十八章 情人与丈夫
第十九章 出征方案
第二十章 途中
第二十一章 德.温特伯爵夫人
第二十二章 梅尔莱松舞
第二十三章 幽会
第二十四章 小楼
第二十五章 波尔多斯
第二十六章 阿拉密斯的论文
第二十七章 阿托斯的妻子
第二十八章 回程
第二十九章 治装
第三十章 米莱迪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第三十二章 讼师家的午餐
第三十三章 侍女和女主人
第三十四章 在这一章中,阿拉密斯和波尔多斯的行装都解决了
第三十五章 夜里的猫都是灰色的
第三十六章 复仇之梦
第三十七章 米莱迪的秘密
第三十八章 阿托斯怎样毫不费事地治好了装
第三十九章 幻影
第四十章 红衣主教
第四十一章 拉罗谢尔围城战
第四十二章 安茹红葡萄酒
第四十三章 红鸽棚酒店
第四十四章 火炉烟囱管的用处
第四十五章 夫妻间的一幕
第四十六章 圣热尔韦棱堡
第四十七章 四个伙伴的密谈
第四十八章 家务事
第四十九章 劫数
第五十章 叔嫂间的谈话
第五十一章 长官
第五十二章 囚禁的**天
第五十三章 囚禁的第二天
第五十四章 囚禁的第三天
第五十五章 囚禁的第四天
第五十六章 囚禁的第五天
第五十七章 古典悲剧的表演手法
第五十八章 越狱
第五十九章 一六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在朴次茅斯发生的事情
第六十章 在法国
第六十一章 贝蒂纳的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
第六十二章 魔鬼的两个化身
第六十三章 一滴水
第六十四章 裹红披风的人
第六十五章 审判
第六十六章 行刑
第六十七章 结局
尾声
节选
第二十七章 阿托斯的妻子 “现在就剩阿托斯还下落不明,”达德尼昂对着精神焕发的阿拉密斯说,这会儿他已经把他们动身以后京城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阿拉密斯,而且一顿丰盛的晚餐已经让他俩一个忘了自己的论文,另一个忘了自己的疲乏。 “您难道还怕他会出什么意外?”阿拉密斯问道,“阿托斯是那么冷静,那么勇敢,剑术又那么出色。” “对,是这样,对阿托斯的勇气和灵巧,谁也不会比我更了解,可是我宁愿我的剑迎击的是长矛,而不是棍子;我就怕当时围着阿托斯打的都是些仆人,仆人下手又重,又爱把人往死里打。所以说实话,我想马上动身去找他,愈快愈好。” “尽管我这会儿恐怕还没法骑马,”阿拉密斯说,“可我要争取和您一起去。昨天我拿下您在墙上看见的那根苦鞭试了试,想用虔诚的苦修来治伤,可是实在疼得受不了,只好作罢。” “我这可是头一回听见有人要用苦鞭来治枪伤;不过您这会儿是在生病,脑子不管用,所以我也不怪您。” “您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天一亮就动身;今天晚上您好好休息,明天您要是能行,咱们就一起走。” “那就明天见吧,”阿拉密斯说,“您也需要休息,铁打的身子也得睡觉呐。” 第二天,达德尼昂走进阿拉密斯的房间,只见他站在窗前。 “您在那儿瞧什么呢?”达德尼昂问。 “嘿!马房伙计牵在手里的那三匹好马可真让人看了眼红;能骑着这样的骏马上路,可就像亲王一般风光喽。” “好,亲爱的阿拉密斯,您就风光风光吧,因为这中间有一匹就是您的。” “是吗!唔,哪一匹?” “这三匹里您想要哪匹都行:我反正都一样。” “上面那副贵重的马铠也是我的?” “没错。” “您在开玩笑,达德尼昂。” “您说法国话以后,我就不开玩笑了。” “这些包金的皮枪套,丝绒的鞍褥,嵌银的鞍子,都是给我的?” “它们是您的,正像这匹蹬着前蹄的马是您的,那匹打着转的马是阿托斯的一样。” “哟!这三匹马可都是百里挑一的好马。” “它们能让您中意,我感到很高兴。” “那这是国王给您的礼物喽?” “反正不是红衣主教给的,您就甭管它们是打哪儿来的,还是想想您爱挑哪一匹吧。” “我挑红头发伙计牵的那一匹。” “好极了!” “感谢天主!”阿拉密斯嚷道,“这一来我那点伤敢情也不会觉得疼了;哪怕挨上三十颗枪子儿,我也照样要骑在上面。哎!凭良心说,这副马镫真够漂亮的!嗬!巴赞,快过来,赶快!” 巴赞愁眉苦脸、没精打采地出现在门口。 “把我的剑擦擦亮,帽子弄弄挺,披风刷一下,手枪装上弹药!”阿拉密斯说。 “*后那句不用吩咐了,”达德尼昂插断他说,“马鞍的枪套里已经有两支上好弹药的手枪。” 巴赞叹了口气。 “得了,巴赞师傅,您放心,”达德尼昂说,“条条道路都能通到天国。” “我主人已经是个出色的神学家了!”巴赞说得几乎要哭出来了,“他会当上教区主教,说不定还会当上红衣主教的呀。” “呣,我可怜的巴赞,行啦,你想想看,当教士有什么好?还不是照样要去打仗;你也知道,红衣主教就要戴着头盔,拿着长戟去打仗了;还有那位诺加雷?德?拉瓦莱特,你又怎么说呢?他也是红衣主教;你去问问他的仆从给主人裹过多少次伤口吧。” “唉!”巴赞叹着气说,“这我知道,先生,现如今这天下是全乱套了。” 这当口,两个年轻人和这个可怜的仆从都下了楼。 “给我抓住马镫,巴赞,”阿拉密斯说。 说着,他纵身跃上马鞍,姿态一如平日那般优雅轻盈;但是禁不住这匹名种好马又是打圈又是腾跃,骑手只觉得伤口疼痛难当,脸色变得煞白,身体摇晃起来。达德尼昂事先就担心会出意外,所以眼睛一直没离开过阿拉密斯,一见情况不妙,便抢步上前把他扶下马来,送回客店房间。 “没事儿,亲爱的阿拉密斯,您好好养伤,”他说,“我一个人去找阿托斯。” “您真是条铁打的好汉,”阿拉密斯对他说。 “不,我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可您待在这儿等我,怎么打发日子呢?总不会再给那些手指啊,祝福啊之类的东西做注疏了吧,嗯?” 阿拉密斯笑了笑。 “我做诗,”他说。 “对,做些像德?谢芙勒兹夫人侍女的那封信一样香喷喷的诗吧。您还可以教巴赞学点音韵学,这样他会心里好受些、至于这匹马,您不妨每天骑一小会儿,这样多骑骑,身手就会灵便起来的。” “哦!要说这个,您只管放心,”阿拉密斯说,“等您回来,我准能跟您走,不会有问题。” 两人相互道了别,达德尼昂又对巴赞和老板娘叮嘱了一番,让他们好好照顾他的朋友,十分钟后,他已经上马朝亚眠而去。 他怎样才能找到阿托斯,或者说,他到底能找到阿托斯吗? 当时阿托斯给撇下的那会儿处境是很危急的;他完全有可能支持不住。达德尼昂想到这儿,不由得蹙紧额头连叹几声,暗自发誓说,此仇非报不可。在他所有的朋友中间;阿托斯的年龄*大,从表面上看来,他的兴趣爱好跟达德尼昂的相距*远,然而,达德尼昂却对这位绅士具有一种特别的感情。阿托斯的气质高贵儒雅、卓尔不群,尽管他一味深自韬晦,不露行藏,但神情举止之间还是常常会透露出一种雍容华贵的大家风度,他的情绪从不大起大落,这就使他成为世界上*容易相处的同伴,他那欢快的神态显得有些勉强、有些辛辣,他的勇敢要不是罕见的冷静使然,简直要让人说是盲目的了,而正是他身上的这些品性,不仅赢得了达德尼昂的尊敬和友谊,而且赢得了他的崇拜。 其实,逢到阿托斯心情好的对候,即使把他跟神情高贵、举止洒脱的德?特雷维尔先生相比,他也绝不逊色;他是中等个子,但是身材极好,看上去显得那么匀称;波尔多斯的力气在火枪营有口皆碑,但这个巨人好几次跟阿托斯较量都败下阵来;阿托斯的脸上,两眼炯炯有神,鼻梁挺直,下巴的轮廓分明有如布鲁图,整张脸上透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高雅的气质;他的手从来不加保养,却仍教整天用杏仁膏和香油保养双手的阿拉密斯看得心灰意冷;他的嗓音深沉而又悦耳;而且,在他身上自有一些难以言表、每每使人相形失色的特点,那就是对世事人情的洞明练达,对上流社会的诸熟审悉,还有那种在举手投足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出身世家的气度风范。 要说操办一顿筵席,阿托斯张罗得比谁都出色,每位宾客都能按其先人或本人的品秩身份安排就座。要说纹章学,阿托斯对王国所有的名门望族,对它们的系谱、姻亲、纹徽以及纹徽的出典全都了如指掌。礼仪典章,事无巨细他全都谙熟在胸,他说得出地位显赫的领主拥有哪些特权,对犬猎和鹰猎更是极其在行,有一天路易十三和他聊起这门精湛的技艺,他侃侃而谈,那位素以行家里手著称的国王不禁听得惊叹不已。 如同那个时代所有的贵族领主一样,他骑马使剑无不娴熟自如、得心应手。更突出的是:他学过的知识很少有遗忘的,即便是那些学究气很重的学问,尽管在那个年头一般绅士难得有人肯在那上面下功夫,可阿托斯照样挺当回事,所以每当阿拉密斯搬弄他那点拉丁文,而波尔多斯又做出一副听得懂的样子的时候,阿托斯总会忍俊不禁;甚至有过两三回,阿拉密斯脱口说句拉丁文,语法出了毛病,阿托斯居然帮他纠正了动词变位、名词变格的错误,弄得那几个朋友惊诧之极。还有,尽管那年头人心不古,军人信仰不虔、昧着良心,情人翻云覆雨、用情不如我们这年头专一,穷人则全然没把天主定下的第七诫放在心上,可是阿托斯的端方正直却是无可指摘的。因此,阿托斯是个非常杰出的人物。 然而,这么端方的品性,这么出众的仪表,这么高雅的气质,却眼看得慢慢地纳入了世俗生活的轨道,犹如一个老人在体力上和智力上都变得衰弱、愚钝了一样。阿托斯常有心情忧郁的时候,遇到这种时候,他的风采就会变得黯然失色,那些闪光点就像销匿进了深邃的黑暗之中。 于是,天神般的人物不见了,剩下的仅仅是个不起眼的凡人。脑袋耷拉,两眼无光,说话滞缓而尖刻,可以一连几个钟头不是瞅着酒瓶和酒杯,就是瞅着格里莫;这个仆从早已习惯了按主人的手势办事,能从主人全无表情的目光中看出主人*隐秘的愿望,即刻就去办妥。赶上哪天四位朋友聚在一起说话的时候,阿托斯即便说上片言只语,也是十分难得的。可要说喝酒,情况却不一样了,阿托斯一个能抵四个,而且喝得再多也不会失态,只是眉头蹙得更紧、神色更加忧郁而已。 达德尼昂,我们知道他是个生性敏锐,爱刨根问底的人,但任凭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多么好奇,还是没能探问出阿托斯这般消沉的原由,对其中的情况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从来没人给阿托斯来过信,而他的一举一动,也从来没有隐瞒过这几位朋友。 不能说他的这种忧愁是喝酒引起的,因为正相反,他喝酒只是为了借酒浇愁,不过我们前面说过,这个药方并不灵验,反而只会使他更添愁绪。这种极度的忧郁,也不能归咎于赌博,因为阿托斯不像波尔多斯那样,赢了就唱歌,输了就骂娘,他赢钱就跟输钱同样的喜怒不形于色。有天晚上,大家瞧着他在火枪营俱乐部先赢了三千皮斯托尔,然后又全部输得精光,连同那根出席盛宴用的绣金腰带都输掉了;临末了又全数都赢了回来,而且还多赢了一百个路易,而尽管输赢变化大起大落,他那两道清秀的黑眉毛始终没有抬高或拉下过一分一毫,他那双手始终没有失却珠玉似的光泽,他的谈吐(这晚上他心情颇好)也始终是平静和愉快的。 他的阴郁的脸色,也不像我们的比邻英国人那样是气候影响所致,因为他的这种忧郁通常到了每年天气*好的季节反而会变本加厉;六月和七月是阿托斯心绪*糟糕的日子。 眼下,他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人家跟他讲起将来,他也总是耸耸肩膀;所以他的秘密是在过去,这话早有人影影绰绰地对达德尼昂提起过。 哪怕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哪怕人家用尽机巧向他提出问题;也休想从他的眼睛,更休想从他的嘴里探出半点端倪,这层笼罩着他整个人的神秘色彩更使别人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嗯,”达德尼昂边想边说,“可怜的阿托斯这会儿说不定已经死了,而且是死于我的过错,因为这事是我把他扯进去的,他既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不会从中有任何得益。” “再说,先生,”布朗谢应声说,“我们没丢命,还应该说是多亏了他。您还记得他是怎么喊的吗:‘快跑,达德尼昂!我中圈套了。’他放了两枪以后,那乒乒乓乓的剑声有多么可怕!简直就像跟二十个疯子,或者干脆说二十个发疯的魔鬼在打架!” 这些话更惹得达德尼昂一心只想快些见到阿托斯,尽管胯下的骏马已经跑得够快了,他还是用马刺狠狠地在马肚皮上勒了一下,骏马带着它的骑士奔驰而去。 上午十一点钟光景,亚眠已经遥遥在望;十一点半,他们来到了那家该死的客店门前。 达德尼昂一路上就在思量,要用什么办法狠狠惩罚这个奸诈可恶的老板方能解心头之恨,可那会儿只是一种期待。所以这会儿他进客店门时,把帽子压到眼睛上面,左手握住剑柄,右手把马鞭甩得呼呼生风。 “你还认识我吗?”他冲着迎上前来鞠躬的客店主人说。 “恕我眼拙,老爷,”这家伙回答说,达德尼昂带来的那两匹珠光宝气的骏马让他看得眼睛发花,一时回不过神来。 “啊!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老爷。” “好吧,只消几句话就能叫你记起来的。差不多两个星期以前,你居然胆敢诬陷一位绅士是造假币的,你后来把他怎么样了?” 客店主人脸色变得刷白,因为达德尼昂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布朗谢也学着主人的样。 “哎!老爷,别跟我提这事儿喽,”店主人带着哭腔嚷道,“哎!老爷,我犯了这么个过错,付了多大的代价哟!哎!我真是倒霉唷!” “我在问你,那位绅士怎么样了?” “请听我告诉您,老爷,您先请息怒。求您啦,请坐呀!” 达德尼昂气急攻心,一时说不出话来,于是一屁股坐了下来,神情严峻得像审判官。布朗谢也神气活现地坐在扶手椅里。 “事情是这样的,老爷,”店主人浑身筛糠似的打着哆嗦说,“因为这会儿我认出您来了;我跟您说的这位绅士争执起来的那会儿,跑掉的那位就是您。” “对,是我;所以你得明白,要是你不把事情全说出来,就别想叫我饶你。” “请听我说下去,我会把事情全都说出来的。” “讲。” “我事先就接到当局通知,说是有个造假市的惯犯要带着几个同伙到我的店里来,而且全部伪装成禁军或者火枪手的模样。你们骑什么马,带几个仆从,还有你们几位老爷的相貌,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 “后来呢?往下说,”达德尼昂说,他立即明白了这些准确的情报是从哪儿来的。 “当局还派来六个人给我做帮手,这么着,我就按照当局的命令,做了一些在我看来刻不容缓的安排,要查出那个所谓的假币犯。” “你还这么说!”达德尼昂喝道,假币犯这个词儿他听着就来火。 “请原谅我这么说,老爷,可要不然我就没法说得清哪。我看见当局就害怕,您也明白,咱们这号开店的可惹他们不起唷。” “我再问你一遍,这位绅士在哪儿?他怎么样了?死了还是没死?” “请别急,老爷,我这就要说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您是知道的,您那么匆匆忙忙的一走,”店主人露出的一丝狡狯神情,没能逃过达德尼昂的眼睛,“就更显得真有这么回事了。您那位绅士朋友拼死抵抗。他的仆从不知怎么搞的,又跟当局派来的那些扮成马房伙计的人吵了起来,……” “啊!你这家伙!”达德尼昂嚷道,“你们早就串通好了,我不知道我当时干吗没把你们全都杀了!” “唉!不是这么回事,老爷,我们没串通,这您马上就会明白的。您那位朋友(请原谅我没法说出他的名字,他想必有个很体面的名字,可我实在不知道),您那位朋友放了两枪解决了两个对手以后,挥动长剑且战且退,一剑把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刺成了重伤,又一下剑背把我敲得晕了过去。” “你这混蛋有完没完?”达德尼昂说,“阿托斯呢,阿托斯怎么样了?” “我对老爷说了,他一边使剑一边往后退,退着退着退到了地窖的踏级,因为地窖的门开着,他就拔下钥匙,反手把自己关在了里面。我们眼看他在里面逃不走,也就由他去待在里面了。” “哦,”达德尼昂说,“你们倒不是非要杀了他不可,只是想把他关起来啰。” “老天在上!有谁关过他啦,老爷?他是自己把自己关在那里面的,我可以向您发誓。在那以前他已经把我们弄得够惨的,一个死在他的枪下,还有两个受了重伤。死人和两个伤员都让他们的同伴给抬走了,以后我再也没听人说起过这些人。我自己恢复知觉以后,就跑去找镇上的长官,把事情一五一十讲给他听,问他我该把那个地窖里的人怎么办。可是长官仿佛十分惊讶;他对我说,我告诉他的这些事情他一无所知,我接到的命令不是他下达的,要是我胆敢对任何人说他跟这场斗殴有半点瓜葛,他就让人把我吊起来。看来我是弄拧了,先生,错抓了这一个而让该抓的那个人逃掉了。” “阿托斯呢?”达德尼昂嚷道,听到地方当局对这事撒手不管,他心头的焦急更是有增无已,“阿托斯呢,他怎么样了?” “我因为急于想对他赔个不是,”店主人接着说,“就跑到地窖门口要放他出来。哎!先生,可他简直不是个人,而是个魔鬼。听到要放他出来,他冲我说这是给他安排的圈套,还说要他出来,他先得提条件。我低声下气地告诉他说,我准备接受他的条件,我这么低声下气,是因为我没法不对自己承认,我这么得罪了一位陛下的火枪手以后,处境实在糟糕透了。 “‘首先,’他说,‘我要你们把我的仆从还给我,武器全得带上。’ “我赶紧照办;因为您很明白,先生,只要是您朋友的吩咐,我是准备一切照办的。这么着,格里莫先生(这一位通报过他名字,尽管他话也不多),虽说他的伤势没好,就下到地窖里去了;他主人等他一进去,马上又把门堵上,命令我们待在店堂里不许下去。” “他现在到底在哪儿?”达德尼昂嚷道,“阿托斯在哪儿?” “在地窖里,先生。” “什么,你这家伙,你居然一直把他关到现在?” “天地良心哟!不是这么回事喔,先生。我会把他关在地窖里!敢情您是不知道他在地窖里都干了些什么哟!哎!要是您能让他出来,先生,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这么说他是在那里面,我去地窖就能我到他?” “一点不错,先生,他说什么也不肯出来。我们每天用长柄叉叉了面包从通风窗给他送进去,他要吃肉就还得叉肉进去;可是,唉!这点面包和肉,跟他消耗的别的东西比起来就算不了什么啰。有一回,我带着两个伙计想下去看看,没想到他却火冒三丈,大发脾气。我只听见他的手枪和他那仆从的短筒火枪咔哒咔哒顶上了发火器。我问他们想要干什么,当主人的回答说,他和他的仆从有四十发弹药好打,他们就是打到*后一枪也决不让我们跨进这地窖一步。我没法子了,先生;就跑去向长官诉苦,没想长官冲我说,我这是自作自受,我侮辱了一位到店里投宿的贵客,这就是给我的教训。” “那么后来呢?……”达德尼昂说,他瞧着店主人的可怜相,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打那以后,先生,”这一位接着往下说,“我的日子就惨得不能再惨喽;因为,先生,您得知道店里所有的存货都放在地窖里;那里有我们一瓶瓶、一桶桶的葡萄酒,还有啤酒,油,香料,肥膘和香肠,统统都在里面;因为他不许我们下去,我们就只好把上店里来喝酒吃菜的客人全都回绝了,结果弄得店里天天都亏本。您的朋友再在我的地窖里待上一个礼拜,我真的就得破产了。” “这是报应,傻瓜。你说,就凭我们这样子,难道还看不出我们都是体面人,根本不会造假币的吗?” “对,先生,对,您说得一点不错,”店主人说道,“可是您听呀,听呀,他又在发脾气了。” “敢情又有人跟他找麻烦了,”达德尼昂说。 “可也没法不跟他找麻烦呀,”店主人嚷道,“店里刚来了两位英国爷们。” “嗯?” “嗯,英国人喜欢喝好酒,这您也知道,先生;他们吩咐要*好的葡萄酒。我老婆就去跟阿托斯先生商量,求他让她进去为那两位先生拿酒;可是他照样不肯答应。喔!老天保佑!这会儿可是愈闹愈凶喽!” 达德尼昂果然听见从地窖的方向传来一阵喧哗声;他立起身来,让店主人拧搓着两手在前面带路,布朗谢端着顶上膛的火枪跟在后面,来到出事的地点。 那两个英国绅士非常恼火,他们经过长途跋涉,这会儿正饥渴难忍。 ……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仲马(1802年7月24日-1870年12月5日),文学界称大仲马,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自学成才,一生写的各种著作达300卷之多,主要以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大仲马信守共和政见,反对君主专政。由于他的黑白混血人身份,其一生都受种族主义的困扰。其子小仲马也是著名作家。
-

炖马靴-短篇小说30年精选
¥21.4¥49.8 -

太白金星有点烦
¥27.0¥45.0 -

间谍故事
¥16.7¥45.0 -

长安的荔枝
¥27.0¥45.0 -

马尾树:六篇小说
¥20.7¥56.0 -

沧浪之水(八品)
¥18.6¥49.0 -

我这一辈子:老舍中短篇小说集
¥10.8¥36.0 -

暗杀大师-死亡信使
¥25.5¥49.9 -

小公务员之死-啜饮一瓢人世的炎凉
¥11.8¥24.0 -

悉达多
¥13.4¥28.0 -

姑妈的宝刀
¥11.4¥30.0 -

山月记
¥18.4¥49.8 -

局外人
¥9.8¥35.0 -

布谷鸟的蛋(八品)
¥16.2¥49.0 -

额尔古纳河右岸/茅盾文学奖
¥22.4¥32.0 -

面纱
¥19.4¥45.0 -

24个比利
¥16.4¥39.0 -

陈忠实短篇小说选萃
¥16.0¥38.0 -

呼兰河传
¥9.9¥38.0 -

废物庄园-艾尔蒙哲系列第一部
¥15.1¥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