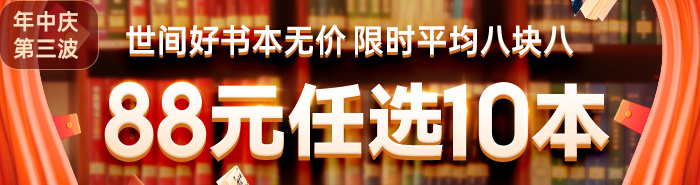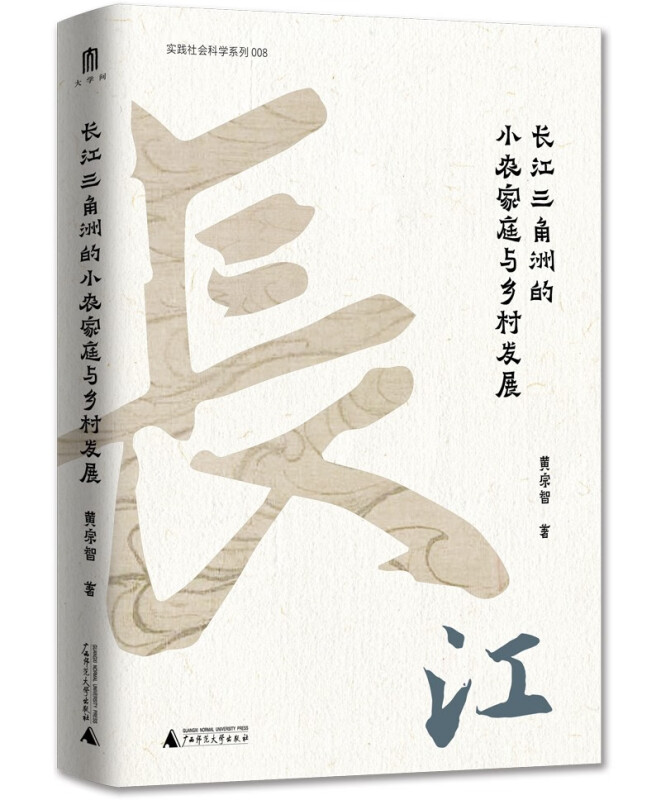
大学问·黄宗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代表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 ISBN:9787559853042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592
- 出版时间:2023-03-01
- 条形码:9787559853042 ; 978-7-5598-5304-2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大众本书卖点
1.“列文森中国研究*佳著作奖”获奖图书,长销30年的经典之作,周锡瑞、怀默霆、周黎安重点评介,《美国社会学学刊》《开放时代》等发文评论,“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8号图书。
2.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得主、“超级教授”黄宗智扛鼎之作,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当代中国发展和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经典著作。
3.探讨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与如何认识中国的关键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商品经济远较华北活跃的江南没有实现向资本主义的跨越?为什么江南的小农家庭生产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能够取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基于西方经验的各种社会科学“规范认识”有哪些局限?
4.发展和完善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揭示了江南小农家庭从明清到改革开放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去内卷化”发展,既澄清了之前的历史,也照亮了现代。
5.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全书以有实地调查资料的8个村庄和作者实地调查的6个自然村为考察对象,以明清至20世纪80年代为考察时段,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两方面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中观研究,既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6.基于丰富详实的史料,对中国小农经济做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全书深度利用满铁资料,系统运用传世文献和实地调查所得资料,由经济领域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指出江南在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内卷化和社会分化现象,以及改革开放后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发展。
7.全新再版,精心校订,作者新增长篇《合序》作为导读。 编辑推荐
凭借《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黄宗智先生斩获了1985年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七年之后,黄宗智先生又以《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荣获1992年的“列文森中国研究*佳著作奖”。黄宗智先生这两本主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中国农业史和乡村经济的著作甫一出版就产生了巨大影响,史景迁、罗威廉、周锡瑞、怀默霆等著名学者先后撰文评介,《美国社会学学刊》《纽约书评杂志》《亚洲史研究》等顶级期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时至今日,黄宗智先生这两本书的影响力依然持久不衰。对于每一个想了解前现代中国历史,以及对当今中国农村变革和经济发展感兴趣的读者,黄老师的这两本书都是非常好的入门之选。
内容简介
本书为黄宗智扛鼎之作,是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当代中国发展和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经典著作。书中基于满铁资料等大量史料与作者实地调研所得资料,对明清以来江南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特点做了深入考察,探讨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问题,尤其就中国江南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给出了极具深度的解释。全书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展和完善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揭示了江南小农家庭从明清到改革开放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去内卷化”发展。本书曾获列文森奖。
目录
新版合序
中文版序
**章 导论
**编 1949年以前
第二章 长江三角洲的生态系统
第三章 商品化与家庭生产
第四章 商品化与经营式农业
第五章 商品化与内卷型增长
第六章 农民与市场
第七章 帝国主义、城市发展与农村内卷化
第八章 两种类型的村社
第二编 1949年以后
第九章 旧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造
第十章 集体、家庭与副业生产
第十一章 农业的增长与发展
第十二章 乡村工业化
第十三章 乡村发展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
第十四章 半农半工的村庄
第三编 结语
第十五章 一个总结
第十六章 几点思考
附录
引用资料
约谈村民
引用书刊目录
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
——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
索引
节选
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有非常大的不同。较之华北,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所有权变换频率更低,生态系统更为稳定,经营方式也更加灵活多样。这些差异,使长江三角洲的农场比华北农场具有更强的应变弹性,也使得两地对革命的反应有很大差异。
——编者按 华北和长三角地区乡村对比 土地所有的稳定性
商品化如何影响到这些不同的村社类型及其进程?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发现的历史事实竟是*令人惊讶的。薛家埭等土地的使用情况出人意料地并没有比商品化程度较低的沙井村变动得更快,而是显示出十分突出的持续性。
田底权的变换确实非常快,买卖田底权犹如买卖股票、债券那样频繁。1940年至少有80名不在地主拥有村里的田底权,*大的是镇上的许公记米行,拥有26亩田底权,以及松江的顾家,拥有34亩田底权(满铁上海事务所,1940:表6)。但是田底权的变换对村庄的生活几乎没有影响。买卖田底权差不多总是在两个不在地主之间进行。有时,田底权的变换意味着农民要换一个地方去交租;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连这样的变动都没有,因为经办收租的仍是原来的米商。而且,农民们对田底权的转手毫不在意,以至很难记得这些事情。薛家埭等村民们能在满铁调查者面前回忆起的仅有一起田底权的变换,之所以能回忆起是因为那次买下田底权的是同村的农民。顾铭芝是松江县富户顾家的一员,本人是县里首屈一指的不在地主,拥有300亩田底权(其中73亩在华阳桥)。20世纪30年代初,顾氏为了去美国留学而卖掉他的田底权。或许因为当时经济不景气,顾氏颇不寻常地把大部分田底权卖给了农民。薛家埭等村村民中那些仅有的田底权拥有者(占耕地面积的13%)就是从那次交易中产生的,他们是西里行浜的陆寿堂(20亩)、陆金堂(12亩)、高长生(8亩)和高良生(5亩),薛家埭的薛炳荣(14亩)和薛培根(14亩)。其余村民们仅占有一些不足一亩的零碎土地,通常就是自己的宅基地。
在农民们看来,田面权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这决定谁耕种哪块地。田面权的买卖受到各种习俗的约束,极少绝卖。在日本人做调查时,薛家埭等村农民只能回忆起两例出卖田面权的事。1932年,何家埭的何有根穷困得走投无路,把家里四代耕种的12亩地的田面权卖给了高家埭的高金唐和高长生,用所得支付了他母亲的丧葬费。1939年,高家埭的高伯唐因连续3年交不起租,把8亩田面权卖给了同村的高全生(满铁上海事务所,1940:58—59,195,表6)。
即使那种附有条件、在若干年后可以赎回的田面权买卖也很少见,村民们也只能回忆起两例。1935年,西里行浜南埭的陆寿堂以每亩26元的价格(绝卖价为每亩33元左右)将4亩田面权典卖给高家埭的高阿根。同年,许步山桥的杨土生以同样的价格把6亩田面权典卖给同村的杨味生(同上)。显然,这里的村民们耕种土地有极大的稳定性,大部分村民一代接一代地耕种同一块家庭田地。
由于不了解这种双层的土地占有制度,许多有关像薛家埭等这样的村庄的资料都不准确。土地关系被等同于田底权关系,而田面权的拥有者因为租种田底权而仅被视为佃户。尽管出卖田面权是社会上流行的实际做法,但清代和民国的法律对此均不予承认。天野元之助和他的调查组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做了细致而内行的调查,但甚至连他们也未能完全把握田面权的性质,从而忽视了一种出租田面权的叫作“混种”的制度。“混种”并不常见,但这种做法证实了双层的土地占有制的存在。高世根向他的叔父良生租了5亩地的田面权,除了向拥有田底权的地主顾铭芝交纳每亩8.2斗的地租,还因租了田面权而向良生交每亩3斗的租。陆海来的情况与此类同,他以每亩3.5斗的租额向屠品山租了3亩地的田面权(调查—Ⅰ—5)。
华北没有类似长江三角洲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土地转手和租佃关系仅涉及单层的土地所有者。一个出卖田地的人可能作为买主的佃户继续在原来的地块耕作,但是在河北东北部这种租约每年须更新一次,在山东西北部的两年三熟制地区则每两年确认一次(黄宗智,1986:221)。更常见的是土地买卖后耕作者也随之变换;所以土地的频繁买卖也意味着土地耕作者的频繁更换。下述事例正与薛家埭等村形成对照。米厂村的农民在1937年时回忆起自19世纪90年代到1936年间,村民们买进土地共73例,计538.4亩(全村耕地面积为2237亩);其中424亩系后20年间米厂村开始植棉后进行的交易(黄宗智,1986:111—112)。在种果树的前梁各庄,农民们能回忆起74例,共达1292.2亩(耕地面积为1564亩)的土地转手交易(满铁,冀东1937c:6—10)。甚至在商品化程度很低的大北关村,农民们也能回想起76例买进土地的交易,在全村2438亩耕地中占402.2亩(满铁,冀东1937a:6—9)。在前梁各庄,满铁的调查者们还能够了解到相当详细的出卖土地情况,达44例,涉及691亩耕地。
我们没有可资对照的有关沙井村的资料,但以满铁调查者绘制的1940年的该村的土地分布地图看,田地被分割得非常零碎,土地占有呈流动状态几乎无可置疑。即使是同族群体的成员,田地也极少相互毗连。全村1182亩耕地中有426亩(即36%)为外村人占有,大多系附近的小农,其中邻近的望泉和石门两村的居民即占了307.4亩(《惯调》,1:附图;2:464—472;参阅黄宗智,1986:82)。
这些由村民回忆而汇总的资料是不完全的,但显然已足够证实华北农村土地占有和使用的高度流动性。商品化程度低的大北关和沙井两村与高度商品化的米厂和前梁各庄同样地显示出土地占有权的流动性,这提醒我们不能将流动性简单地等同于商品化。长江三角洲的薛家埭等商品化的程度更高,但土地关系极其稳定,也更证明了这一点。 生态系统,多种经营和稳定性
我曾经指出,华北土地占有权的频繁变换可归因于这个地区结构性的贫困和生态上的不稳定。艰难的旱作农业区与密集的人口造成了结构性的贫困;这种结构性的贫困继而又削弱了该地区对天灾人祸的承受力。华北的小农犹如处于水淹及颈的境地,哪怕*微小的波浪也足以使其遭受灭顶之灾。正如华北的一个村民所说的,一年灾害,三年负债;(连续)二年灾害,终生穷苦(黄宗智,1986:307)。自然灾害是迫使农民出卖土地的*主要原因。从1917年到1940年的23年间,沙井村遭受了4次水灾、1次旱灾,其中3次水灾大到足以毁灭该村一半到四分之三的年收成(同上书:223)。在*坏的情况下,农民们被剥夺了所有的生计,被迫离开村庄流浪。在这样的农村里,土地买卖频繁,村民流入和流出的比率也高。
满铁调查者绘制的沙井村地图所显示的该村社会结构和居住形态也证实了以上所述的情况。沙井村共有18个族团。1940年时该村7个原有族团只剩下了一户,而另有5户是新近两代才因各种原因而从不同地方移居沙井的:赵绍廷原系顺义县城的居民,因在沙井村有田,于1910年左右移居沙井;小贩傅菊是1910年代落户的;山东来的铁匠白成志因有姻亲在沙井,于1929年移居该村;任振纲系从邻近的石门村来的,他在原村无处栖身而在沙井有亲戚,于1930年左右移居;*后是景德福,也从石门村来,因为在沙井村买了田而于1939年移居(《惯调》,1:附录)。
薛家埭等村的农民却只能回忆起1939年曾有20%的庄稼毁于虫害,这是本世纪以来该村仅有的一次大的自然灾害。村民中无人能记得这里有过大的水、旱灾。就像本书第二章所陈述的那样,尽管长江三角洲并非没有生态问题,但它的自然条件远较华北稳定。从1401年至1900年500年间,此地仅发生过20次较大的水灾,而华北的黄河却几乎年年决口。
长江三角洲还得益于远较华北平原肥沃的土壤。确实,这也是使双层的土地租佃制度可行的条件,因为土地之高产使农民交了双层地租后尚可有所收益。而这样的制度在华北却绝无可能存在,一个佃农交付一半收成给地主后已难糊口,没有余力去支付另一层地租。
而且,由于较高的生活水平,长江三角洲家庭农场的活力较强。例如,西里行浜南埭的陆龙顺(生于1926年)丧父后不久因无力支付租种的4亩地的田租,只得将田面权交还地主,成为一个“小长年”。如果陆氏生活在华北,几乎没有可能从收入中节俭出足够的剩余来恢复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黄宗智,1986:210—211)。但陆龙顺有幸在当了3年长工后,偿还欠租,赎回4亩田面权(调查—Ⅰ—2)。生于1930年的吴余才的故事与此略同:父亲去世后,他去邻村当“小长年”,而他已婚的哥哥则仍耕种家里的田地。余才学会了养鸭,16岁时已精于此道,因此有一雇主以每年多出240斤米外加两个月假期的待遇诱其离开原来的雇主。余才的养鸭技术使他成为较理想的招婿对象,20岁时便入赘于许步山桥某户(调查—Ⅰ—4)。
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商品化和多种经营还提供了其他的就业和上升途径。许步山桥的杨味生(生于1906年)曾经非常落魄,仅租有两亩田面权。但他靠农闲时在低洼的水稻田里挖泥鳅(这在江南一带被视为美味)攒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钱。杨和他的4个十几岁的孩子天未明即起床,步行3小时到约18公里外的地方,从水底铲挖泥鳅,每人每天约可得十余斤。然后他们到华阳桥镇设摊,以每斤泥鳅换2.5—4斤米的价格出售。杨借此收入买下了6亩地(调查—Ⅰ—8)。
另一例是何家埭的何书堂(生于1917年)。何仅种6亩地,每年3月后便青黄不接,他的补充收入是冬天去镇上的餐馆打工,一月所得相当于80斤米。何还以一元钱100斤的价格买下荸荠,然后挑到松江县城设摊叫卖,赚20%左右的利润来贴补家用(调查—Ⅰ—4)。
诸如此类的辅助性收入并没有取代家庭农业,而是弥补了农业收入的不足,帮助小农维持了家庭农场。这类收入强化了而非削弱了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稳定。 变化对内卷化
历史事实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模式相悖。长江三角洲的高度商品化带来的不是村庄内部资本主义农场主和无产者的两极分化,而是相反;不是农民的背井离乡,而是相反。商品化和家庭化使长江三角洲的农场增强了应变的弹性。华北则没有同样的条件来减轻生态环境的打击和缺田少地带来的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下,共产党组织之所以没有能够在长江三角洲动员大量的农村人民参加革命是不足为奇的。尽管这里的租佃率很高,共产党号召进行一场反“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村革命时却应者寥寥。相反,华北平原的租佃率尽管很低,但农村生活的不安定却使农民较易响应革命的号召。华北农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在国共内战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根据社会现实修改了它原先的纲领,革命运动不一定会取得农民的拥护。华北出租的田地不到耕地面积的20%,革命如仅强调佃户反对“封建”地租,不会得到农村广大人民的拥护。共产党组织能够因地制宜,把抗税和保卫家园的号召加进他们的纲领之中,这是华北农村革命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裴宜理,1980;黄宗智,1986)。
作者简介
黄宗智,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UCLA历史系,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等。
-

谈起古代.仕途就这回事
¥9.8¥29.8 -

你不知道的古人生活冷知识
¥18.1¥49.0 -

安史之乱
¥25.8¥68.0 -

两张图读懂两宋
¥16.0¥76.0 -

名家小史——中国历代党争史(图文版)
¥12.8¥29.8 -

中国历史年表-(修订本)
¥5.8¥18.0 -

民国往事
¥7.7¥18.0 -

三国史话
¥13.4¥42.0 -

埃及法老图坦卡蒙
¥26.2¥69.0 -

中国历史的瞬间
¥17.9¥38.0 -

(精)近代中国人物论
¥22.4¥68.0 -

帝国失格:明清易代十六人
¥17.7¥59.0 -

资治通鉴(精装)
¥18.6¥49.0 -

狄更斯英国简史
¥18.1¥42.0 -

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22.7¥59.8 -

中国庭园记
¥13.8¥26.0 -

牛史
¥18.7¥48.0 -

中国兵器史
¥28.2¥88.0 -

中国通史
¥19.4¥45.0 -

帝国的技艺:统治不可统治之地
¥30.8¥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