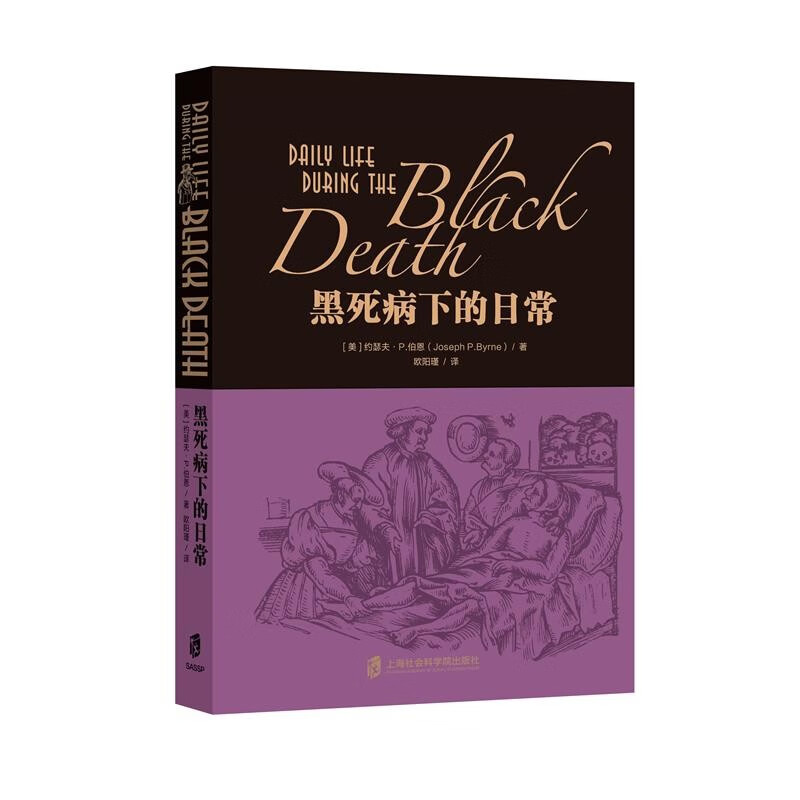- ISBN:9787552040142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468
- 出版时间:2023-04-01
- 条形码:9787552040142 ; 978-7-5520-4014-2
本书特色
黑死病下的日常一点儿也不正常,当瘟疫袭来时,人们的日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聚焦于生活中的各个场景——医学院、诊所、家庭、教堂、传染病院等,探讨黑死病的起源、发展和影响。约瑟夫·P.伯恩带领我们进入医学院的教室,在那里,正在教授关于黑死病的错误理论,而医学生们即将开启徒劳无用地治疗受害者的职业生涯;进入市政厅,在那里,市民领袖们正在苦苦思索如何应对黑死病,但却很难阻止疫情的蔓延;进入教会和教堂,在那里,主教和神父们正在一遍遍地重复着神的启示,可根本无助于缓解病情……伯恩还尽可能地利用当时的目击者和受害者的文字记录,讨论欧洲各地和伊斯兰世界在面对疫情时所采取的举措,以及瘟疫所引发的医学、文学、艺术、丧葬习俗等方面的变化。
内容简介
1348年,死神挥动镰刀,整个欧洲笼罩在黑死病的阴影下,学校停课、教堂关门、店铺废弃、邻里远迁、建筑停工……街道上不再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摊贩们的叫卖声变成了尸体搬运工们粗声粗气的吆喝,堆满了尸体和濒死之人的马车嘎吱嘎吱地提醒着所有人死亡的迫近。人们蓦然发现,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但受到了疾病的威胁,而且永远被疾病改变了。 但生活还在继续,在医学院、诊所、家庭、教堂、修道院、传染病院、市政厅以及其他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依旧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生命力,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每个人都在挣扎着适应这个特殊的时代。回溯这段不同寻常的日常,我们会发现:“如果说历史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人类总能战胜自然和人类自身各种邪恶冲动带来的威胁。”
目录
致谢001
年表001
引言001
**章 在医学院014
中世纪的健康与疾病理论015
中世纪的医学教育021
中世纪的瘟疫理论025
近代早期的医学教育032
近代初期的瘟疫理论039
第二章 在诊所046
形形色色的医者046
社会中的内科医生063
医学防护(预防)068
诊断瘟疫078
治疗方法083
第三章 在家里应对鼠疫092
家庭: 结构与功能092
家人亡故099
鼠疫侵袭家庭110
第四章 在教堂与教堂墓地119
教会与社会119
教堂123
葬礼129
坟墓、掘墓人与安葬137
宗教艺术与仪式148
第五章 在主教座堂与修道院163
主教与瘟疫164
中世纪神职人员的问题165
黑死病与修道院180
第六章 在传染病院187
封闭措施188
医院194
茅屋与小木屋201
传染病院205
第七章 在市政厅229
欧洲城市的管理229
鼠疫对管治的影响231
市政当局对疫情的普遍反应234
应对鼠疫的立法246
瘟疫之后258
第八章 在欧洲的大街小巷268
城市街道269
道路与旅行283
第九章 在书店与戏院297
医学文献与瘟疫299
中世纪的通俗文学与瘟疫311
近代初期的通俗出版物318
瘟疫与英国的戏剧325
第十章 在村落与庄园340
乡村地区的瘟疫341
新的机会350
地主的压榨356
威压与国家干预364
第十一章 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372
中世纪伊斯兰社会中的瘟疫373
中世纪的瘟疫与伊斯兰医学384
瘟疫和伊斯兰社会393
第十二章 瘟疫在欧洲的*后时刻409
欧洲的瘟疫消失411
西欧的*后一次大流行:马赛,1720—1722年418
俄国的*后一场大瘟疫:莫斯科,1770—1772年424
尾声428
选读书目435
节选
第六章 在传染病院
无论人们曾经多么强烈地想要相信瘟疫源自上帝的烈怒、天体的合相或者污浊的空气,但他们都决定迅速行动起来,仿佛瘟疫是在人与人之间或者通过“受感染”的物品直接传播一样。在《十日谈》一书中,薄伽丘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头猪在一名染疫死者的衣物中拱来拱去觅食,然后很快就染病死了。当时的人认为,接触[touch,它是“传染”(contagion)一词的由来]、呼吸、体味,甚至是所谓人们眼中发出的光线,都会传播这种疾病。人们逃离的时候,不但是避开了污浊的空气,也是逃离了身边有可能让他们“染上”鼠疫的病人。1348年和1349年,薄伽丘和其他许多作家都评论过父母遗弃子女、兄弟相弃等诸如此类的现象——这显然是一种道德沦丧,但在人们确实有可能感染疾病的时候,也是一种谨慎的自我保护行为。市政当局往往会慢慢地将这种理论的含义变成官方举措,可一旦这么做了,当局就会用一种常常看上去很不人道的野蛮态度行事。**步就是把病人隔离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是将那些有可能已经染病的人隔离起来。官员们*终还扩大了“封闭”的范围,给患者兴建了特殊的住处;这种住所常常不过是位于城墙之外的棚屋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局接管了一些更大的场所,比如医院和修道院,将它们用作鼠疫医院。*后,一些较大的城市兴建了专门的“传染病院”,用于收治患者和隔离潜在的感染者。到了17世纪中叶,欧洲各地的官吏都在拼命地采用所有的这些措施。 封闭措施
自愿隔离
1665年7月14日,正值鼠疫席卷各地之时,伦敦的一位杂货商把自己、妻子、儿子、3个女儿和1名学徒全都锁在了家里。此人已经储备了充足的食物、水和药品,靠一名一直守在雇主家窗外的仆人亚伯拉罕(Abraham)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亚伯拉罕送来他们所需的给养或者*新的“死亡名单”(Bills of Mortality)时,杂货商会打开二楼的一扇窗户,向外发射火药以净化进入的空气,然后用一只篮子把东西吊上来。那位仆人会点硫黄或火药对收到的信件进行熏蒸,并且喷上醋,然后才装入篮子里吊上去,而杂货商打开信件之前还会熏上一次。*后,亚伯拉罕染上鼠疫死了,一名老妇又向这一家子推荐了一个叫作托马斯·莫林斯(Thomas Molins)的仆人,后者已经感染过鼠疫,却幸存了下来。这一家人开始遭受坏血病之苦后,莫林斯给他们送来了柠檬与酸橙。其间家里有人感冒时,他们吓了一大跳,不过全家人都活了下来。莫林斯死后,一个全家都已去世的巡夜人接替了他,直到当年12月这一家子搬到了伦敦的郊区。这一行动是杂货商根据官方发布的“死亡名单”中显示的死亡趋势而采取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类型的自我隔离与伦敦一位内科医生,同时也是塞缪尔·佩皮斯邻居的伯内特医生(Dr. Burnet)的自我隔离之举比较一下。1665年6月11日,佩皮斯曾步行经过那位医生的住宅: 看到可怜的伯内特医生家的门是关着的。但我听说,左邻右舍对此人都颇为感激,因为是他本人率先发现(仆人威廉感染了鼠疫),然后主动把自己关在家里——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做法。 伯内特后来被人指控说他误杀了威廉,并在同年8月25日死于鼠疫。佩皮斯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相当“奇怪,他的仆人早就死了,这个月他家又开门了。如今他本人也死了——真是个不幸的可怜之人”。实际上,伯内特是在对一名鼠疫患者进行了尸检之后死去的。 第三个例子无疑也是其中*著名的一个,那就是英国德比郡(Derbyshire)伊亚姆村(Eyam)的全村隔离。虽然那里远离伦敦,但伊亚姆的村民还是感染了瘟疫。据说,是1665年8月从鼠疫肆虐的首都运来了一车布匹,他们才染上了鼠疫。收到这批布料的裁缝**个死去,接着又死了很多的村民。时年28岁的牧师威廉·蒙佩松(William Mompesson)肯定地告诉大家,说*好的办法就是他们全部留下来,不要逃跑。于是,所有的村民都留在那里,承受着鼠疫肆虐带来的苦难。伊亚姆的村民与邻村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疫封锁线,无人可以越过,而村民所需的给养则会放在指定的地点。伊亚姆的村民靠着附近村庄的施舍生活,反过来,其他村庄则因伊亚姆村的牺牲而得以幸免。村中的母亲亲手埋葬了孩子,儿子则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父母。这场瘟疫持续了14个月之久,夺走了大约260位村民的性命,在*邻近的地区幸存下来的还不到100人。 欧洲的强制隔离
选择主动隔离自己、家人或者所属的群体是一回事,用武力强制实施这种隔离则是另一回事。1348年首度出现一些鼠疫病例之后,米兰便开始采取强制隔离措施了。当时的米兰政府由领主贝尔纳博·维斯孔蒂(Bernabò Visconti)领导,而不是由民选议会统治,所以能够迅速而毫不手软地采取行动。他们把*初发现的少数患者及其家人都封锁在自己的家里,直到所有人都死去,或者幸存下来的人证明身体健康才作罢。阿尼奥洛·迪·图拉(Agnolo di Tura)曾报告说,当时只死了3户人家,因此米兰并未遭遇意大利其他城市的种种可怕厄运。不过,在后来的瘟疫中,米兰没有再度获得成功,而在15世纪晚期以前,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没有效仿米兰的做法。 不论是由于空气污浊的理论、缺乏可供组织的资源,还是隔离对人类尊严的侵犯,反正中世纪晚期没有几座城市采取过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倡导这种政策的政府——比如维斯孔蒂领导的米兰、大公治下的佛罗伦萨以及伊丽莎白治下的英格兰——都属于组织有序的威权政府。就许多方面而言,这种行为也反映出了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冷酷无情的新基调。有很多16世纪早期由荷兰人文主义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所写的信函存世,他在其中一封中描述并讨论了强制隔离带来的道德问题:“在意大利,瘟疫迹象甫一出现,房屋就会上锁封闭,照料患者的人也会被隔离起来。有人说这样做很不人道,可实际上,这才是*高的人道,因为正是有了这种预防措施,瘟疫才得以被遏制,才只有少数人死亡。”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做法一直都饱受争议。 1557年,荷兰的鼠疫患者都受到了严厉的对待。家人虽然可以决定是否留在家里照顾患者,但一旦留在家里,就不能再出来。当局会用一条上锁的铁链和一道篱笆,将整座房子围起来,还会在门上挂上一束稻草,作为标记。从那时起,莱顿的稻草商就不准再用稻草捆的实物来做广告了,此时,他们只能展示绘制出来的稻草图片。海牙(Hague)的鼠疫患者家门上会标有“PP”字样,表示“有瘟疫”(plague present);在鲁尔蒙德(Roermond),当局则把印有“耶稣”一词的锡板贴在瘟疫患者家的前门上。所有门窗必须一直关着(这是一种常见的规定),只不过,荷兰人每天可以把门的上半部分打开一小段时间。凡是去过患者家里的人,此后的两个星期内在公共场合都须携带一根白色手杖。*后一位患者死亡或康复之后的6个星期里,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可以离家去购买东西或到教堂去做礼拜,但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只能到圣安东尼礼拜堂(St. Anthony’s Chapel)去。这些人也须携带一根白色手杖,并且不能靠近水井或者其他的水源地。 在英格兰的发展
伦敦将鼠疫患者隔离起来的做法始于1518年红衣主教沃尔西治下。但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政府之前,这种措施只偶尔实施过;该政府在一个瘟疫之年成立后,便开始采取更加有力的协调措施,来遏制瘟疫的影响。1568年,鼠疫患者的住宅要封闭20天,且不管有病没病,患者的所有家人都必须关在家里。他们的门上都钉着一张写有祷词的纸:“主啊,请怜悯我们。”一个由教区支付工资的“诚实孤身者”每天给他们准备食物,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去请掘墓人。必要之时,食物的费用由市政府支付,而官员们会把患者的所有衣物和被褥付之一炬。1578年,英格兰再度实施强制性的瘟疫法令,将隔离期延长到了6个星期。这种趋势还在朝着更加严格的强制隔离措施发展:1604年,议会宣布巡夜人可以使用“暴力”来约束隔离者,身上带有明显的鼠疫疮疤的人若是外出到公共场合,有可能被视为罪大恶极者并被处以绞刑,身体健康的隔离者若是被人发现非法外出,则有可能被当成流浪汉而受到鞭笞。英国的地方城镇在实施这项政策时都碰到了问题,尤其是在供养那些无力谋生的贫困隔离者方面。1593年向郡里寻求帮助时,莱斯特的市长曾对亨廷顿伯爵抱怨说,他们很难获得供养贫困隔离者的资金,应对瘟疫的支出已经上升到了500多英镑。该市当时正在为每家每户提供“肉、酒、火炭、蜡烛、水、肥皂,(以及一个)看守”。不过,即便是国家的首都,也没有会获得支持的保证。1593年,伦敦的清教徒威廉·雷诺兹(William Reynolds)曾给伊丽莎白女王手下的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称: 据我本人所知,有位患病的孕妇即将生产,在极大的痛苦中挣扎,她和孩子都死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前去施以援手。啊,你们是狗,啊,你们是魔鬼,你们是坏透了的恶棍,用野蛮的方式把患者锁起来,毫不顾及他们,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也不去看一看。 差不多与此同时,言辞同样犀利且早期曾当过疫病医生的内科医生西蒙·福尔曼(Simon Forman)发现,自己竟然跟一位明显已经染病的仆人被关在一起隔离;对此,他感到极不高兴。在后来撰写的一本瘟疫小册子里,他曾如此悲叹说: 啊,一个国家里那些可恨的毛虫是多么恶毒啊。他们也许认为,我既没有用金钱买通瘟疫,也没有出国去探寻疫病。可这是至高者(上帝)降下的……上次瘟疫期间,我没有从他们身边逃离,当时他们曾因我的存在和建议而感到欢喜。那时我既没有不怜悯任何人,也没有像他们对待我一样,把我家的大门关上。 1604年,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有20%的人都被隔离了(411户,共计1300人),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一个小村庄斯通村(Stone)里,则存在着115户隔离家庭。富人试图通过隐瞒染疫死亡的情况来逃避隔离,连一些不可一世的权威人士也耍过这样的花招。1604年,格洛斯特的市议员约翰·泰勒(John Taylor)家里有名仆人死于鼠疫,这一家子便偷偷地把仆人埋掉了。第二名仆人也染上了此病,并且接受了一位女性医生的治疗。在一场晚宴上,这名染病的仆人甚至侍候过格洛斯特的好几位市政领导人。直到这名仆人和另外几人都死了之后,这一欺骗行径才暴露出来。泰勒被罚了100英镑,而泰勒家也被封闭隔离起来了。然而,泰勒的儿子竟然破门而出,并且威胁说不管是谁,要是再想把他家的房子封上,他就开枪打死这个人。治安官抓住了他,把他关到了该市的牲口棚里。 1665年“大瘟疫”期间,伦敦继续采取这种措施,而人们的争论也依然很激烈。有些人埋怨说,这是用牺牲病人的办法去挽救健康的人;有些人声称,这种做法触怒了上帝,延长了疫情的蔓延时间;还有一些人则指出,这种政策的作用实际上适得其反。在一本名为《封闭染病之宅》(Shutting up Infected Houses)的小册子中,姓名不详的作者曾指出:“传染可能导致了数千人死亡,可封闭已让数万人丧生。”20年之前,英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Ⅰ)的专职教士约翰·费尔蒂(John Fealty)曾为“他相识的一位贵妇”写下了《抗疫之泪》。此书在“大瘟疫”期间重印,发行量极大: 瘟疫吞噬了一切,哀鸿遍野。于是,访客就这样死了,却不知死因是什么。疾病在召唤,饥饿在呼唤,匮乏在呼唤,痛苦在呼唤。一切都汇集起来,汇集在可怕的和谐中,汇集在恐怖的不和里,召唤着我们的崩溃,欢呼着我们的毁灭。 在封闭的房屋内部,恶臭的气味一定极其难闻,因为人与动物的正常体味与用于熏蒸的东西点燃之后散发的烟雾混合在一起,有硝石、焦油、烟草、树脂、硫黄、火药,以及较富裕家庭所用的香木、较贫困家庭所用的旧鞋子和皮革废料。难怪人们会反对当局的做法,难怪会出现像年轻气盛的泰勒或同样实行隔离政策的德国汉堡(Hamburg)市那3个破门而出、逃到乡下的人。后来,官员们发现那3人因染病而死在一座谷仓里,便立即将那座谷仓烧掉了。1665年那场“大瘟疫”暴发的半个世纪之后,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撰写了他那部令人震惊的“史书”兼警世故事《大疫之年日记》;当时,法国的马赛正在经受一场特别恐怖的鼠疫。笛福笔下的主人公H. F.承认在个人自由与公共需求的平衡方面存在问题,却根据3个理由大力抨击当局采取的隔离措施:民众纷纷逃走,所以这种措施没有起到作用,把健康的人与病人关在一起既不人道,“从医学上来看也是反常的”,那些感染了疫病却没有出现症状的人仍然自由来去。H. F.认为,自愿隔离很好,但强制隔离徒劳无用。尽管如此,恐惧仍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因素:在离鼠疫肆虐的伊亚姆村不远的布内尔(Bubnell),有位病人被左邻右舍怀疑是感染了鼠疫,于是他们便在此人的家门外安排了一名守卫,若是病人想走出家门,守卫就会用石头砸他。医生检查之后却证明,此人仅仅是得了感冒而已。
作者简介
约瑟夫.P.伯恩(Joseph P.Byrne)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Nashville, TN)贝尔蒙特大学(Belmont University)荣誉副教授,其研究领域广泛,发表过包括罗马地下墓穴和美国城市化研究在内的一系列文章,但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黑死病时期的意大利。其作品包括《黑死病》(The Black Death, 2004)和《黑死病下的日常》(Daily Life during the Black Death, 2006)等。
-

两张图读懂两宋
¥16.0¥76.0 -

你不知道的古人生活冷知识
¥24.5¥49.0 -

清朝穿越指南
¥21.6¥45.0 -

人类酷刑简史
¥32.5¥59.0 -

万历十五年
¥16.3¥25.0 -

唐潮:唐朝人的家常与流行
¥31.3¥68.0 -

朱元璋传
¥25.0¥39.0 -

汉朝其实很有趣
¥9.5¥38.0 -

从三十项发明阅读世界史
¥11.7¥39.0 -

消寒图:珍重待春风
¥19.7¥58.0 -

两晋其实很有趣
¥9.1¥35.0 -

至道无餘蕴矣:梁漱溟访谈录
¥21.8¥68.0 -

中国通史
¥34.7¥45.0 -

硬核原始人
¥19.5¥65.0 -

中国近代史
¥10.2¥20.0 -

胡同里的姑奶奶
¥25.0¥78.0 -

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
¥28.9¥45.8 -

创造圣经的城市
¥18.6¥58.0 -

谁是剽窃者:牛顿与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战争
¥15.8¥45.0 -

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第七部
¥15.2¥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