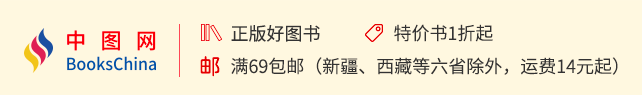- ISBN:9787508685748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285
- 出版时间:2018-05-01
- 条形码:9787508685748 ; 978-7-5086-8574-8
本书特色
书名“The Violet Hour”出自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意为“暮色苍茫的时刻”,用以形容人弥留之际,如同紫色暮霭,恢弘瑰丽。在书中,洛芙记录下六位伟大作家生命结束的场景:苏珊•桑塔格曾奇迹般地两度击败癌症,但这一次,生命不再眷顾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生研究死亡、拥抱死亡……;厄普代克通过体验和书写性爱来对抗死亡,他独一求而不得的便是描摹出死亡时刻的真实形态;狄兰•托马斯活得热烈,向死而生,他的生命在女人,以及他迷恋的名利之中消逝了……人生的末尾时刻,一切身外事变得十分渺小,只留下爱与自我。如果能体验一次死亡,或许我们的人生将全然不同。
本书荣获《纽约时报》年度图书,作者凯蒂•洛芙,纽约大学文学教授,被誉为与乔治•奥威尔比肩的“散文写作的典范”;译文出自知名文学译者刁俊春之笔,忠实典雅,金句频出;封面设计由崔晓晋操刀,印刷选用触感膜和烫银工艺,精致独特。
书中收录六张作家书房私照,能一窥伟大头脑背后的生活日常,具有收藏价值。
苏珊•桑塔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狄兰•托马斯、莫里斯•桑达克,死前陪在他们身边的是谁?约翰•厄普代克在书中歌颂性爱和出轨,是否取材于现实生活?
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吗?伟大思想家在面对死亡时,是否有普通人没有的智慧?
内容简介
十二岁那年,凯蒂?洛芙有了靠前次濒死体验。长大后,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也遭遇了父亲毫无先兆的自然死亡。她没能见他很后一面。自那之后,死亡开始强烈地吸引着她,她决定通过研究死亡,来探寻人生很后时刻的真相。她称之为:查看死亡。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几个名字跃入她的脑海:苏珊?桑塔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约翰?厄普代克、狄兰?托马斯、莫里斯?桑达克。这些伟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似乎都处理好了死亡的问题,拥有某种死亡智慧。洛芙认为,假如用语言捕捉死亡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他们是很有可能做到的人。通过大量与艺术家生前亲人和好友交谈,爬梳卷帙浩繁的文字资料,她在纸页上重现了作家们的很后时刻。《暮色将至》便是这样一部从死亡写起的逆向传记。每个人的人生,从死亡开始,缓缓地展开了。
前言
我忘了怎样呼吸。我正被拽到水面以下。那位出租车司机把我送进急诊室,因为我在车上昏迷了,而我母亲抱不动十二岁的我。
在《死亡的脸》(How We Die)一书中,舍温•努兰描述了肺炎对身体的影响:“那些被称为肺泡的微型气囊肿胀起来,并被炎症所破坏。结果就是,正常的气体交换受阻,血氧因而降低,与此同时,二氧化碳会堆积起来,直至重要的功能难以为继。当氧气水平降到一个关键点以下,大脑会通过更多的细胞死亡来体现这一点。”
有人给我戴上一个面罩。我尝到了氧气的甜美,就像品尝天空一样。
我发烧107度。在家的时候,母亲把我放进浴缸,里面放着冰块。在重症监护室,我的手臂上插着各种管子或者蛇形物;护士有善良的,也有邪恶的。一个实习生把一根针头插进我的动脉,测量氧气水平。旁边一张床上,一个婴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就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
三周后,我出院了,但没有彻底地好起来。
咳嗽非常严重,就像有一头动物睡在我床上,如影随形。*糟糕的日子里,母亲试图让我待在家,不去学校,但是我非常固执,一定要上学。
每到傍晚我都要发烧,浑身颤抖地吃完晚饭,做好作业,洗完澡。毫无疑问,这就是将永远伴随我的感觉了;没有一个方式,可以形容发烧之后的状态,或者说,即使有这样的方式,它也是苍白的,难以令人相信的,因为发烧就是一个世界。
醒来时睡衣被汗水浸湿,床单也因为汗水而湿透。汗水是令人感到羞辱的,是某种要加以遮掩的东西;发烧同样令人羞辱。
咨询了一些医生,也开了一些抗生素,我频繁进出医院。我父亲——本身就是医生——在那些医生说话的时候,非常安静。没有一个说法能解释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有一天,当我咳嗽的时候,纸巾里发现了血。口中有血的味道。我知道,这意味着我要死了,于是我做了明智的决定:不告诉任何人,包括母亲、父亲、姐妹们,以及我的医生。
在现实世界里,我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十二岁孩子。在我**次得肺炎期间,母亲的一个朋友用纸板盒为我做了一个小房子,里面有一只毛皮做的玩具老鼠,穿着一件蓝色的方格花布裙,还有小小的床罩、扶手椅、衣服以及书本;我喜欢这幢房子并拿它做游戏,尽管我早过了那个年龄。我是一个依然会和穿裙子的毛皮老鼠玩耍的女孩,努力地想要理解咳血这件事。
我母亲千般设计,万般恳求,打电话给各种各样的医生朋友,为我预约了一位著名的肺科专家。当我*终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母亲对医生说,我每走上一段楼梯都会上气不接下气。那位医生问我感觉如何。我只字未提我正在咳血的事情。我只是说:“我感觉很好。”
与此同时,我阅读一些奇怪的书籍。我读的书,无一例外都有关种族灭绝:普里莫•莱维,埃利•威塞尔,还有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手记述。对于这些书籍,我有着一种巨大的、永无止境的胃口,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死去,还因为死亡的数量惊人,包括儿童、战争、大屠杀,以及壕沟里赤裸的尸体。我一本接着一本地读这些书。我阅读时,带着某种类似于欲望的东西。我想要看到儿童死去。
我在学校的文学杂志上写过一篇故事,关于医院里的一个小女孩。故事结束时,一个声音向她呼唤:“来我这里吧,风之女。”那个声音呼唤她投降,打点行囊;它几乎是细胞层面的,这声音,女孩身体内部的某种东西在让她停止战斗,关闭功能。这让我重新想起了某些东西。死亡——这个你所抗拒、斗争,并为之恐惧的东西——是如何突然转过身来,变得诱惑难挡。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令人目眩的冥想录《论生病》(“On Being Ill”)一文中写道:“疾病常常披上爱情的伪装,并且玩着同样古怪的把戏。”
你读过那些有关士兵难以回归平民生活的故事。他们不能融入日常所关注的事务当中:是否该穿上冬衣,是否该去一个派对,是否该吃午餐。他们完全、彻底地陷在那段触目惊心的时光里;他们不停地被拉回到那时光中;他们深爱着它,就像你深爱着某个伤害了你的人:它不会放过他们。到*后,它们到底是你一生中*美好的时光,还是*糟糕的时光,已经无所谓了;所有那一切都是不相干的,并且消除殆尽:你被拉回到它之中。出院后,我的感觉就像那一样,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它。
莫里斯•桑达克在他深爱的那些人的弥留之际,会坐在他们身边,给他们画画。对一些人来说,这样做看上去似乎有悖常理或者怪异不堪,但是我凭借直觉可以完全理解。事实上,我自己正在做着某种类似的事情。
我眼下的写作是关于一些死亡的。不是那些我所爱之人的死亡,而是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的死亡。他们对于死亡特别敏感,或者说同死亡特别合拍,这些人在他们的艺术、信件、风流韵事以及睡梦中,已经解决了死亡的问题。我所选择的人,有着疯狂的表达能力,有着充沛且非凡的想象力,或者在智力上气势凶猛,他们可以把同死亡的对抗付诸文字(其中一个付诸意象)。他们所用的方法,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所不能够或者不情愿的。
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些特定的人。是本能让我被他们每一个人吸引,我感到他们的写作能量磅礴,我有一种直觉:我问自己的那些问题,他们能够回答,使它们或复杂或精炼,同时他们的死亡——就这样公之于众——会向我展示我所需要见到的东西。我选择那些对我有着某种意味的作家,他们的声音已经存在于我的脑海中,他们应对死亡的方法是极端的,要么朝着一个方向,要么朝着另一个方向:鼓舞人心,或者令人迷惑,或者非常英勇,或者异常愤怒。我选择那些拼图游戏般的人生,它们既令人困惑又吸引着我,使我感到不安和惊恐。我选择的这些人,他们的想象力更加强大,或者更加伟大,或者因为在描述上拥有更加强烈的感知力和精确性,从而提供了某种我自身不具备的可能性。我当时想:假如用语言捕获死亡的到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谁*有希望做到这一点?
当我决定好我的写作对象后,我立即开始梳理他们的作品、信件、日志、笔记、贺卡、涂鸦漫画、访谈以及手稿,以期获得他们有关死亡的那些闪着光芒、不断进化着的思想和情感。我谈话的对象有他们的儿子、女儿、情人、妻子、前妻、朋友、照看人、管家以及夜班护士。我获知他们在死亡面前,是如何选择面对或者不面对、拥抱或者躲避、与之和解或者义愤填膺,有时候兼而有之。我写下他们在医院里讲的那些笑话,或者一次让他们振作起来的理发,或者一个让他们抓起纸并写下某些东西的瞬间,发生这一切的场合都是痛苦而离奇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巨大的痛苦中,为了自己可以清晰地思考,拒绝服用任何比阿司匹林药效更强的东西,并且*终选择了自己死亡的时刻。苏珊•桑塔格则与死亡战斗到底,她相信在某种深刻的非理性层面上,她可以成为必死命运的一个例外。莫里斯•桑达克一辈子以死亡为工作对象,他的恐惧和执念通过那些插画而得以驯服,*终他在不羁的想象里,营造了一个画家的美丽梦境,让自己得到安慰。约翰•厄普代克在临死前的一个月,把脑袋靠在打字机上,因为要打出那些有关死亡的*后诗歌,对他来说太难了,他准备要放弃了。就在那一刻,他找到了完成它们的力量。狄兰•托马斯在他*后的日子里,将他的情妇丢在楼下的派对中,然后上楼同女主人睡觉。他飞奔疾驰,表现了他身上混合的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和自我毁灭的力量。如他所说:“我带着锁链歌唱,如同大海一样。”
在这些死亡之中,我们可以瞥见几分勇敢和美丽、毫无意义的极端痛苦、狂暴的自我毁灭、真正的糟糕举止,当然也有创造性的爆发、无上的奉献和准确的自我认知在闪耀,还有一些华美的幻象。这些事情,我原本无从猜想或付诸理论或有所期待,而正是在那些具体事件中,在那些诡异惊奇的细节中,在那些无心为之的评论中,其他一些更伟大的故事得以讲述和传播。
为什么桑达克想要绘画出死亡?为什么安妮•莱博维茨拍下了苏珊•桑塔格弥留之际以及死亡之后的照片?那些*后的照片充满争议,令人不安。为什么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给死去的婴儿拍照?那些婴儿被放在婴儿车里面以及人们的大腿上。为什么浪漫主义者们制作死亡面具?“我做这件事,因为我无法不做,”正如桑达克在谈及他的艺术时通常说的,“我体内某种东西失灵了。”
我认为,如果我可以在书页上捕获到一种死亡,那么我将修补或者治愈某种东西。我会感觉好一些。唯此而已。
起初,我想我正在努力理解死亡,但是后来我意识到,那是自我欺骗的一个谎言。我想要查看死亡。当我说“查看”,我指的是某种具体而书卷气的东西。其他人——胆子更大的记者——也许会前往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同即将不久于人世的人们交谈,也许会飞往多个战区,也许会采访埃博拉地区医院的众多病人,但是我查看的方式一向与众不同,更加腼腆。为了查看这个世界,我总是已经打开了一本书。
我从一个房间开始。弗洛伊德的房间,那些法式门俯视着一棵正在开花的扁桃树;厄普代克的房间非常舒适,位于马萨诸塞州丹弗斯市那家高档医院里;桑塔格*后的房间在“斯隆•凯特琳”;狄兰•托马斯的房间在圣文森特医院,里面有氧气帐篷;莫里斯•桑达克在丹伯里医院的那间“舒适护理”房。显而易见,我不属于这些房间。
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强大禁忌中的一个。舍温•努兰写道:“现代的死亡发生在现代的医院里面,在那里,死亡可以被隐藏,随之而来的器官萎缩也可以被清洗,*终打成包裹,进行现代的掩埋。我们现在可以否认的,不仅有死亡的力量,还有自然本身的力量。”我们看待死亡的方式,与之前所有世纪的人们都不一样——一个躺在四柱床上分娩的母亲,一个裹在床单里被送到大厅的婴儿,一个因猩红热而高烧不止的儿童。我们不再经常在家里面看到人们的死亡了,于是死亡成了某种我们可以忘记、可以设防的东西。但是,那份热烈或好奇依然存在。苏珊•桑塔格曾经写道:“人们对那些展示痛苦身体的照片的胃口,几乎和对那些展示裸体的照片的欲望一样强烈。”她捕获了一种对于死亡的近似于色情的感觉,那是一种去查看它的欲望。人们感到这欲望是不合法的、错误的。
对于这种查看死亡的欲望,我已经做过了很多思考。一位记者曾经问安妮•莱博维茨,为什么她给那些亲近之人——苏珊•桑塔格以及她的父亲——拍照片,在他们弥留之际和死亡以后。她回答道:“你发现自己不断返回到你所知道的事物之中。你并不确切地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并没有真正地分析它。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着我去做这件事。”
那种驱使是否有些好色,带着偷窥的意味?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病态的,或者精神错乱、趁火打劫的东西?
即使存在,这种好奇心在感觉上也是自然的。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回到过往。
我为这本书所做的工作,包括了与大量的陌生人谈论有关他们的母亲、父亲、丈夫以及亲密的朋友在弥留之际的情形。起初,我感觉内心不安,因为侵扰了别人,因为要求他们重新显露那一段幽暗的、难以安顿的时光。我写了一封又一封长长的道歉信和电子邮件,告诉他们如果不愿意同我谈话,我非常理解。“我并不想侵犯您的隐私,”我这样写道,“您如能拨冗,我感激不尽;当然您如果不愿意,我也完全理解。”我所采访的人经常一开始先安慰我;可以想象,当时我有多么尴尬。不过,我们的谈话,一再成为我这一生所有的谈话中,*非同寻常的那些。
一个死亡的故事总是私密、可怕的,让人难以举重若轻,但也许就某些方面来说,讲给一个陌生人听会容易一些。蜷缩在床上,我连着数小时打电话和若干个人交谈。有些人给我回电话或者电子邮件,告诉我他们记起的一些新事情,或者一些想法,或者他们分析出的几条观点。有些人会停止交谈,然后再开始。有些人说他们不想谈,然后说他们愿意。有些人说他们不想谈,然后一谈数小时。有一位坐在酒吧的高脚凳上,放声大哭。有一位只有在为我画肖像的时候,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交谈时,我就坐在他的画室里,努力地——差一点就失败了——保持着身体一动不动,也不做手势的状态。有些访谈慢慢变成喝茶吃饭,小酌几杯,一起参观博物馆,就这样延绵数月之久。谈话总是扣人心弦;解释的欲望,以及与一个同样深陷其中的人细加揣摩的欲望,那是无法否认的,也是一种惊喜。我所交谈的那些人,毫无保留地谈起他们的印象,内心深处的个人反应,以及那些忧虑的时刻,不过他们同时也想要谈一些没有被谈及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心神不宁地绕着一个禁忌在兜圈。
古埃及人经常阅读《亡灵书》,学习一些如何通行于阴间的实用技巧——例如如何不在阴间遭人砍头,如何拥有鳄鱼的形体,或者在进入阴间的时候不是头下脚上——但是我们没有一本《亡灵书》。
这一计划的问题是,它可能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有那么多的死亡我想潜心钻研:威廉•布莱克幸福的死亡,当时他坐在床上,看到了天使们;巴尔扎克用工作和咖啡杀死了自己;普里莫•莱维那很可能是自杀性质的摔下楼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热忱地投身于报告自己的死亡;伍尔夫沉入河中,大衣里面装着石头;卡夫卡在疗养院中的挨饿,正如他那饥饿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离开妻子,在一个火车站近旁的站长室里迎接死亡的降临;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心脏病发作。他们所有人都似乎在召唤我。
我不相信你可以学会如何死亡,或者获得智慧,或者有所准备。我在本书上所做的工作,如果有什么成绩的话,那就是证实了这种怀疑,但是,我真诚地认为你可以直面死亡,然后变得不那么害怕。
在研究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死亡肖像极其地、出人意料地安慰人心。生命之美不断溢了出来。那些为此而努力的强大灵魂,给人启发。不知何故,这些素描解放心灵,给人慰藉,令人愉悦,也许部分原因在于,我所写作的这些人一辈子过着伟大、鲜活、辉煌而多产的生活。在临终的那些瞬间里,有某种被压紧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纷至沓来,甚是浓烈。这都是美丽的,尽管死亡并不美。
莫里斯•桑达克拥有济慈的死亡面具,他将其放在一个木盒子里。他很崇拜它。他喜欢抚摸它的前额。我看到过它,非常美丽。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拥有一张死亡面具?我问自己。但是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书写一张张死亡面具。
目录
苏珊·桑塔格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约翰·厄普代克
狄兰·托马斯
莫里斯·桑达克
尾声:詹姆斯·索特
致谢
资料来源说明
节选
孩身体内部的某种东西在让她停止战斗,关闭功能。这让我重新想起了某些东西。死亡——这个你所抗拒、斗争,并为之恐惧的东西——是如何突然转过身来,变得诱惑难挡。
你读过那些有关士兵难以回归平民生活的故事。他们不能融入日常所关注的事务当中:是否该穿上冬衣,是否该去一个派对,是否该吃午餐。他们完全地、彻底地陷入在那段触目惊心的时光里;他们不停地被拉回到那时光中;他们深爱着它,就像你深爱着某个伤害了你的人:它不会放过他们的。到*后,它们到底是你一生中*美好的时光,还是*糟糕的时光,已经无所谓了;所有那一切都是不相干的,并且消除殆尽:你被拉回到它之中。
我眼下的写作,是关于一些死亡的。不是那些我所爱之人的死亡,而是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的死亡,他们对于死亡特别敏感,或者说同死亡特别合拍,这些人在他们的艺术、信件、风流韵事以及睡梦中,已经解决了死亡的问题。我所选择的人,有着疯狂的表达能力,有着充沛且非凡的想象力,或者在智力上气势凶猛,他们可以把同死亡的对抗付诸于文字(其中一个付诸于意象)。他们所用的方法,是我们中绝大多数人所不能够或者不情愿的。
假如用语言捕获死亡的到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谁*有希望做到这一点?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巨大的痛苦中,为了自己可以清晰地思考,拒绝服用任何比阿司匹林药效更强的东西,并且*终选择了自己死亡的时刻。苏珊•桑塔格则与死亡战斗到底,她相信在某种深刻的非理性层面上,她可以成为必死命运的一个例外。莫里斯•桑达克一辈子以死亡为工作对象,他的恐惧和执念通过那些插画而得以驯服,*终他在不羁的想象里,营造了一个画家的美丽梦境,让自己得到安慰。约翰•厄普代克在临死前的一个月,把脑袋靠在打字机上,因为要打出那些有关死亡的*后诗歌,对他来说太难了,他准备要放弃了。就在那一刻,他找到了完成它们的力量。狄兰•托马斯在他*后的日子里,将他的情妇丢在楼下的派对中,然后上楼同女主人睡觉。他飞奔疾驰,表现了他身上混合的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和自我毁灭的力量;如他所说:“我带着锁链歌唱,如同大海一样。”
死亡,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强大禁忌中的一个。苏珊•桑塔格曾经写道:“人们对那些展示痛苦身体的照片的胃口,几乎和对那些展示裸体的照片的欲望一样强烈。”她捕获了一种对于死亡的近似于色情的感觉,那是一种去查看它的欲望。人们感到这欲望是不合法的、错误的。
在研究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死亡肖像极其地、出人意料地安慰人心。生命之美不断溢了出来。那些为此而努力的强大灵魂,给人以启发。不知何故,这些素描解放心灵,给人慰藉,令人愉悦,部分原因在于,我所写作的这些人一辈子过着伟大、鲜活、辉煌而多产的生活。在临终的那些瞬间里,有某种被压紧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纷至沓来,甚是浓烈,这都是美丽的,尽管死亡并不美。
我在为本书所做的调查中发现,虽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后谈话”的幻想,但是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拥有。这是有关出路的幻想,有关*终净化宣泄式交流的幻想,它罕有实现的机会,因为那相伴一生的刺痛,或者矜持,或者愤怒,依然还在那里,因为死亡的紧迫并没有疏浚一生的泥沼,也没有消除障碍,或者化冲突于无形,或者强迫我们去谈论什么是重要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能够做到。
“过去这些天萦绕在他脑海里的大限将至的感觉,已经凝结成现实了,就像云朵凝结成人们所需的雨水。有一种轻松感,一种放松感,伴随着痛苦而来:你生命中大块的部分,已经被剥夺一空了,突然变得可有可无了。你变成了简简单单的一件人体行李,等待着被运送到他人之手。”
作者简介
凯蒂•洛芙(Katie Roiphe),美国作家、记者。普林斯顿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任教于纽约大学。作品散见于《纽约时报》《巴黎评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各大媒体。她的写作被用来与乔治•奥威尔相比,“精当、优雅,力道惊人,是散文写作的典范”。1994年处女作《次日早晨:性、恐惧与女性主义》(The Morning After: Sex, Fear, and Feminism)因其中关于校园强奸的观点而引起巨大关注。她的母亲是著名女性主义者,安•洛芙。
-

大宋宰相王安石
¥29.7¥55.0 -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10.2¥29.0 -

毛姆自传
¥19.9¥38.0 -

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靳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
¥17.3¥36.0 -

水浒人物之最
¥22.0¥49.0 -

天地悠悠-胡宗南夫人回忆录
¥12.9¥36.0 -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26.8¥48.0 -

瞧这个人
¥11.5¥26.8 -

词人纳兰:西风独自凉
¥20.0¥48.0 -

梁启超传-最新修订精编精校版
¥14.3¥29.8 -

三毛传
¥13.7¥38.0 -

项城袁氏(精)
¥30.2¥52.0 -

鲁迅传
¥16.3¥38.0 -

宗庆后:有一种人生叫“大器晚成”
¥24.9¥58.0 -

梦里不知身是客 : 李煜词传
¥12.6¥36.0 -

人生一直在告别
¥18.2¥42.0 -

名家经典:苏东坡传(精装)
¥27.4¥56.0 -

美在天真-新凤霞自述
¥9.2¥28.0 -

别样风景-张乐平(八品)
¥30.1¥65.0 -

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16.3¥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