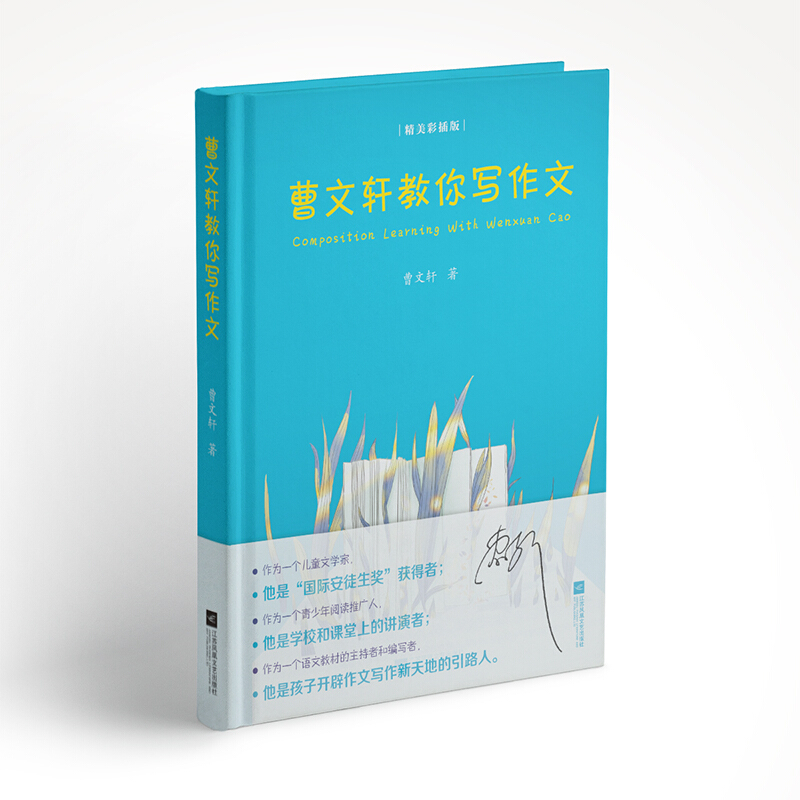
包邮曹文轩教你写作文

温馨提示:5折以下图书主要为出版社尾货,大部分为全新(有塑封/无塑封),个别图书品相8-9成新、切口有划线标记、光盘等附件不全详细品相说明>>
- ISBN:9787559428301
- 装帧:一般轻型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9cm
- 页数:190页
- 出版时间:2018-10-01
- 条形码:9787559428301 ; 978-7-5594-2830-1
本书特色
语文教材编写者、“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 为孩子读书写作指点迷津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家,他是“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作为一个青少年阅读推广人,他是学校和课堂上的讲演者;作为一个语文教材的主持者和编写者,他是孩子开辟作文写作新天地的引路人。 ★ 大师级别的写作课★ 全方位地写作、阅读指导★ 辅以精美彩插、契合曹文轩的纯美文学 《曹文轩教你写作文》不同于一般的写作教学,曹文轩先生从自己写作的经验出发,从对语文教学、学生阅读的实际了解程度和介入程度出发,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表达了阅读与写作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写作应该坚持怎样的态度,又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实现长篇优秀作文的产生。“好文章在于折腾”,曹文轩从实操层面讲述如何将一句话扩展为一段话,进而成为一篇“有戏”的作文。 ★从实操层面分析写作的动力和方法;★解读阅读对写作的根基性作用;★纯美的文学观、端庄的写作态度。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几十篇曹文轩先生关于如何写作、如何教写作, 在他看来, 文章与世界上的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门技艺一样, 都是可教的。他以自己多年来与中小学语文教育、作文写作牵连的经验, 将自己有关写作的思考总结出来, 告诉读者, 写作并非只有一条途径, 找到适合自己的, 乃是根本。
目录
写作:另一种造屋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文字建造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也许我如此喜欢写作,*重要的原因是它满足了我天生向往和渴望自由的欲望。
作文与“自己的”生活
不要总怀疑自己没有生活。你既然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且又是一个天性不安分的少年,你一定会有生活——难道你没有发现你就在生活之中吗?
好文章在于折腾
读书要读有文脉的书;未经凝视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创造的自由是无边无际的;好文章离不开折腾;一本好书就是一轮太阳。
端庄的写作姿态——《蜻蜓眼》创作谈
也许是我对故事反应迟钝,也许是我的“深思熟虑”,我通常的状态就是这样:很难做到逮到一个故事马上就将它变为文字。有的故事,我只能取端庄的写作姿态,用庄重的语调去书写。
我的作品
我愿意我的作品永远具有诗性,与诗性相关的词有“意境”“气韵”“情调”“雅兴”等。我喜欢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些东西。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贯注。
阅读的意义
阅读是一把弓,写作是一支箭,没有这个弓,哪有这支箭?弓的力量越大,这个箭就射得越远。写作灵感从哪里来?灵感,就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突然爆发。
阅读教学还是语文教学?
我们中国人早就明白了字词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我们都十分热衷于、擅长于咬文嚼字。加之汉字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字,它的每一个字本身就是存在着某一对象的口号。因此,细读字词对于孩子学习语文而言,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什么样的书值得看
如果你看到某本书,觉得这个句子不错,那个词不错,只有一个段子你很想抄到笔记本上,这本书就是一本好书了。
培养审美的能力
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每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苦难。面对苦难,我们应抱有感恩之心。
解读四个成语
文学不是比力气,而是比潇洒,比智慧。
“读好书”与“把书读好”
人生的经验越厚实,书就读得越好。
文学何为?
在于净化灵魂,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文学的变与不变
一个没有知识浸润,没有知识武装的大脑,是不可能有灵感的,也不可能有发现财富的眼力的。
圣坛
也许有一天,我会厌倦北大的讲坛,但至少现在还恋着。恋它一天,就会有一天的神圣感。
跋
节选
写作:另一种造屋 我为什么要——或者说我为什么喜欢写作?写作时,我感受到的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一直在试图进行描述。但各种描述,都难以令我满意。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确切的、理想的表达:写作便是建造房屋。 是的,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它满足了我造屋的欲望,满足了我接受屋子的庇荫而享受幸福和愉悦的欲求。 我在写作,无休止地写作;我在造屋,无休止地在造屋。 当我对此“劳作”细究,进行无穷追问时,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造屋的情结,区别只是造屋的方式不一样罢了——我是在用文字造屋:造屋情结与生俱来,而此情结又来自人类*古老的欲望。 记得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杂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书柜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一座屋子里,有很多空间分割,各有各的功能。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严重的是,可能有一个霸道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愿望未能得到满足,恼了,突然一脚踩烂了马上就要竣工的屋子。每逢这样的情况,其他孩子也许不理那个孩子了,还骂他几句很难听的;也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打斗,直打得鼻青脸肿“哇哇”地哭。无论哪一方,都觉得事情很重大,仿佛那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屋子。无论是希望屋子好好地保留在树下的,还是肆意要毁坏屋子的,完全把这件事看成了大事。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庆贺的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就有一个孩子在过了一阵子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杂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唉!”就搬砖去——哪里有什么砖,只是虚拟的一个空空的动作,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这个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呢——小的,不,大的,是我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很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了——它很大很大,比挂在天空中央的太阳大好几倍。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支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穹顶上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不时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地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直到一天夜里或是一个下午,一场倾盆大雨将它冲刷得了无痕迹。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那时,除了积木,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玩具了。一度,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造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大小小、形状不一、颜色各异的积木,建造了一座又一座屋子。与在田野上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房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盖一座与之前不一样的屋子。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总有罢手的时候,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现在我知道了,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类祖先遗存下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堂美术课上,老师往往总是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再用几条长长短短、横着竖着的直线画一座屋子的原因。 屋子就是家。 屋子的出现,跟人类对家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落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终于长大时,儿时的造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愈加强烈。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建造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去的地方——文字屋。而此时,我会发现,那个由钢筋水泥筑成的物质之家,其实只能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还有,也许我如此喜欢写作——造屋,*重要的原因是它满足了我天生想往和渴求自由的欲望。 这里所说的自由,与政治无关。即使*民主的制度,实际上也无法满足我们自由的欲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参与者的萨特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听上去让人感到非常刺耳,甚至令人感到极大的不快。他居然在人们欢庆解放的时候说:“我们从来没有拥有比在德国占领期更多的自由。”他曾经是一个革命者,他当然不是在赞美纳粹,而是在揭示这样一个铁的事实:这种自由,是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都无法给予的。在将自由作为一种癖好、作为生命追求的萨特看来,这种自由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他找到了一种走向自由的途径:写作——造屋。 人类社会如果要得以正常运转,就必须讲义务和法则,就必须接受无数条条框框的限制。而义务、法则、条条框框却是和人的自由天性相悖的。越是精致、严密的社会,越要讲义务和法则。因此,现代文明并不能解决自由的问题。但自由的欲望,是天赋予的,那么它便是合理的,是无可厚非的。对立将是永恒的。智慧的人类找到了许多平衡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写作。你可以调动文字的千军万马。你可以将文字视作葱茏草木,使荒漠不再。你可以将文字视作鸽群,放飞无边无际的天空。你需要田野,于是就有了田野。你需要谷仓,于是就有了谷仓。文字无所不能。 作为一种符号,文字本是一一对应这个世界的。有山,于是我们就有了“山”这个符号。有河,于是我们就有了“河”这个符号。但天长日久,许多符号所代表的对象已不复存在,但这些符号还在,我们依然一如往常地使用着。另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叙述,常常是一种回忆性质的。我们在说“一棵绿色的小树苗”这句话时,并不是在用眼睛看着它,用手抓着它的情况下说的。事实上,我们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在用语言复述我们的身体早已离开的现场、早已离开的时间和空间。如果这样做是非法的,你就无权在从巴黎回到北京后,向你的友人叙说卢浮宫——除非你将卢浮宫背到北京。而这样要求显然是愚蠢的。还有,我们要看到语言的活性结构,一个“大”字,可以用它来形容一只与较小的蚂蚁相比而显得较大的蚂蚁——大蚂蚁,又可以用它来形容一座白云缭绕的山——大山。一个个独立的符号可以在一定的语法之下,进行无穷无尽的组合。所有这一切都在向我们诉说一个事实:语言早已离开现实,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个王国的本质是自由。而这正契合了我们的自由欲望。这个王国有它的契约,但我们可以在这一契约之下,获得广阔的自由。写作,让我们的灵魂得以自由翱翔,让我们自由之精神得以光芒四射,让我们自由向往的心灵得以安顿。 为自由而写作,而写作可以使你自由。因为屋子属于你,是你的空间。你可以在你构造的空间中让自己的心扉完全打开,让感情得以充分抒发,让你的创造力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造屋本身就会让你领略自由的快意。房子坐落在何处,是何种风格的屋子,一切,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当屋子终于按照你的心思矗立在你的眼前时,你的快意一定是无边无际的。那时,你定会对自由顶礼膜拜。 造屋,自然又是一次审美的历程。房子,是你美学的产物,又是你审美的对象。你面对着它——不仅是外部,还有内部,它的造型、它的结构、它的气韵、它与自然的完美合一,会使你自然而然地进入审美的状态。你在一次又一次的审美过程中又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再后来,当我意识到了我所造的屋子不仅仅是属于我的,而且是属于任何一个愿意亲近它的孩子时,我完成了一次理念和境界的蜕变与升华。再写作,再造屋,许多时候我忘记了它们与我的个人关系,而只是在想着它们与孩子——成千上万的孩子的关系。我越来越明确自己的职责:我是在为孩子写作,在为孩子造屋。我开始变得认真、庄严,并感到神圣。我对每一座屋子的建造,殚精竭虑,严格到苛求。我必须为他们建造这世界上*好、*经得起审美的屋子,虽然我知道难以做到,但我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去做。 孩子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需要屋子的庇护。当狂风暴雨袭击他们时,他们需要屋子。天寒地冻的冬季,这屋子里生着火炉。酷暑难熬的夏日,四面窗户开着,凉风习习。黑夜降临,当恐怖像雾在荒野中升腾时,屋子会让他们无所畏惧。这屋子里,不仅有温床、美食,还有许多好玩的开发心智的器物。有高高矮矮的书柜,屋子乃为书,而这些书为书中之书。它们会净化他们的灵魂,会教他们如何做人。它们犹如一艘船,渡他们去彼岸;它们犹如一盏灯,导他们去远方。 对于我而言,*大的希望,也是*大的幸福,就是当他们长大离开这些屋子数年后,会时不时地回忆起曾经温暖过、庇护过他们的屋子,而那时,正老去的他们居然在回忆这些屋子时有了一种乡愁——对,乡愁那样的感觉。这在我看来,就是我写作——造屋的圆满。 生命不息,造屋不止。既是为我自己,更是为那些总让我牵挂、感到悲悯的孩子们。
作者简介
曹文轩,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是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作品《红瓦》《草房子》《根鸟》《细米》《天瓢》《青铜葵花》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分别被译为英、法、德、日、韩等文字。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2017年获得2016-2017“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其余国内外**学术奖、文学奖四十余种,包括国家图书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奖大奖等奖项。
-

燕子来时
¥9.6¥25.0 -

谈文学
¥7.0¥20.0 -

老人与海
¥6.9¥28.0 -

宇宙从何而来
¥16.8¥52.8 -

学习.就是找对方法
¥11.5¥35.0 -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窄门
¥11.5¥31.0 -

骑鹅旅行记
¥5.8¥13.8 -

朝花夕拾
¥5.2¥16.8 -

悉达多-一首印度的诗
¥18.6¥32.0 -

聊斋志异
¥8.2¥26.8 -

汤姆索亚历险记
¥13.7¥39.8 -

道德经
¥16.4¥48.0 -

飘
¥15.0¥39.0 -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精装)
¥20.6¥43.8 -

八十天环游地球
¥12.9¥39.8 -
![艺术卷[先秦-唐]-图解中国文化](/Content/images/nopic.jpg)
艺术卷[先秦-唐]-图解中国文化
¥5.9¥19.8 -

城堡
¥17.6¥45.0 -

写作课
¥17.1¥46.0 -

想念地坛
¥13.2¥36.0 -

三国演义-(全二册)
¥17.5¥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