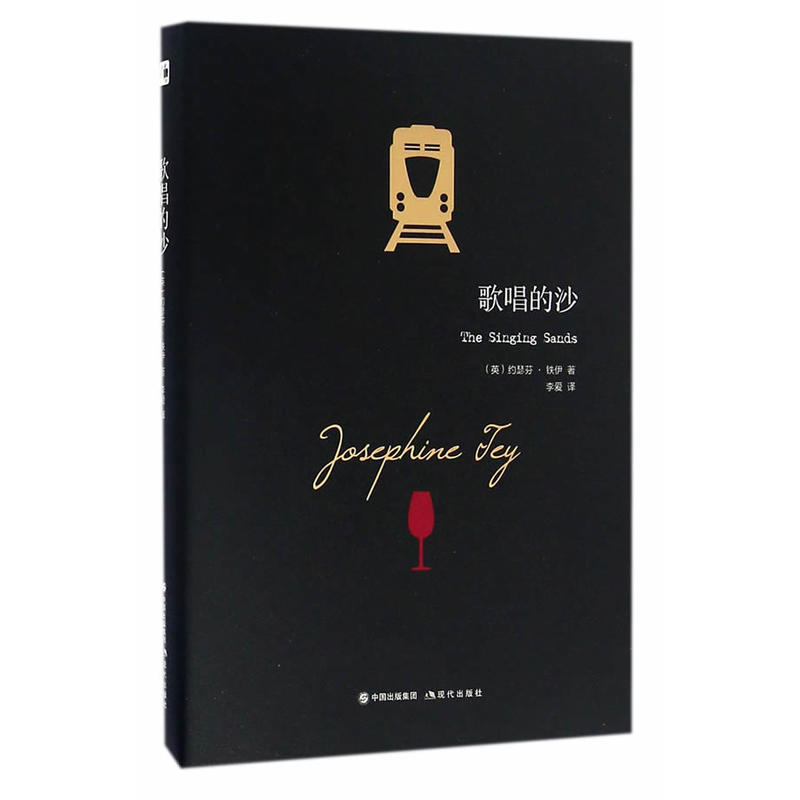
4.6分
歌唱的沙
推理史辉煌的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之一约瑟芬·铁伊作品

温馨提示:5折以下图书主要为出版社尾货,大部分为全新(有塑封/无塑封),个别图书品相8-9成新、切口有划线标记、光盘等附件不全详细品相说明>>
- ISBN:9787514350432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205
- 出版时间:2017-01-01
- 条形码:9787514350432 ; 978-7-5143-5043-2
本书特色
★ “一生中没有任何失败作品的大师”——约瑟芬·铁伊★ 侦探小说史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 与阿加莎·克里斯蒂齐名 却相爱相杀★ 特立独行,心思诡巧
内容简介
本在休假的格兰特探长意外被卷入命案!
醉死在火车上的年轻人。
死者生前留在残破报纸上的涂鸦。
究竟是死亡信息( dying message)还是另有所指?
追查证据的历程异常辛苦,眼看着*后一丝线索都中断了的时候,凶手却自己招认了……
节选
那是三月的一个早晨,六点来钟,天还未亮。一列长长的火车侧身驶过布满灯光的调车场,它咔嗒咔嗒缓缓通过铁轨道岔,又进出于信号房的灯火中。在信号桥上,一盏翠绿的灯嵌在宝红色的灯中,火车从桥下通过后便朝拱形下静候的站台驶去。灰色的站台上空无一人,异常荒凉。
伦敦邮政列车驶向了它旅程的终点。
昨夜的尤斯顿站被甩在五百英里漆黑的铁轨后。一路而来,历经五百英里月下的田野和沉睡的村庄,漆黑的城镇和不眠的熔炉,雨水和霜雾,阵雪和洪水,隧道和高架桥。此刻,在这三月阴冷的早晨,六点时分,渐渐显露的丘陵环绕着火车悄然驶了过来,驶向长途奔袭后的休憩。火车到站时,在那长而拥挤的人群中,除了一个人,所有人都舒了口气。
在舒了口气的人群中至少有两个人欣喜若狂。其中一位是旅客,另一位是列车员。旅客名叫艾伦?格兰特,列车员名叫默多?加
拉赫。
默多?加拉赫是卧铺车厢的乘务员,也是瑟索和托基之间*让人痛恨的活物。二十年来,默多恐吓勒索旅客,让他们进贡,孝敬他些钱财,还不得声张。人们还会自发地“称颂”他。默多被各处头等车厢的旅客称为“酸奶”(当他那张令人厌恶的嘴脸从尤斯顿蒸汽弥漫的昏暗车站显现时,他们便会说:“哦,上帝,是老酸奶!”)。三等车厢旅客的叫法则各种各样,不过都很生动形象。只有三个人曾治服过默多:一位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牧牛工,一位是女王私人卡梅伦高地人团的一等兵,还有一位是三等车厢一个不知名的伦敦女人。这位矮个儿女人威胁说,要用柠檬水瓶打烂他的秃头。无论是地位还是成就都无法影响默多:他恨这个,怨那个,却很怕肉体的疼痛。
二十年来,默多一直碌碌无为。这份工作,他还没做到一周就厌倦了,但发现是个肥差,便留下来捞点油水。如果你从他那儿要了份上午茶,那么茶是淡的,饼干是软的,糖是脏的,托盘滴着水,连茶匙也没有,但当默多来收盘子时,你曾演练过的抗议言辞,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只是偶尔有一位类似海军元帅的人物,才会大胆提出意见,但普通人都是付了钱,一笑了之。二十年来,旅客们被恐吓、被勒索,身心疲惫却只能给钱,而默多就只管敛财。现在,他是达农一栋别墅的主人,在格拉斯哥拥有一家炸鱼连锁店,还拥有大笔的银行存款。几年前他就该退休了,可是一想到会失去全部的津贴,他就无法忍受,所以便在这无聊的岗位上再忍耐些日子。为了扯平自己的损失,除非旅客自己要求,他都不会费心劳力地提供早茶。有时,他要是很困,干脆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每次到达旅程终点时,他便像个算出刑期就要所剩无几的人一样,如释重负,欢呼雀跃。
艾伦?格兰特看着调车场的灯光浮在满是蒸汽的窗户上,从眼前划过,听着车轮咔嗒咔嗒驶过铁轨道岔,发出轻柔的声音。他满心欢喜,因为旅程的终点即是夜晚煎熬的结束。这一夜,格兰特都消磨在努力地克制自己不去打开通往走廊的门。他十分清醒地躺在昂贵的床垫上,一小时一小时地冒着汗。他之所以冒汗不是因为卧铺房间太热——空调工作得出奇地好——而是因为这个房间相当于“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唉,可悲!唉,可恶!唉,可耻!在普通人看来,卧铺房间仅仅是一个整齐的小屋,里面有一个铺位,一个洗手盆,一面镜子,各种大小的行李架,提供的可展开可收起的架子,能存放贵重物品的精美小盒子,还有一个挂表的挂钩。但是,对于一个新入住者,一个悲伤失落、焦虑不安的新入住者,它就是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
医生称之为劳累过度。
“放松,浏览一会儿书刊。”医生温坡?斯特里特一边说一边把一条优雅的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并欣赏着跷起的二郎腿。
格兰特无法想象让自己放松,他把浏览视为一个令人憎恶的词语,一种让人鄙视的消遣。浏览,一张堆积如山的桌子,一种漫无目的地满足动物的欲望。浏览,确实如此!这个词语就连声音都是种罪过。一种枯燥乏味。
“你有什么爱好吗?”医生问道,并将欣赏的目光移到了他的鞋上。
格兰特简短地说道:“没有。”
“假期时你做什么?”
“钓鱼。”
“钓鱼?”心理医生说着便收回了他自恋的眼神,“你不认为那是一个爱好吗?”
“当然不是。”
“那么你说它是什么?”
“某种介于体育和信仰之间的东西。”
温坡?斯特里特面带微笑看着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向他保证,治愈只是时间问题。时间和放松。
好吧,至少昨晚他尽量没有打开门。但是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让他精疲力竭,成了个行尸走肉的人。医生曾说:“别和它对着干。如果想去户外,就去。”但昨晚要是开了门,那将意味着致命的一击,他会感到康复无望。那将是对非理性力量的无条件投降。所以他躺在那儿,任汗直流,但是房门一直紧闭。
不过现在,在这清晨失意的黑暗中,在这莫名阴冷的黑暗中,他就像是一个丧失了德行的人。“我想女人在漫长分娩之后的感觉就是如此吧。”他用温坡?斯特里特解释和赞许过的从根本上无所谓的心境想。“但是,至少她们拥有了一个可以用来炫耀的孩子,而我得到了什么?”
他想,是他的尊严。这尊严就是他没有打开门,也没有任何理由打开。哦,上帝!
现在他打开了门,却极不情愿,他意识到了这种不情愿的讽刺意味。他不愿面对早晨和生活,真想把自己扔回凌乱的床上,睡啊睡啊睡啊。
由于酸奶不提供任何服务,格兰特提起两个行李箱,把一捆未读的期刊夹在胳膊下,走进了走廊里。给得起小费出手阔绰的人,他们的行李已经堵住了走廊尽头的小通过台,几乎堵到了车顶,连门都要看不见了。格兰特便朝头等车厢的第二节移动,但前方尽头处也堆放着齐腰高特权者的障碍物,他只好开始沿着走廊向车厢后面的门走去。与此同时,酸奶本人从远端他那间小屋走出来,去确认B7的旅客知道就要抵达终点站了。这是B7或其他任何旅客公认的权利,以便在火车抵达后从容地下车,但是当某个人在睡觉的时候,酸奶当然不想闲逛。所以他大声敲打着B7的房门,然后走了进去。
当格兰特走到敞开的门边时,酸奶正扯着B7的衣袖猛摇,压抑着愤怒说道:“快,先生,快点!就要进站了。”而B7则衣着整齐地躺在铺位上。
格兰特的身影遮蔽了车门,酸奶抬起头看着他,厌恶地说道:“喝得烂醉如泥!”
格兰特注意到这个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威士忌气味,浓到可以立起一根拐杖。他整理了一下这个男人的夹克,还不自觉地捡起了一张报纸,这是酸奶摇晃B7时掉到了地上。
格兰特说道:“你看着他时,难道没有认出是个死人吗?”透过昏沉沉的倦意,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看着他时,难道没有认出是个死人吗?好像这是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你看着它时,难道没有认出是迎春花吗?你看着它时,难道没有认出是鲁本的作品吗?你难道没有认出是阿尔伯特纪念碑吗——
“死了!”酸奶用一种近乎咆哮的声音说道,“他不能死!我要下班了。”
格兰特从他置身事外的立场上注意到,这一切对于加拉赫先生那该死的灵魂意味着什么。某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温暖和感觉,毫无知觉,所有这些,在该死的加拉赫眼里只是意味着他要晚点下班。
酸奶说道:“我该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有人酗酒死在了我的车厢里!我该怎么办?”
“当然是报警。”格兰特说道。他再一次意识到生活所具有的快感。酸奶终于遇见了他的对手,这给了他一种扭曲恐怖的快感:这个男人没有给他小费,这个男人给他带来的麻烦比二十年铁路服务中任何人带来的都要多。
他又看了眼那凌乱黑发下年轻的面庞,便沿着走廊走了。死人不是他的职责。在他的工作时间,充斥着死人,虽然这无法挽回的事还是会让他心头一紧,但死亡已不再让他震惊。
车轮的咔嗒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火车进站时所发出的悠长而又低沉空洞的声音。格兰特摇下车窗,看着站台的灰色缎带向后驶去。一阵寒意像是有人朝他脸上来了一拳,让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他把两个行李箱放在站台上,就像被诅咒的猴子一样冻得打战。他站在那儿,怨恨地想到,希望自己可以暂时死去。在他内心幽暗的深处,他知道,在冬季早晨六点来钟,能站在这站台上,因寒冷和紧张而颤抖,也是件幸事,是还活着的必然结果。但是,哦,如果可以暂时死去,在舒服时活过来,该多好!
“先生,去旅馆吗?”搬运工说道。“去,我看到推车会自己带过去。”
他蹒跚地走上阶梯,穿过天桥。天桥的木板听起来就像鼓声,他的脚下是空的,从下面翻滚起巨大而又猛烈的蒸汽包围着他,铿锵的噪声和回声从黑洞洞的拱顶里发出。他想,关于地狱人们都错了。地狱不是一个受油煎之刑、温暖舒适的地方,地狱是一个有着回音的极寒之洞,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一个漆黑的只有回音的不毛之地。地狱的精髓都集中在了这冬日的早晨,一个自我厌恶的人经历了彻夜未眠。
他走入一个空旷的庭院,突如其来的宁静抚慰着他。黑夜虽然寒冷却也清澈。一抹灰色预示着清晨的来临,清澈的空气中,一股雪的气息诉说着此处就是高地。不久之后,当天亮的时候,汤米就会来旅馆接他,然后一起驾车驶入干净的高地乡间,驶入宽广辽阔、亘古不变、无欲无求的高地世界。那里的人们生于此、死于此,总之没有谁家会大门紧闭,因为那太麻烦。
旅馆的餐厅里,只有一边的灯亮着,没有灯光的幽暗处,整齐地摆着几排没有铺台布的桌子。这时他才想到,以前还从未见过餐馆的桌子没有铺台布。撤掉白色盔甲的桌子,真是很寒碜落魄,就像服务员没有穿衬衣的硬前胸一样。
一个小孩儿身穿黑色的制服套裙和绿色的绣花毛衣,把脑袋抵着纱门转圈,看见格兰特时好像被吓了一跳。他问道有什么早餐。她拉响了鸣铃,以示开餐,从餐柜上取了一个调味瓶放在他前面的桌布上。
“我去替你找玛丽。”她贴心地说道,便朝纱门后走去。
他想,餐馆服务已经失去了它的拘谨古板和光鲜亮丽,变成了家庭主妇所说的简单枯燥。不过,偶尔一句“找玛丽”倒也弥补了绣花毛衣和类似的不得体。
玛丽是个丰满稳重的人,如果奶妈没有过时,她肯定是个奶妈。在她的服务下,格兰特感到,自己就像个孩子在仁慈的长辈面前放松了下来。他苦涩地想着,这倒也是件好事,在他如此需要安慰的时候,一位胖乎乎的餐厅女服务员给予了他。
格兰特吃了她放在面前的东西后,开始感觉好些了。不一会儿,她过来挪走了切片面包,在原位放了盘早餐面包卷。
她说道:“给你的大面包卷是刚做好的。这东西如今是有点糟,完全没有嚼劲,不过总好过那些面包。”
她把果酱推近他的手边,看他是否还需要来些牛奶,随后又离开了。格兰特原本不打算再吃了,但还是拿了块大面包卷抹上了黄油,又从昨晚的书堆中拿了份没读过的报纸。他拿到手里的是一份伦敦的晚报,他就像不认识似的满脸疑惑地看着它。他买过晚报吗?通常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肯定就读过晚报了。怎么会在晚上七点再买一份?难道买晚报已经成了他的条件反射行为,就像刷牙一样无意识?亮着灯的书报亭即是晚报。是这样发生的吗?
这是一份《信号报》,即早晨《号角报》的下午版。格兰特又看了遍昨天下午就曾了解过的标题,思量着它们在本质上还真是一成不变。这是昨天的报纸,和去年的抑或下个月的报纸如出一辙。标题永远和现在看到的一样:内阁争论,梅达谷里金发碧眼的死尸,关税诉讼,抢劫案,美国演员的到来,道路事故。他把这份报纸挪开,可当伸手去拿下一份报纸时,却注意到,在*新消息的空白处,有用铅笔写的潦草字迹。为了能够看清有人在那计算着什么,他把报纸倒转过来,但好像根本不是某个送报人匆忙地计算差额,而是有人想要写诗。这是一首原创诗,而不是去回忆一些早已被人熟知的诗句。这首诗写得断断续续,事实上,作者已经把两句缺失的诗句标上了音步数量。在格兰特六年级时,作为*好的十四行诗人,他就已经用过这种技巧了。
但这次的诗不是他写的。
忽然,格兰特明白了这份报纸是从何而来。他取得这份报纸的行为比买晚报更无意识。当它滑落到卧铺房间B7的地面上时,他捡了起来,并将它和其他报刊一起夹在了胳膊下。他的意识,或者说经历昨夜后尽可能还有的意识,都集中于酸奶正在让一个无助的男人衣冠不整。他唯一故意的行为,就是用拉直那个男人的夹克来谴责酸奶,为此他需要一只手,所以那份报纸与其他报刊一起夹在了胳膊下。
那么这位留着凌乱黑发、长着轻率眉毛的年轻人是一位诗人,是吗?
格兰特感兴趣地看着那铅笔字。看起来,作者是在努力创作一首八行诗,但是没能想出第五行和第六行。所以潦草地写道:
说话的兽,
停滞的河,
行走的石,
歌唱的沙。
……
……
守卫去往
天堂的路。
平心而论,这首诗很奇怪。震颤性谵妄的前兆吗?
具有这样一张非常独特面庞的主人,在他酗酒后的酒精幻想中看见了非同寻常的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世界在这个长着轻率眉毛的年轻人眼里,会变得天翻地覆。被如此可怕的怪物所守卫的天堂是什么?遗忘?他为什么如此需要遗忘,它代表着他的天堂吗?他准备从不断靠近的恐惧中逃跑吗?
格兰特吃着没有嚼劲、刚出炉的大面包卷,思考着这个问题。笔迹虽显稚气,但一点也不颤抖,看起来是一个字迹稚气的成年人所写,不是因为他的协调性不好,而是因为他还不够成熟。从本质上看,他仍然是采用孩童*初书写时的方式。首字母的字形也证实了这一看法,那纯粹就是习字簿的字形。奇怪,一个如此个性的人却无意将自己的个性融入他的字形中。确实,很少有人不依自己的喜好、不按自己的潜意识需要来调整习字簿的字形。
这么多年,格兰特的一个小兴趣就是研究字迹,而且在工作中,他发现长期的研究结果很实用。当然,偶尔他的推论也会让人失望,比如一个将受害者用酸液溶解的连环杀手,结果却写了一手好字,只是有极强的逻辑性,这毕竟还是有足够的合理性。不过总体来说,笔迹提供了辨识一个人很好的标志。一般来看,一个人一直使用学生字体写信有两个原因:要么他不太聪明,要么他很少写字,没有机会把个性融入笔迹里。
考虑到他能很聪明地用语言将天堂之门那梦魇似的危险表达出来,所以很明显,这个字迹稚气的年轻人不是缺乏个性。他的个性——他的活力和兴趣——投入了其他事情。
什么事情?积极的事情,外部的事情。写一些像这样的留言:“坎伯兰郡的酒吧,6:45见面,托尼”,或是填写日志。
但是,他是个足以内省的人,会去分析和用语言表达通往梦想国度天堂的路,足以内省地置身事外地观察,想要去记录。
格兰特沉浸在一种舒心温暖的恍惚中,嚼着面包思考着。他注意到n和m的顶部紧紧相连。他是一个骗子?或只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长着这样眉毛的男人,他的字迹透出一种奇怪的谨慎特征。一个人的面容所蕴含的意思有多少决定于眉毛,是很不可思议的。眉毛的角度变换一下,整体效果就不一样。电影巨头从巴勒姆和麦斯威山带来两个漂亮的小姑娘,然后将她们的眉毛刮去,重新画一对,她们立刻变成来自鄂本斯克和托本斯克的神秘人物。漫画家泰伯曾告诉他,欧尼?普赖斯就是由于他的眉毛而失去了成为首相的机会。泰伯喝着啤酒,眨着像猫头鹰般的眼睛说:“他们不喜欢他的眉毛。为什么?不要问我。我只画画。或者因为看起来脾气暴躁。他们不喜欢脾气暴躁的人。不相信他。但就因为这样他失去了这个机会,相信我。他的眉毛。他们不喜欢。”脾气暴躁的眉毛,骄傲自大的眉毛,忧心忡忡的眉毛—— 一对眉毛赋予了一张脸主要的基调。那对倾斜的黑色眉毛,让这张躺在枕头上苍白消瘦的脸显得如此轻率,而在死亡的时候更是如此。
好吧,当这个男人写下这些诗句时,他还没有喝醉,至少是清醒的。这个醉汉所寻找的天堂,在B7卧铺房间里的遗忘——充满酒气的空气,皱了的毯子,地板上滚动的空酒瓶,架子上打翻的玻璃杯,但是当他描绘这通往天堂之路时,他还没有喝醉。
歌唱的沙。
古怪,但不知何故,很吸引人。
歌唱的沙。某个地方确实有歌唱的沙吗?一种模糊而又熟悉的声音。歌唱的沙。当你走在沙上,它们会在你的脚下哭泣。或者是风,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一个男人的前臂伸到格兰特的面前,花格呢的袖子,并从盘里拿了一块大面包卷。
汤米拉出椅子坐了下来,说道:“你看起来正自得其乐。”他撕开面包,抹上黄油。“如今,这东西完全没有嚼劲。我小的时候,用牙咬,向外拉。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你的牙还是面包。如果你的牙赢了,真值得一尝,满嘴美味的面粉和酵母会持续几分钟。现在它们再也尝不到了,你可以把这东西对折,然后整个放到嘴里,完全没有任何噎着的危险。”
格兰特怀着喜爱之情静静地看着他。他想,没有什么关系会如此亲密,亲密地把你和一个男人绑在一起,他和你同住一间预备学校的宿舍,然后一起上公学。但是,每当再次遇见汤米时,他就会想起预备学校。或许因为在本质上,这张精力充沛、棕色透着红的面庞和一双又圆又单纯的蓝眼睛,都和曾经歪歪扭扭系着纽扣的褐红色夹克上的面庞一样。汤米常常会满不在乎地系着夹克上的纽扣。
汤米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问一些客套话,例如旅途和健康问题。当然,劳拉也不会。他们接纳眼前的他,就好像他已经在这待了一段时间,好像他根本就从未离开过,还是此前的来访。这种非常轻松的氛围让人沉浸其中。
“劳拉怎么样?”
“很好,长胖了一点。反正她是这么说的。我是没有看出来。我一直都不喜欢清瘦骨感的女人。”
曾有一段日子,那时他们都才二十岁,格兰特曾想过要娶他的表妹劳拉,他确信,劳拉也曾想要嫁给他。但在一切还未倾诉之前,魔法就消失了,他们又回到了原来友爱的关系。那魔法存在于高地令人陶醉的漫长夏日,存在于山间清晨的松针气息,存在于无尽暮色中三叶草香甜的气味。对于格兰特而言,表妹劳拉往往就是他快乐暑假的一部分,他们一起在溪里从划桨到钓鱼,他们一起**次漫步在拉瑞格,**次站在布雷里克的山顶。但直到那个夏天,他们青春期结束的时候,快乐才转化成劳拉,整个夏天都聚焦在劳拉?格兰特这个人身上。每当他想起那个夏天,心里还是会泛起一阵涟漪。一个明亮完美、色彩斑斓的气泡,因为秘而不宣,那个气泡永远也不会破裂。它依然明亮完美、色彩斑斓、泰然自若。他们又继续各奔东西,认识不同的人。事实上,劳拉带着小孩儿玩跳房子似的无所谓,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后来,格兰特带她参加了毕业时的舞会,她遇见了汤米?兰金。事情就是这样。
汤米问道:“火车站出了什么事,乱哄哄的?还有救护车什么的。”
“火车上死了一个人,我想就是这事。”
汤米“噢”了一声就抛之脑后了,用一种恭喜的方式补充道:“这次不是你的葬礼。”
“不是啊,谢天谢地,不是我的葬礼。”
“人们会在维多利亚地区(曾是伦敦警察厅的所在地——译者注)缅怀你的。”
“我可不信。”
汤米说:“玛丽,要一壶上好的浓茶。”他用手指尖鄙视地敲击着盛面包卷的盘子。“再来两盘这种便宜货。”他转过脸,像孩子一样认真地盯着格兰特说:“他们少了一个人,肯定会想你的,是吧?”
格兰特喘了口气,差点发出几个月来的一次大笑。汤米对总部表达了慰问,不是因为失去了他的才华,而是少了他这个人。他这位“家人”的态度和他长官那职业化的反应大体一样。“因病离开!”布莱斯说道,他用大象似的小眼打量着格兰特看起来健康的身体,然后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好吧,好吧!究竟怎么回事?我年轻的时候,你坚守着岗位直到倒下。你继续写着笔录直到救护车把你从地上运走。”你很难向布莱斯解释医生所说的话,布莱斯理解不了。布莱斯的身体里从未有过一根神经,如果说智力有限,那么他的身体仅仅是靠狡猾来赋予生命。他听到格兰特的消息,既不会理解,也不会同情。事实上,隐约有些迹象,仅仅是些暗示,他认为格兰特是装病。一个看起来面色很好的人,如此奇怪地垮下,该和春天高地流淌的河水有关,在去看温坡?斯特里特前,他就已经准备好了钓鱼的鱼饵。
汤米问道:“他们怎么填补这个空缺?”
“可能提升威廉姆斯警长。不管怎么说,他早该升职了。”
向忠诚的威廉姆斯坦白一点也不容易。当你的下属,多来年一直毫不掩饰地把你当作英雄来崇拜,而你却深受神经紧张的困扰,被并不存在的恶魔所控制,这样出现在他面前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威廉姆斯向来随遇而安,心态平和,不会猜忌。所以要告诉他并不容易,看着崇拜变成关心。或是变成——同情?
“把果酱推过来。”汤米说道。
作者简介
约瑟芬·铁伊,推理小说作家。原名伊丽莎白·麦金托什(Elizabeth Mackintosh),1896年7月25日出生于苏格兰西北部。
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推理史辉煌的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之一,也是其中特立独行的一位。和她齐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榭尔斯都是大产量、行销惊人的作家,铁伊却穷尽一生之力只写了八部推理小说,八部水准齐一的好小说——是推理史上极少数一生没有任何失败作品的大师。
-

姑妈的宝刀
¥9.9¥30.0 -

八仙得道传
¥12.0¥40.0 -

悉达多
¥10.6¥28.0 -

捕梦网
¥18.0¥45.0 -

企鹅经典:城堡 变形记
¥14.7¥49.0 -

正义与微笑
¥17.6¥55.0 -

杀死一只知更鸟
¥22.6¥48.0 -

去吧.摩西-企鹅经典
¥11.7¥39.0 -

鼠疫
¥13.2¥38.8 -

小小小小的火
¥14.0¥52.0 -

企鹅经典:月亮与六便士
¥11.7¥39.0 -

三叶虫与其他故事(八品)
¥24.6¥52.0 -

生死场
¥8.1¥36.0 -

偶发空缺
¥17.1¥57.0 -

荒原狼
¥19.9¥39.8 -

一千一秒物语
¥44.2¥69.0 -

龙楼镇
¥20.3¥52.0 -

窄门
¥17.6¥28.0 -

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17.8¥46.0 -

浮世绘女儿(八品)
¥27.5¥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