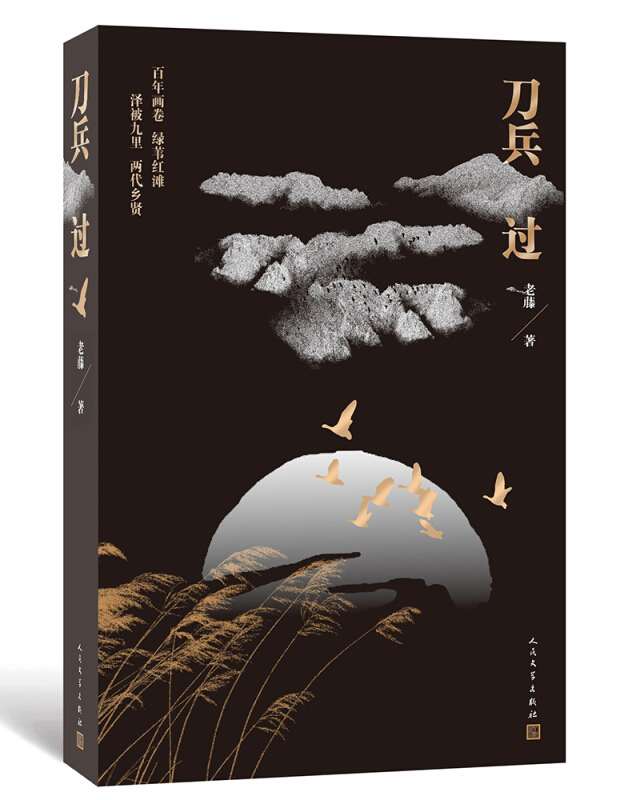- ISBN:9787020134175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481
- 出版时间:2018-08-01
- 条形码:9787020134175 ; 978-7-02-013417-5
本书特色
滕贞甫著的《刀兵过》这是一部以东北大地百年历史为背景、反映东北流人之后经历种种坎坷,始终坚守儒家信念的乡贤文化作品。主人公汪孝儒乃江南名医之后,他的一生频遭磨难,而他始终信念不移,情怀不改。王克笙歌是村民的精神领袖,田庄百姓在他和他的儿子王鸣鹤的引领下度过了一场场风波,生生不息地扎根于辽河两岸。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以东北大地百年历史为背景、反映东北流人之后经历种种坎坷,始终坚守儒家信念的乡贤文化作品。主人公汪孝儒乃江南名医之后,他的一生频遭磨难,而他始终信念不移,情怀不改。王克笙歌是村民的精神领袖,田庄百姓在他和他的儿子王鸣鹤的*领下度过了一场场风波,生生不息地扎根于辽河两岸。 小说讲述了皖南祁门新安医派朱家后人王克笙离开几代偷生的津门闯入关外,寻遍关东之地,落户苇深地远的九里,开办酪奴堂,以图恢复祖姓、传承家学的动人故事。以孔子、达摩和孙思邈为代表的儒释道、仁忠恕的精神,医道、茶道各种中华传承之道,在大先生蒲娘小先生以及塔溪止玉道姑身上得到完美的诠释。九里是一个看似世外桃源、打渔耕织的理想国,寄托了作者的人生追溯和理想。那里从起初丁火不旺的四户人家,繁衍生息至数百口近百户,成为十里八乡口口相传的圣贤之地,培育出声名不凡的白鹤五子;从清末到共和国建立的半个世纪里躲过了各种刀兵之灾,躲过了苇地死神霍乱之灾。九里的故事印刻了中国的乡绅机制如何将传统与文化维护并传承下来的痕迹。它是一个家族的百年史,折射出一个民族乡村变迁的百年侧影,一个家族的梦想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夙愿以偿。 整部作品采取断年扫描的结构,其间暗潮激荡、险环相扣,舒缓中有紧张,峻急处蕴平和,父与子两代乡绅性格一直一曲跃然纸上,让人更加领悟道的无穷魅力。全书视野开阔,笔力雄健,寓意深刻。
目录
节选
九里 引子 王克笙一降生就给了接生婆一个耳光。 因为是站生,估衣街上*有名的接生婆郑氏接生时费了不少力气。要紧关头她甚至泄了底气,高声问在门帘外走来走去的王淦:保大还是保小?本身就是医生的王淦毫不犹豫地说:大小都保。郑氏左上唇的一颗黑痣瞬间像只吸饱了血的蜱虫,几乎要从嘴角上滚落下来,她没好气地说:保下来也是个讨债鬼! 这话是不是被娘胎里的王克笙听到无法考证,他双脚先踏入这个世界时眼睛是睁着的,像两粒野地里常见的黑星星。他大哭着,两只粉嫩的小手胡乱挥舞,正俯身剪脐带的郑氏被小手扫在脸上,虽不疼,却也气恼,郑氏拧着眉头说:这孩子,估衣街上怕是装不下了。 估衣街是一条六百岁的老街。 光绪年之前,估衣街是一家挨一家的估衣铺,街上天天赶集一般人群熙攘。估衣街只估衣裳的规矩是被一家药铺打破的,好比扎紧的篱笆冷不丁就开了个洞,接着,什么麻花铺、剪刀铺、酱菜铺,甚至胭脂铺都一夜间冒出来,让估衣街变得名不副实。 破这规矩的是皖南人王茗。这个溜肩窄腮的中年人花五两纹银买下街巷西南角一个裁缝铺,雇木匠打了一排百眼柜、一张两尺宽三尺长的台案,门楣上挂出一块酪奴堂的牌子,开始坐诊抓药。初时,街坊们抬头侧目瞭一眼牌匾后都摇头,觉得药铺开错了地方,有人甚至编了一句歇后语来调侃:估衣街上开药铺——胡闹。在街坊的另眼中,酪奴堂不温不火地开起来,后来,王茗把皖南的妻儿接来,王家如同一窝南来的燕子,在估衣街上筑巢安家,过上了自鸣钟一样守规守时的日子。 其实,估衣街上的街坊并不知道酪奴堂堂主的来历,他们没料到这个其貌不扬的郎中竟然做过大周的五品官! 王茗不姓王,姓朱,原籍皖南祁门,新安医派世家,以砭石和针灸治病闻名远近。朱家在祁门的堂号不叫酪奴堂,而是叫金石堂,体现了砭石之用。康熙十二年冬月,被撤藩的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叛乱,西南生出战事。康熙十六年春,吴三桂一彪兵马进驻祁门,一天,一个患湿热之症的紫面将军到金石堂看病,朱茗用砭石疗法消去了他的疾患,紫面将军大喜,说你姓朱,与前皇同宗,大军兴明讨虏,你焉能置身事外?说完就让军士把朱茗连拖带推掠入军中做了随军医官。次年,吴三桂建大周称帝,加封文武百官,朱茗稀里糊涂被封五品医官。受封前夜,朱茗做一梦,梦见自己着前朝官服,在金石堂中坐诊,早上醒来,不明此梦凶吉,找一道士圆梦。道士说此梦绝非吉兆,着故国官服,坐今朝之堂,运程大变矣!朱茗觉着官服如同戏装,唱什么戏穿什么衣而已,自己只管治病救人,不用去理什么前朝后朝,此事也就略过。朱茗任五品医官未久,一代奸雄吴三桂驾崩,大周江山随之土崩瓦解,朱茗成了清兵俘虏。也该朱茗幸运,他落在一个姓宋的汉人副将手里。宋副将是郓城人,浓眉重须,声若洪钟,左股被旧年箭伤所困,因战不治,已成大患,看过几个名医,都说此腿不保,副将为此焦虑异常。提审王茗时,宋副将挽起战袍问他能不能医。朱茗仔细查看一番,见伤腿血管条条蚯蚓一样几乎要破皮而出,淤堵之症十分严重,他点点头说可以用砭石一试。宋副将说你若保我一腿,我便留你一命。王茗说此乃沉疴,治愈非一日之功。宋副将说,你只管随我营中,用心治病便是。王茗用一块三角砭石,日日在宋副将穴位上挑来刮去,一段时日后,宋副将腿上条条蚯蚓钻入了皮下,疼痛也大有缓解,一条被诸多名医判为不保的大腿留住了。宋副将对王茗心存感激,觉得这般人才杀头着实可惜,便想学一回老乡宋江,有心帮他脱险。康熙皇帝一道圣喻,大周俘虏悉数发配东北,在押送俘虏北上经过天津时,宋副将给了王茗十两纹银命他去街上买些金枪药,以备军需。王茗上街后,押送俘虏的队伍不等他回来便奉命开拔北上,故意将换了衣装的朱茗撂在了天津。事前宋副将曾嘱咐他:世世代代隐姓埋名,勿言周事!于是,朱茗改称王茗,用五两纹银在估衣街西南角兑下了裁缝铺,剩下的银子置办药柜,进些药材,正式撑起了酪奴堂的门面。开张之日,王茗一没鸣鞭,二没结彩,只在门口载了两株杯口粗的白果树,树上系了两条红布,算是志喜。王氏酪奴堂在估衣街上历经百年五代,成了街上资深老字号。王茗谨记恩人嘱咐,行医做事十分低调,他告诫子孙:牌匾不鎏金,砭石与银针,子孙永相继,柔弱立乾坤。并要求后人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家训,只做良医,不谋良相,守分安命,顺时听天。晚年,他在《朱子治家格言》后补录八十字,让子孙熟记于心,躬行不忘。王家人人都会背诵先祖补录的这一段治家格言: 敬天法祖,固本维新;扶危济困,贫贱同仁;宠辱莫惊,富贵不淫;医上显贵,礼下庶身;立懦强怯,邦小道淳;传习授业,居必择邻;近有道士,远是非君;少言寡语,百毒不侵;朝纲在胸,梦不骇神;三才交互,治病救人。 从创立人王茗、二代王琪、三代王琼都是单传,到了第四代王淦这里情形有了变化,王淦为了打破三代单传宿命,对前辈单字命名的做法加以改进,立下“克明祖训,家国斯存”八字行辈供后代命名,以便族属代代不乱,长幼有序,王氏后人名字由两字变成三字。王淦确立了行辈后果然就生了两个儿子,克箫、克笙成了王氏三字姓名**代。克箫、克笙两兄弟模样相差无几,性格却天地之别。老大克箫像一把胡琴,能屈能伸,可急可缓;老二克笙则像一面铜锣,擂之即响,经久不息。按照长子嫡传的惯例,克箫继承祖业顺理成章,克笙只能辅助兄长坐诊行医。王淦视茶如命,喝茶只喝祁门安茶,诊台上有一把文旦紫砂壶,一年四季总是壶暖茶热,每次切脉,总要先饮一口茶,长舒一口气,然后再专心诊断。酪奴堂没有问诊者时,王淦喜欢独自吟诵一首描写估衣街的竹枝词:衣裳颠倒半非新,提纲挈领唱卖频,夏葛冬装随意买,不知初制是何人。 克笙出生后一直不安分,宋氏担心孩子走了型,想给孩子打个蜡烛包。王滏摇摇头,说王家的孩子*忌讳“捆绑”,几代人都没有打过蜡烛包,到了笙儿这也不能例外。克笙周岁时,依俗要抓周,王淦在笸箩里放了笔、铜钱、书籍、算盘、砭石、黄帝九针、胭脂、茶叶等物件,小克笙一双眼睛只盯住两样东西,茶叶和砭石,一手抓了一样,自顾自玩耍起来。王淦长舒一口气,对宋氏道:复兴朱门者,竖子也!宋氏记得,克笙的哥哥克箫抓周抓了算盘。 童年的王克笙遇事敢抻头。一次,他与克箫在街上玩耍,遇到一个来自新野的耍猴人在耍猴。耍猴人尖嘴猴腮,很像那只猕猴的父亲,被耍的小猕猴看上去瘦骨嶙峋,翻几个跟头就发出凄惨的叫声,有围观者扔给猴子一只梨,猴子捡起刚咬了一口就被耍猴人抢了去,不但抢了去,还抽了猕猴一鞭。小小的克笙气不过,冲过去将耍猴人手中的梨子夺下,还给了眼巴巴盯着梨子的猕猴,耍猴人被这孩子的举动吓愣了,好半天没缓过神儿来。克箫怕弟弟惹祸,过去向耍猴人赔个不是,拉起克笙挤出人群跑回酪奴堂。看两个孩子面红耳赤的样子,父亲问发生了什么事,克箫没敢说,倒是克笙气呼呼地说:那个耍猴的欺负猴子,我不该夺梨,该夺了他的鞭子!父亲叹了口气,嘱咐克箫再上街要看好弟弟,别多管闲事。 克笙七岁开始跟母亲读书,读《三字经》《千字文》和《朱子治家格言》,也背诵一些汤头歌之类的中医歌谚。克笙读书用功,与哥哥克箫只专注于医书不同,他还喜欢《论语》《孟子》,小小年纪提出的一些问题有时会把母亲问住。一次,他问母亲:孔子陈蔡之困,见到颜回偷吃米饭,为什么不能直接呵斥,而要旁敲侧击说风凉话呢?孔子不是主张友直吗?宋氏说,有些话不能当面讲的,总要给人留些颜面。克笙摇头,颜回要是不辩解,这个疙瘩一辈子也解不开,话还是说开了好。克笙对各种味道特别灵敏,别人闻不到的味道他能轻易嗅出来,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别人目视耳闻得知,他却能凭味道有所感悟。酪奴堂右邻是个宁波籍的老裁缝,嗜好烟土,平时霜打般无精打采,一旦吸过烟土便鬼狐附体一样亢奋。一日克笙在街上玩耍回家,迈进门槛时,他鼻子忽然抽动几下,说闻到一股悲味。母亲说悲味岂能闻之,克笙说是僵腐之味,恐怕邻里家有不祥。家人没在意,小孩子说话没来由不必当真。须臾,邻居来报丧说老人刚刚过世,打扰邻里乞望体谅。小克笙竟然能嗅出死亡之味,家人深感神奇。还有一次,正在吃饭的小克笙说家里有一股来自山野中的湿腥之味。父亲说酪奴堂药材大都经过九蒸九晒,何来湿腥之味?他说还是找找看,这湿腥味应是来自活体。于是家人四处寻找,果然在厨房水缸下找到一条盘成一团的菜花蛇。母亲说克笙有这等本事,对行医诊病大有裨益。 依照王家祖规,孩儿满十六岁应告知家史,说明家族渊源。克笙十六岁生日那天傍晚,父亲王淦关紧门窗,在酪奴堂中三圣图下将王家来龙去脉说与克笙。父亲要求克笙对此事守口如瓶,不得对外人吐露半字。为了让克笙谨记教诲,父亲特意讲了前朝崇祯皇帝五太子朱慈焕的教训,朱慈焕隐姓埋名一个甲子,七十五岁时却因言泄风,遭满门抄斩。父亲告诫他:行不离道,医不扣门,无灾无祸便是福祉。克笙听后默默不语,一连两个白天,就坐在台阶上仰望着门前两棵白果树上的喜鹊窝出神。他明白了王家为什么世代谨小慎微,原来头顶有一座大山压着。他理解了父亲为何酒后经常吟诵那首竹枝词,父亲一定由竹枝词联想到了朱家命运的坎坷。 在知晓家史后第三天,克笙恢复了常态,他对哥哥克箫说自己嗅到了一股干草味,这味道让他心里充满了对远方的憧憬,时刻有催马扬鞭的冲动。克箫不会知道,此时的弟弟已经在心中立下罚誓: 不复祖姓,誓不为人!
作者简介
滕贞甫,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1963年11月生于山东即墨,1983年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鼓掌》《腊头驿》《樱花之旅》,小说集《熬鹰》《会殇》《没有乌鸦的城市》等六部,文化随笔集《儒学笔记》《探古求今说儒学》。
-

生死场
¥8.6¥36.0 -

长安的荔枝
¥27.1¥45.0 -

告白
¥12.0¥36.8 -

鱼河岸小店
¥14.5¥45.0 -

人性的因素
¥20.5¥65.0 -

守夜
¥14.3¥42.0 -

姑妈的宝刀
¥11.2¥30.0 -

蟑螂
¥15.3¥45.0 -

月亮与六便士
¥10.0¥36.0 -

西线无战事
¥21.6¥48.0 -

无足轻重的小误会
¥19.6¥58.0 -

面纱
¥20.3¥45.0 -

野性的呼唤
¥9.4¥36.0 -

萨宁
¥19.9¥59.0 -

不安公主
¥15.4¥48.0 -

黑男孩
¥15.9¥49.8 -

欢喜
¥15.1¥42.0 -

三四郎
¥13.6¥42.0 -

悉达多
¥18.4¥49.8 -

秘密(八品)
¥18.1¥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