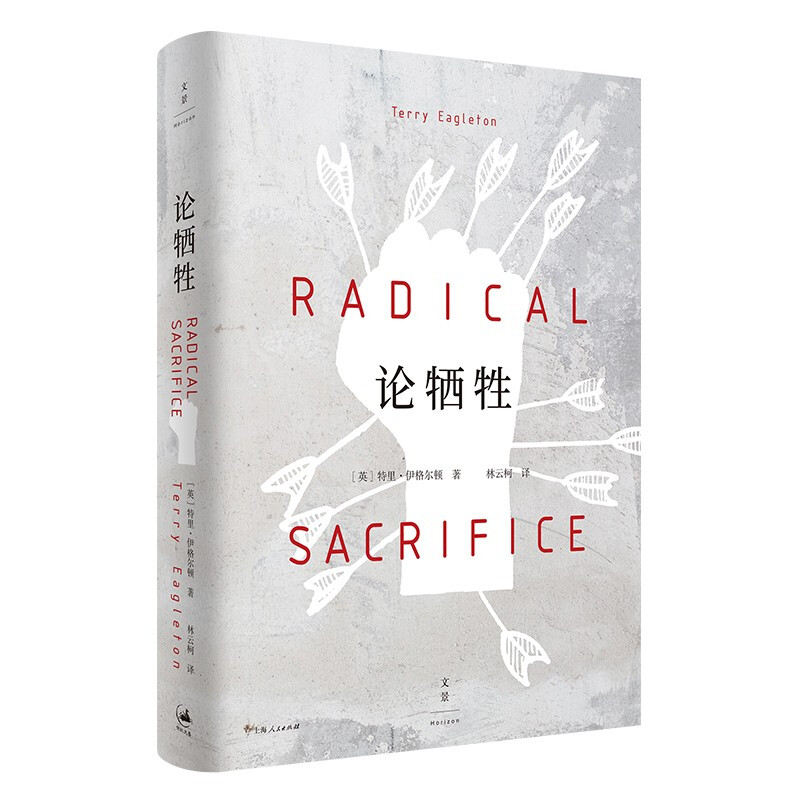- ISBN:9787208166493
- 装帧:一般轻型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20cm
- 页数:283页
- 出版时间:2021-04-01
- 条形码:9787208166493 ; 978-7-208-16649-3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当代西方文化批评领袖人物伊格尔顿晚年跨领域综合性代表作之一。继《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文化与上帝之死》后,伊格尔顿贯通文学评论、政治哲学批判、神学研究的集成之作。 ★深入西方文明的内在肌理,重绘牺牲观念的思想地图。 ★一部追溯暴力与文明源头的另类西方文化小史。
内容简介
作为现代概念的“牺牲”, 昭示着自律战胜了欲望, 同时也被贬为消极与陈腐的自我克制。在本书中, 伊格尔顿通过扣人心弦的论述, 揭示出“牺牲”这一理念其实一直遭到诸多曲解。在本书中伊格尔顿试图追溯“牺牲”的复杂话语谱系。他对“受难”做了全景式的分析, 将一大群哲学家、思想家及文本绘制在了一起 —— 从黑格尔、尼采、德里达到《埃涅阿斯纪》和《鸽之翼》。他试图抛开误解, 探求“牺牲”在现代性中的意义。
目录
前言
**章 激进的牺牲
第二章 悲剧与受难
第三章 殉道与必死之厄
第四章 交换与过剩
第五章 国王与乞丐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重估伊格尔顿的可能
节选
在弗洛伊德看来,爱欲总是在其消逝处才发觉自己已经开始,正如自我在死亡中才找到了庇护所,就像一个令人喜悦的国,它曾兴盛,而后却踏上了时运不济的旅程。狄多在自杀行为中发现了自己的庇护所。色欲作为累退性质的满足具有一种泯灭叙事的倾向,恒久地想要折返回之前的情态,并由此对作为城邦创建物和历史方案的爱欲造成威胁,但那依然是退行与进步兼具。埃涅阿斯寻求建立罗马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向起源的折返,因为特洛伊自身就是由意大利勇士达耳达诺斯所建立的。作为第二个特洛伊,罗马是对起源的重复,是对爱欲时间性的消除。与此相同,先知混淆了时间,将未来折入现在之中。正如拉丁姆这个名字所暗示的,它是一处藏身之所,一个萨图恩在逃避朱庇特时所寻找到的避难所,遍体鳞伤的异乡者终会在此处安歇,正如在弗洛伊德理论中饱受摧残的自我也终将找到其安息之地。 因此,维吉尔伟大的史诗所记录的,正是罗马的史前暴力,它从战争的纷乱和万物的混沌之中勾勒出了一段流畅的叙事,而文明正是从这些难以驾驭的强力之中抽取出自身一段连贯的轨迹。特洛伊战争中的强掳和残暴是罗马的黑暗之渊,而埃涅阿斯,这座城遥远的祖先则是一名被放逐者和流亡者,无根的领袖,无所顾忌的奋勇之士,战争中浴火幸存之人,他正是过去与现在之间脆弱的纽带。16不过这段关于一场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充满恶意神灵的历史,通过诗本身被转化成了辉煌当下的序曲。其他杂乱的插曲则被织入天命延续的严丝合缝之中,被炼金术般地淬炼进神圣的国运。我们知道埃涅阿斯必会达成他的使命,因为诗本身就存在于其所被打磨成的光环之下,国家的硕果近在眼前,而其自身野蛮的开端得以被纵览,从而确保屠杀的历史已经被恰当地终结。罗马现在所行使的主权超越于各种权力之上,这也意味着必须磨灭掉其所形成的过往,去抹杀那些埃涅阿斯及其同伴曾时常被描绘成尽情受其摆弄之人的权力。国运叙事于是就战胜了一种前历史的灾难叙事。 然而,文明一旦被建立,那些血腥的叙事也就沁入其骨髓,无法被缓解。因此与所期望的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是那类冷峻传说的不断延续—以一种更高层次的野蛮形式,也就是说以律法、君权和普遍秩序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文明社会所伴随着的无止境的帝国扩张就被证明为应许之地的反面,正如罗马将那些与其自身的兴起形影不离的破坏和屠杀加罪于弱势民族,于是,往往与《埃涅阿斯纪》中所叙述的不同,其所追溯到的国之根源并非国家诞生的光辉时刻,而是那些荣光湮灭的场景。暴力就是文明沐浴在文明化的条件中持续走向兴盛的前奏,通过某些方式,暴力会被一些文明教条和治理技术所缓解,但是也在以另外一些方式被强化。除此之外,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则被纯化为律法的合法暴力,从而保证像《埃涅阿斯纪》这样的国家史诗能够被书写。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提醒我们的,这样的律法代表了“钳制暴力的暴力”。在这种被许可的肇起于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的侵犯之中,野蛮与文明几乎难以区分。文明的*后保证则是由国家裁定的死亡。不过,这样的情势本就是自始至终被期盼的。瓦尔特·伯克特写道,在神话中,“与文明化生活之达成同时相伴随的往往是被撕碎的生物和食人的故事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在神话的两面性中,也在赐福与诅咒均被视为神圣的耦合中,人们能够瞥见死亡和分裂正潜伏在和平与繁荣的源头里。 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阿》中,恐怖力量的阴云笼罩于文明的前哨之上,预示着文明将被塞回羊水当中,而这种恐怖之力*终会在文明的边界被供奉,正如复仇三女神(Furies)被转而认作欧墨尼得斯(Eumenides)或是仁慈女神。1在前现代时期,恐怖的人物必须被甜蜜地讲述,如此巧言令色地被塞入一种城府极深的叙事,这使得这种恐怖似乎是发自善心而又被归置得当的,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可怖与圣洁之间暧昧的界限才被用“神圣”(sacred)这个词来指涉。正是这样的胁迫无迹可寻地渗入社会秩序,由此它便是恰当的、崇高的,并且由内面转为外向性,化为抵御城邦之敌的力量。在一种醒目的悖论当中,暴力是从泥沼中解救文明之力,如今则化为律法形式保护文明免于外来侵略与内部动荡。野蛮与文明与其说是前后相继的,不如说是同时发生的,与其说是连贯的历史阶段,不如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建构起人类文化的力量同样也有能力撕裂它。 在另外一些方面,牺牲也试图探索调试致命之力的方式,诱发其潜在的创世之力,去认识其所依赖的神圣或魔鬼的能量是如何比理性更深入骨髓,且同时还依附着文明的宣言。理性若要发挥权能,就必须对自己些许的力量有所意识,去照亮被黑暗和空无阴云笼罩的前线。在这一层面上,《俄瑞斯忒阿》中的真理也就是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中的真理。自我必须建立在无我之上,没有痛苦和恐怖,则律法与秩序也就无所从来,城邦只是野蛮的一个改进版本—虽然这一点显然已经被它抛诸脑后了。想要在这些神圣力量的角力中获胜,你就必须在它们之中寻找一种象征性的身份认同,但正如《酒神的伴侣》中彭修斯的遭遇那样,这种身份并不来自某个确切的安顿之所,而是*终把你撕得支离破碎。向权能致以应有的敬意并非对于它们的屈从。相反,它们必须被融入社会秩序当中,尤其是融入律法崇高恐怖的形式当中,只有这样,对于政治权威的认同才能够通过威权得到强化。而这里的麻烦在于,威权如何就能够支撑起这种认同而不是摧毁它。牺牲总是离不开弱者积怨的暗流涌动,而对于宰治权力的谦卑服从则总是伴随着反叛敌意的死灰复燃。因为无论谁想要通过展示其倾向的优越性来向你传达某种赞同,那么你因其慷慨而产生的感激之情就必然被某种实际的不满所反噬,两者必会纠缠在一起。为了缓解这种敌意的罪责,于是在律法成为超越我们所在之永恒之前,我们必须一再修复祭坛,永远处在对于纯净的、无瑕的自我克制的追寻之中,一刻不得安宁。
作者简介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曾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现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杰出教授。1960年代至今,已出版著作数十种,涉及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领域。代表作有《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之后》《英国现代长篇小说导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等。
-

伦理学与经济学
¥8.3¥20.0 -

《老子》注评
¥3.9¥11.0 -

冯友兰的伦理思想
¥20.6¥49.0 -

理想国
¥22.0¥45.8 -

脑海中的声音:自我对话的历史与科学
¥17.1¥49.0 -

道家哲学研究-(附录三种)
¥4.9¥18.0 -

小窗幽记
¥5.7¥19.0 -

谈修养
¥6.0¥20.0 -

论语讲座
¥6.2¥23.0 -

谈美
¥5.0¥10.0 -

中国禅宗
¥9.9¥26.0 -

一种人生观
¥23.0¥42.0 -

昨日书林:道教史
¥11.0¥33.0 -

西方哲学与人生-第二卷
¥13.2¥49.0 -

中国哲学十讲
¥14.9¥49.8 -

艺术美学讲演录
¥9.6¥32.0 -

和颜爱语
¥9.9¥29.8 -

宽容:人类的解放
¥12.7¥39.8 -

宋代理学三书随劄
¥19.9¥32.0 -

孔子的智慧-精装典藏新善本
¥16.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