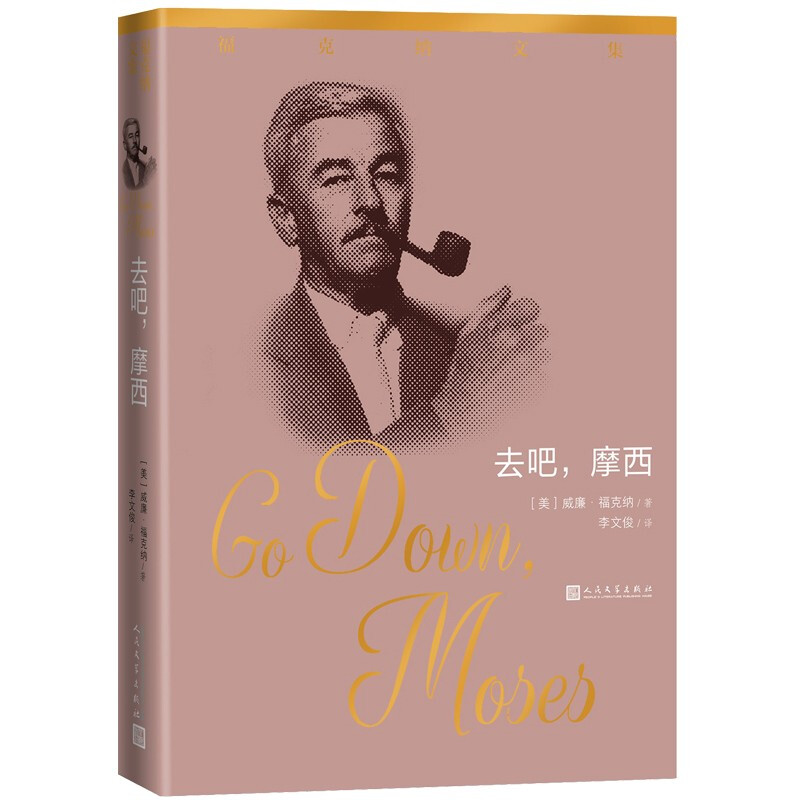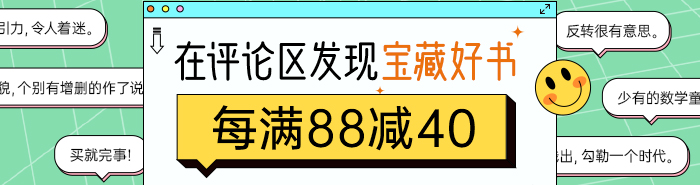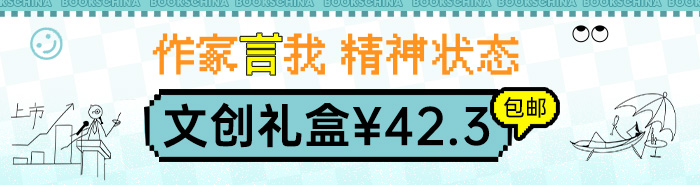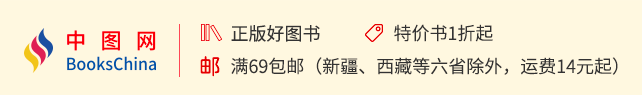- ISBN:9787020128105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其他
- 页数:369
- 出版时间:2021-06-01
- 条形码:9787020128105 ; 978-7-02-012810-5
本书特色
福克纳是长篇小说巨匠,也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此文集收录的篇目均为福克纳短篇小说中的杰出之作,代表了福克纳短篇小说的文学风格和主要成就。无论在题材内容或手法技巧方面,福克纳的短篇小说跟他的长篇小说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他大部分的短篇小说还是以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描述的还是那个王国的沧海桑田和世态人情,探讨其中的家族、妇女、种族、阶级等问题,表现“人类的内心冲突”。李文俊是我国研究和翻译福克纳作品的**人,他的译文忠实传神,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内容简介
福克纳是长篇小说巨匠,也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此文集收录的篇目均为福克纳短篇小说中的杰出之作,代表了福克纳短篇小说的文学风格和主要成就。无论在题材内容或手法技巧方面,福克纳的短篇小说跟他的长篇小说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他大部分的短篇小说还是以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描述的还是那个王国的沧海桑田和世态人情,探讨其中的家族、妇女、种族、阶级等问题,表现“人类的内心冲突”。
目录
目录
前言
谱系图
人物表
献词
话说当年
灶火与炉床
大黑傻子
古老的部族
熊
三角洲之秋
去吧,摩西前言
节选
话说当年 1 艾萨克·麦卡斯林,人称“艾克大叔”,早过七十都快奔八十了,他也就不再实说自己的年纪了,如今是个鳏夫,半个县的人都叫他大叔,但他连个儿子都没有本节原文除**个词(Issac)系大写之外,每段首词均为小写,而每段结尾处均无句号。作者的用意想是表示出此节与以下各节时间上的差异。这一节可以看作是故事正文之前的“楔子”。 这里要说的并非他亲身经历甚至亲眼目睹的故事,经历与目睹的是年纪比他大的表亲麦卡斯林·爱德蒙兹,此人乃是艾萨克姑妈的孙子,说起来是家族中女儿一支的后裔,不过却是产业的继承人,到一定时候又会是赠予人,这份产业原先有人认为而现在仍然有人觉得该是艾萨克的,因为当初从印第安事务衙门那里得到土地所有权状的是姓他那个姓的人,而住在这儿的他父亲手下的奴隶的有些后裔直到如今仍然姓他的这个姓。可是艾萨克本人却不作此想:——二十年来他一直是个鳏夫,他一生中所拥有的东西里,无法一下子塞进衣袋并抱在手里拿走的就是那张窄窄的铁床和那条沾有锈迹的薄褥子,那是他进森林野营时用的,他去那里打鹿、猎熊、钓鱼,有时也不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喜欢森林;他没有任何财产,也从来不想拥有,因为土地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的,就跟阳光、空气和气候一样;他仍然住在杰弗生镇一所质量低劣的木结构平房里,那是他和他女人结婚时老丈人送的,他女人临死时把房子传给了他,他装作接受了,默许了,为的是讨她喜欢,让她走的时候心里轻松些,不过尽管临终有遗言关照,这房子并非他的由法院判定有正式遗嘱规定而具有永久所有权的产业,正式说法是不是这样可不清楚,反正是这么回事,而他留着房子仅仅是为了让他小姨和那几个外甥有地方住,他老婆死后他们便跟他住在一起,也是为了自己可以住其中的一间,老婆在世时他就是这样住的,她那时也愿意他这样住,如今小姨和外甥们也这样,他们愿意他这样住,直到他去世,至于死后 这并非他亲身经历甚至亲自记得的,仅仅是从表外甥麦卡斯林处听来的,是耳闻而得的陈年旧事,他这外甥出生于一八五年,大他十六岁,由于艾萨克这棵独苗儿出生时父亲已年近七十,所以与其说麦卡斯林是他外甥还不如说是长兄,或者说简直就是他父亲而非外甥与哥哥,这故事发生在早年间,那时候2 他这里的“他”已不是艾萨克,而是麦卡斯林·爱德蒙兹,下同。本故事发生在1859年,当时他9岁。下文常用“孩子”来指他。和布克大叔发现托梅的图尔又逃走了,便跑回到大房子里去,这时候,他们听见布蒂大叔在厨房里诅咒和吼叫,接着狐狸和那些狗冲出厨房,穿过门厅进入狗房,他们还听到它们急急穿过狗房进入他和布克大叔的房间接着看见它们重新穿过门厅进入布蒂大叔的房间,然后听见它们急急穿过布蒂大叔的房间重新进入厨房,到这时听起来像是厨房的烟囱整个儿坍塌了,而布蒂大叔大叫得直像条汽艇在拉汽笛,这时狐狸、狗群外加五六根劈柴一起从厨房里冲出来把布蒂大叔裹挟在当中而他手里也拿着根劈柴瞅见什么就揍什么。真是好一场精彩的赛跑呀。 当他和布克大叔跑进他们的房间去取布克大叔的领带时,那只狐狸已经蹿到壁炉架上的钟后面去了。布克大叔从抽屉里取出领带,把几只狗踢开,揪住狐狸脖颈上的皮,把它拎下来,塞回床底下的柳条筐里,接着他们走进厨房,布蒂大叔正在那里把早饭从炉灰里捡起来,用他的围裙擦干净。“你们这究竟算什么意思,”他说,“把这天杀的狐狸放出来让一群狗满屋子的追撵?” “别提那骚狐狸了,”布克大叔说,“托梅的图尔又跑了。快让我和卡斯胡乱吃点早饭。没准我们能赶在他到达那边之前把他逮住。” 这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托梅的图尔是往哪儿跑的,但凡有机会可以开溜,一年总有两回吧,他总是朝休伯特·布钱普先生的庄园跑去的,就在县界的另一边,休伯特先生(跟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一样,他也是个老光棍)的妹妹索凤西芭小姐至今还想让大家称那地方为“沃维克”,这是英国一个府邸的名称,她说休伯特没准是真传的伯爵,只不过他从来没有那份傲气,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争取恢复他的正当权利。托梅的图尔是去那儿跟休伯特先生的女奴谭尼厮混的,他总是在那儿泡着直到有人前去把他抓回来。他们无法从休伯特先生手里买下谭尼,用这个办法来稳住托梅的图尔,因为布克大叔说他和布蒂大叔手底下黑鬼已经太多,弄得都没法在自己地里自由走动了,他们又不能把托梅的图尔卖给休伯特先生,因为休伯特先生说他不但不想买托梅的图尔,也不想让自己的家里有这个天杀的白皮肤的(他身上有一半麦卡斯林家血液因为图尔是托梅跟艾萨克的祖父卡洛瑟斯老爷养的私生子。)小伙子,白送不要,即使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肯倒贴房饭钱也不要。若是没人立即去把托梅的图尔领回来,休伯特先生就会自己把他押来,还和索凤西芭小姐一起来,他们会待上一个星期或甚至更久,索凤西芭小姐住在布蒂大叔的房间里,而布蒂大叔就得干脆搬出房子,睡到小木屋区去,那是麦卡斯林的外曾祖父在世时黑奴们住的地方,外曾祖父死后,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就让所有的黑鬼都搬进外曾祖父来不及装修完毕的大房子里去,而黑鬼们住在那儿时,布蒂大叔连做饭也不上那儿去做,甚至连屋子也不再进去,只除了晚饭后在前廊上坐坐,在黑暗里坐在休伯特先生与布克大叔之间,过了一会儿,连休伯特先生也敛住了话头,不再说等索凤西芭小姐出嫁时他还要往给她的陪嫁上增添多少口黑奴和多少英亩土地,而是就去睡觉了。去年夏季有一天半夜里,布蒂大叔偶然醒来,恰巧听见休伯特先生驾车离开庄园的声音,等他叫醒大家,大家让索凤西芭小姐起床、穿戴好,再把车套好出发,赶上休伯特先生,天都快亮了如作为陪伴者的休伯特不在,未婚的索凤西芭小姐的名誉将受到损害,布克便不得不与之结婚。因此,他们非得把想摆脱妹妹的休伯特追住不可。。因此,总是他卡斯和布克大叔出发去逮托梅的图尔的,因为布蒂大叔是从来不出门的,他不愿进城,就连到休伯特先生那里把托梅的图尔领回来也不愿去,虽然大伙儿知道布蒂大叔冒起风险来要比布克大叔胆大十倍。 他们匆匆忙忙把早饭吃完。布克大叔趁大伙儿朝空地跑去抓马儿时赶紧把领带打上。抓托梅的图尔是他唯一需要打领带的时候,而他从去年夏天那个晚上之后就再未把它从抽屉里取出来过,当时布蒂大叔在黑暗里把他弄醒,说:“起来,得赶快。”布蒂大叔则是连一根领带都没有的;布克大叔说布蒂大叔根本不愿费这份心,即使在他们这样的地区,感谢上帝这儿女士是如此稀少,一个男人可以骑马沿着一根直线走上好几天,也无需因见到一位而躲躲闪闪。他的奶奶(亦即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的妹妹;他自幼失母,是姥姥把他一手领大的。他的教名,麦卡斯林,也由此得来,而他的全名是卡洛瑟斯·麦卡斯林·爱德蒙兹)说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两人合用一根领带,无非是堵别人的口的一种办法,不让他们说两人像双胞胎,因为即使年届六十,他们仍然一听人说分不出他俩谁是谁就要跟人打架;这时麦卡斯林的父亲就说了,任何人只要跟布蒂大叔打过一次扑克,就再也不会把他当作布克大叔或是任何人了。 乔纳斯应是麦卡斯林庄园里的一个黑种仆人。已经给两匹马备好鞍,等在那里了。布克大叔登上马背的动作一点儿也不像个六十岁的人,他瘦削灵活得像一只猫,头颅圆圆的,一头白发留得很短,一双灰眼睛又小又冷酷,下巴上蒙着一层白胡楂,他一只脚刚插进马镫,那匹马就挪动步子了,等来到开着的院门口就已经在奔跑了,到这时,布克大叔才往马鞍上坐了下去。爱德蒙兹不等乔纳斯托他上去,便胡乱爬到那匹矮小些的马的背上,用脚跟夹了夹,让小马跑起它那僵僵的、两下两下连得挺紧的小步,出了院门去追赶布克大叔,这时布蒂大叔(麦卡斯林甚至都没注意到他在场)从院门里跨出来一把抓住马嚼。“看着他点儿,”布蒂大叔说,“看着梯奥菲留斯。一旦有什么不对头,赶紧骑马回来叫我。听见了吗?” “听见了,大叔,”麦卡斯林说,“快让我走吧。我连布克大叔都要撵不上,更别说托梅的图尔——” 布克大叔骑的是“黑约翰”,因为只消他们能在离休伯特先生家院门至少一英里的地方看见托梅的图尔,“黑约翰”就能在两分钟以内撵上他。因此当他们来到离休伯特先生家大约三英里的那片长洼地时,瞧,托梅的图尔果然正在前面大约一英里外端坐在那匹叫“杰克”的骡子背上往前赶路呢。布克大叔伸出胳膊往后一挥,勒紧缰绳,蹲伏在他那匹大马的背上,圆圆的小脑袋和长有瘤子的脖子像乌龟那样伸得长长的。“盯住打猎用语,原文为“stole away”,意思是催促猎狗紧跟住猎物的嗅迹。!”他悄没声地说,“你躲好,别让他见到你惊跑了。我穿过林子绕到他前面去,咱们要在小河渡口把他两头堵住。” 他等着,直到布克大叔消失在林子里。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可是托梅的图尔看到他了。他逼近得太早了;也许是因为生怕赶不上看见图尔被撵上树这前后用的都是猎人追捕猎物的语言。“撵上树”即逼进死角之意。。那真是他有生以来所见过的*精彩的一次赛跑。他从未见过老杰克跑得这么快,而托梅的图尔平时走路总不慌不忙的,即使骑在骡背上也这样,谁也没料到他也能快跑。布克大叔在林子里呼啸了一声,对准猎物冲去,紧接着只见黑约翰从树丛里蹿出来,急急奔着,伸直身子,平平的,像只鹰隼,这时布克大叔简直就趴在它耳朵后面,一边在大声吼叫,看上去活像一只大黑鹰据注家泰勒女士说,这种美国南方的沼泽鹰在冬季总是掠过野草飞捕猎物。故此福克纳以之比喻布克大叔胯下的那匹黑马。驮着只麻雀,他们穿过田野,跳过沟渠,又穿过另一片田野,这时这孩子也动起来;还不等他明白过来,那匹母马已在全速飞奔,他自己也吼叫起来。照说作为黑人,托梅的图尔一见他们本该从牲口背上跳下,用自己的双脚跑的。可是他没这样做;兴许是托梅的图尔从布克大叔处溜走已有点历史,所以已习惯于像白人那样逃跑了。仿佛是人和骡把托梅的图尔平时走路的速度和老杰克生平发挥得*好的速度加到了一起,而这速度恰好足以使他赶在布克大叔之前到达渡口。等孩子和小马赶到时,黑约翰已经喘得不行,浑身冒汗,布克大叔下了马,牵着它遛圈儿,好让它缓过劲儿来,这时他们已能听到一英里外休伯特先生家招呼进午餐的号角声了。 不过,眼下托梅的图尔好像也不在休伯特先生的庄园里。那黑孩子仍然坐在门柱上,在吹号——院门早就没有了,光剩下两根门柱,一个个头跟他差不多的黑孩子坐在一根门柱上,正在吹一把猎狐小号;这就是索凤西芭小姐仍然在提醒人们其名称为沃维克的那个庄园,虽则人们早已清楚她要这样称呼用意何在,到后来一方面人们不愿意叫它沃维克而她呢甚至都不想知道他们在讲的是什么,于是听上去就像是她和休伯特先生拥有的是两个各不相干的庄园,却占据着同一块地方,仿佛是一个叠在另一个之上。休伯特先生正坐在“泉房”里,脱了靴子,双脚浸在泉水里,一边啜饮甜酒用糖水、波旁威士忌和冰兑成的一种饮料。。不过那边的人谁也没看见托梅的图尔;有一阵子好像休伯特先生甚至连布克大叔所说的那人是谁都对不上号。“哦,那个黑鬼,”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咱们吃过午饭去找他就是了。” 不过看上去他们也还不打算吃饭呢。休伯特先生和布克大叔干了一杯甜酒,这时休伯特先生总算派人去关照门柱上的那孩子可以不必吹了,接着他和布克大叔又干了一杯,而布克大叔仍在不断地说,“我只不过是想找回我的黑小子。然后我们就得动身回家。” “吃了午饭再说吧,”休伯特先生说,“要是咱们没能在厨房左近把他轰出来,咱们就放狗出去搜他。只要那臭挨刀的沃克种狗一种猎狐犬,因约翰·沃克参与育种而得名。嗅得出来,就不愁逮不住他。” 可是终于有一只手从楼上百叶窗破洞里伸出来,开始挥动一块手帕或别的什么白布。于是他们穿过后廊,走进宅子,休伯特先生跟往常一样,再次警告他们要留神他还顾不上修的一处朽坏的地板。这以后他们站在门厅里,过不多久传来一阵环佩丁当与衣裙窸窣的声音,他们开始闻到香气,原来是索凤西芭小姐下楼来了。她把头发拢在一顶带花边的软帽里;她穿的是星期天穿的出客服装,一根珠链和一条红缎带系在脖子上,有个黑小妞给她拿着扇子,孩子静静地站在布克大叔身后一点儿的地方,注视着她的嘴唇,一直盯到双唇张开,他看见了那颗有黄斑的牙齿。他以前从未见到过有谁牙齿带黄斑,他还记得有一回他姥姥和他爸爸谈到布蒂大叔和布克大叔,他姥姥说索凤西芭小姐有一阵子也还算好看。也许她好看过。他可说不准。他才只九岁啊。 “唷,是梯奥菲留斯先生呀,”她说。“还有小麦卡斯林,”她说。她从不把眼光投向他,这时也不是在对他说话,这他很清楚,虽然他做好了准备,也平衡好身子,等布克大叔脚往后退时也把他的脚向后退。这是当时美国南方绅士正式鞠躬的一种姿势:在把头低下去的同时右脚向后退十八英寸左右。“欢迎光临沃维克呀。” 他和布克大叔把脚退了退。“我无非是来把我的黑小子领回去,”布克大叔说,“完了我们就得动身回家。” 接下去索凤西芭小姐讲了一通一只大黄蜂的事,不过他记不清是怎么讲的了。话说得太快,也说得太多,耳环与珠链的碰击声犹如小体型的骡子一路小跑时它那小挽链发出的音响,而香气也更咄咄逼人了,好像耳环与珠链每一晃动都能把香水喷雾似的喷向别人似的,他还盯视着那颗变色的牙齿在她的唇间轻叩并闪光;反正是在说布克大叔像只从一朵又一朵花里吮吸蜜汁的蜜蜂,从不在一处久留,而积贮的蜜都虚掷在布蒂大叔的荒凉的空气里了参见英国诗人托·格雷(1716—1771)的《墓园挽歌》中的诗句:“世界上多少花吐艳而无人知晓,/把芳香白白的散发给荒凉的空气。”,她把布蒂大叔叫作阿摩蒂乌斯先生,就像把布克大叔叫作梯奥菲留斯先生一样,要不,说不定这蜜汁是留待一位女王莅临时享用的吧,那么这位幸运的女王又是谁,将于何时莅临呢?“什么,小姐?”布克大叔说。这时候休伯特先生接茬说了: “哈。一只雄蜂此处的“雄”,原文为“buck”,与“布克”谐音,休伯特是接住妹妹的话头在打趣。啊。我看等他把双手揪住那黑小子的时候,那黑小子会觉得布克是只雄赳赳的大黄蜂英语俗语中有“疯得像只大黄蜂”(mad as a hornet)之说。休伯特是在继续逗弄布克。哩。不过我想布克眼下*需要的还是尝点肉汁,吃点饼干和喝上一杯咖啡。我自己也饿了呢。” 他们走进餐厅吃起来,这时索凤西芭小姐说真不像话,只隔开半天骑马路程的邻居如今也不常来往,布克大叔就是这样,于是布克大叔说是的,小姐,接着索凤西芭小姐说布克大叔打从生下来躺在摇篮那会儿起就是个铁了心的浪荡单身汉,这一回布克大叔竟停止了咀嚼,把眼睛抬起来说,是的,小姐,他的确是这样,而且天生如此,现在太晚了,再改也难了,不过至少他可以感谢上帝没有哪位女士必须受和他与布蒂大叔一起生活的罪,这时索凤西芭小姐又说了,呀,也许布克大叔仅仅是至今还未遇到这样一位女士吧,她会不但愿意接受布克大叔愿意称之为受罪的那种生活,而且还会使布克大叔觉得连自己的自由也只不过是值得为之付出的一个很小的代价呢,这时布克大叔说,“是啊,小姐。还没有遇到。” 接着他、休伯特先生和布克大叔走出屋子来到前廊上坐下。休伯特先生甚至还没来得及再把鞋子脱掉,也没来得及请布克大叔把他的也脱了,索凤西芭小姐就从门里走了出来,托着一只托盘,上面搁着又是一杯甜酒。“得了,西贝,”休伯特先生说,“他才吃过饭。他现在不想喝。”可是索凤西芭小姐像是根本没听见他的话。她站在那里,那颗黄斑牙现在没有闪光,而是固定着,因为她这会儿没开口说话,只是把甜酒递给布克大叔,过了片刻才说她爸爸以前总是说再没有一位密西比密西西比的简称,这里有学小儿语故作娇态之意。女士的纤手更能使一杯密西比甜酒喝起来更加怡人的了,布克大叔想不想看看她以前是怎样给爸爸添点甜味的呢?她举起酒杯抿了一小口,然后端还给布克大叔,这一回布克大叔接下了。他再次把一只脚往后退了退,喝下了那杯甜酒,说若是休伯特先生打算躺下休息的话,他也可以睡一会儿,因为从各种情况看来,托梅的图尔是决心让他们有一番漫长、艰苦的追逐的,除非休伯特先生的那些狗表现特别出色,与往常大不一样。 ... 于是休伯特先生带了那群猎狗和几个黑小子回去了。而他麦卡斯林和布克大叔还有那个带来小杂种狗的黑小子继续前进,那黑小子一手牵着老杰克,另一只手捏着系小狗的皮带(那是一段磨旧的犁绳)。这时布克大叔让小狗闻闻托梅的图尔的外套;那只小狗好像这会儿才**次明白他们要找的是什么,他们本该把套在它脖子上的皮条解开,骑马追随在它的后面,可是不早不晚,宅子那边的黑孩子吹响了招呼用晚餐的猎狐号角,他们便不敢那样做了。 接下去天空全黑了。这以后——孩子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也不清楚他们在什么地方,离宅子有多远,只知道那是块良田,天黑了已有一阵子,而他们还在往前走,布克大叔时不时弯下身让那小狗再闻闻托梅的图尔的外套,而自己则端起威士忌瓶子再呷上一口——他们发现托梅的图尔又绕回来了,正在兜一个大圈子往大宅子走去。“我的天,咱们算是找到他了,”布克大叔说,“他想缩进洞去呢。咱们抄近道回宅子去,赶在他缩进窝之前截住他。”因此他们让那黑人放开小狗,让他骑上老杰克跟踪图尔,而孩子和布克大叔则策马朝休伯特先生家奔去,只在山冈上停留片刻,让马儿喘口气,同时谛听小狗在沟底叫唤的声音,托梅的图尔还在那儿兜圈子呢。 可是他们压根儿没逮住他。他们来到漆黑的黑人村;他们可以看见休伯特先生宅子里灯光仍然亮着,有人再次吹响了猎狐号角,那肯定不是什么小孩吹的,而他从未听到过有谁把猎狐号吹得这样气急败坏的,他和布克大叔便分开,守在谭尼小屋下的斜坡上。接着他们听到了那小狗叫起来了,不是在搜寻嗅迹,而是在狂吠,约摸在一英里以外,接着那黑人发出了高声吆喝的声音,他们便知道小狗又失去嗅迹了。那是在沟边出纰漏的。他们在堤岸上来回搜寻了一个多小时,仍未能把托梅的图尔乱七八糟的嗅迹理出个头绪来。*后连布克大叔也不抱希望了,他们开始朝大宅赶回去,那只小狗现在也上了坐骑,就趴在黑小子身前的骡背上。他们正来到通向黑人村的巷道上;他们顺着屋脊能看见休伯特先生的大宅如今已一片漆黑,这时,小狗突然叫了一声,从老杰克背上跃下,一落地就急急奔跑,每蹦一下就叫一声,布克大叔也下了马,而且不等孩子双脚完全退出铁镫就一把将他从小马背上拽下,两人也奔跑起来,一直跑过好几座黑黑的小屋,朝小狗蹿去的那座跑去。“咱们找到他了!”布克大叔说,“快绕到后面去。别喊;就给我抄起根棍子朝后门猛敲,声音要响。” 事后,布克大叔承认是他自己不好,他竟忘掉了即便是小小孩也该明白的事理:但凡惊动一个黑鬼时千万别站在他面前或是背后,而是要永远站在他的一边。布克大叔居然忘了这档子事。他对准前门而且就站在门口,还有那小狗梗在他前面,只要新吸进一口气就像叫救火和救命似的叫;他说他光知道小狗尖叫一声,转了个回旋,托梅的图尔便已在狗的身后了。布克大叔说他都没看见门是怎么开的;那只小狗仅仅尖叫了一声,便从他腿缝里钻过去,接着托梅的图尔飞跑着从他身上跨过。他甚至都没有颠跳一下;他撞倒了布克大叔,没有停止奔跑,便在布克大叔着地前扶住了他,他托住布克一只胳膊,把他拉起来,仍然没停下,把他往前拖了总有十英尺,一边嘴巴里说,“留神这儿哟,老布克。留神这儿哟,老布克。”然后才把他扔下,兀自往前跑。到这时,他们连小狗的叫唤也完全听不见了。 布克大叔倒没有受伤;就只是托梅的图尔把他四脚朝天撂倒在地时一下子气儿回不过来。不过他后面兜里揣着个威士忌酒瓶,他省下*后一口原本想在逮住托梅的图尔时喝的,所以他不愿动弹,非得先弄清楚那摊湿的仅仅是威士忌而不是血。因此布克大叔稍稍转向一侧,松开身子,让孩子跪在他背后把碎玻璃从他兜里掏出来。接着他们朝大宅子赶去。他们是步行去的。那黑小子牵着马赶了上来,不过谁也不提让布克大叔再坐上去。他们现在根本听不见小狗的声音了。“他跑得很快,不错,”布克大叔说,“可是就算是他,我也不信能赶上那杂种狗,我的天,今儿晚上真是够瞧的呀。” “咱们明天准能逮住他。”孩子说。 “明天,去你的吧,”布克大叔说,“明天咱们已经回到家了。休伯特·布钱普或是那黑鬼,不管是谁吧,只要把脚踩进我的地,我就要让上头以非法侵入和流浪罪把他们逮捕。” 宅子里一片漆黑。他们能听见休伯特先生此时鼾声大作,就像是在一门心思对着房子练习竞走。可是他们听不见楼上有任何声响,即使进入了黑黢黢的门厅,来到了楼梯底下。“看来她的卧室是在后面,”布克大叔说,“在那儿,她不用起床也能对着楼下的厨房吆喝。再说,家里来客人时,未婚的女士一定会锁上房门的。”因此布克大叔就在楼梯*低一级处坐下来,孩子便跪下来帮布克大叔脱下马靴。接着他也脱了自己的,并把靴子贴墙根放好,他和布克大叔便登上楼梯,摸黑来到二楼的过厅。这里也是黑黢黢的,还是听不到什么声响,除了楼底下休伯特先生的鼾声,于是他们一路摸黑朝前楼走去,直到摸到一扇门。他们听不见门里有什么声音,布克大叔试着转了一下门把,门儿开了。“行了,”布克大叔悄没声地说,“轻点儿。”他们这时稍稍能看出一点儿了,也仅能看出床和蚊帐的轮廓。布克大叔卸下背带,解开裤子的纽扣,来到床边,小心翼翼地往床沿坐下去,想松快松快,孩子再次跪下,帮布克大叔把裤子拉下来,他正脱自己的裤子时,布克大叔撩起蚊帐,抬起双脚,就翻身上床。这时,索凤西芭小姐在床的另一边坐了起来,发出了**下尖叫声。
作者简介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国文学史上*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原因为“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

24个比利
¥18.7¥39.0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伊豆舞女
¥24.0¥48.0 -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魔山(精装)
¥23.5¥59.0 -

钱德勒短篇侦探小说全集2:找麻烦是我的职业
¥11.8¥37.0 -

勒索者不开枪
¥12.2¥38.0 -

魔力的胎动
¥17.6¥45.0 -

春风沉醉的晚上
¥12.0¥40.0 -

小小小小的火
¥22.0¥52.0 -

陈忠实短篇小说选萃
¥14.1¥38.0 -

无人知晓
¥17.1¥45.0 -

悉达多
¥12.0¥28.0 -

山海经
¥20.4¥68.0 -

长安的荔枝
¥40.1¥45.0 -

比利战争
¥12.1¥39.0 -

想我苦哈哈的一生
¥16.0¥42.0 -

我这一辈子:老舍中短篇小说集
¥10.8¥36.0 -

偶发空缺
¥20.0¥57.0 -

额尔古纳河右岸
¥20.8¥32.0 -

十日谈-上下册
¥15.0¥37.6 -

局外人
¥10.6¥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