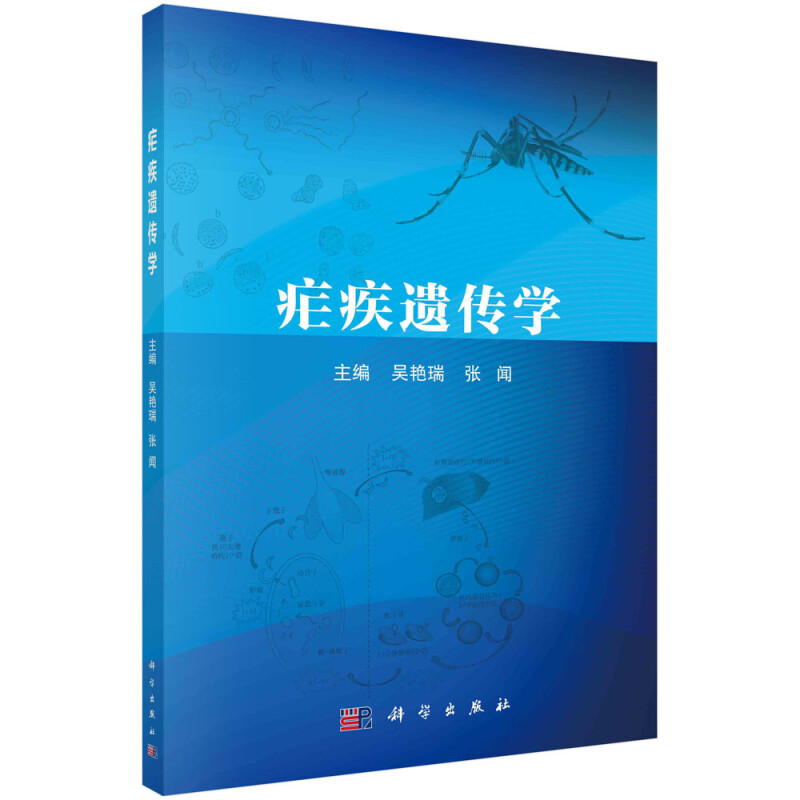- ISBN:9787030641748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26cm
- 页数:161页
- 出版时间:2021-11-01
- 条形码:9787030641748 ; 978-7-03-064174-8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从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角度来系统介绍疟疾的基本知识和研究进展。全书分为九章, 即疟疾简史、疟原虫、疟疾医学、蚊媒、疟疾基因组学、疟疾免疫、抗疟药物、青蒿素类抗疟药和药物抗性遗传。
目录
**章 疟疾简史 1
**节 早期人类疟疾 1
第二节 疟疾研究历程 4
第三节 疟疾防治历程 6
第二章 疟原虫 11
**节 疟原虫的分类 11
第二节 疟原虫的形态 14
第三节 疟原虫的发育 19
第四节 疟原虫的代谢 31
第三章 疟疾医学 37
**节 疟疾的病理 37
第二节 疟疾的诊断 42
第三节 疟疾的治疗 46
第四节 疟疾的预防 50
第四章 蚊媒 54
**节 蚊的分类 54
第二节 蚊的习性 59
第三节 蚊的免疫 63
第四节 蚊媒防治 67
第五章 疟疾基因组学 71
**节 疟原虫基因组 71
第二节 疟原虫功能组学 74
第三节 蚊基因组 79
第六章 疟疾免疫 82
**节 遗传抗疟性 82
第二节 疟疾的免疫应答 85
第三节 疟疾疫苗 94
第七章 抗疟药物 97
**节 传统医药学的抗疟药 97
第二节 抗疟药的种类 101
第三节 喹啉类抗疟药 102
第四节 叶酸代谢抑制抗疟药 115
第八章 青蒿素类抗疟药 120
**节 青蒿素的发现历程 120
第二节 青蒿素的化学合成 127
第三节 青蒿素的生物学合成 131
第四节 青蒿素衍生物 135
第五节 青蒿素复方药物 142
第九章 药物抗性遗传 146
**节 氯喹抗性 146
第二节 叶酸代谢抑制药物抗性 148
第三节 青蒿素抗性 152
第四节 多药抗性的扩散和避免策略 157
第五节 新药研发 160
参考文献 161
节选
**章 疟疾简史 疟疾( malaria)俗称打摆子、瘴气病、冷热病或间歇热,是疟原虫( Plasmodium)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疾病。疟原虫在雌性按蚊吸血时进入蚊胃,经过发育繁殖,在蚊唾液腺内形成大量的感染性子孢子。当雌性按蚊再次叮人时,蚊唾液里的子孢子就被注入人的皮肤组织内,可穿过微血管壁,随血液到达肝脏。疟原虫侵入肝细胞后完成裂体增殖,产生数以万计的裂殖子,离开肝细胞后进入血液,对红细胞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侵入和繁殖,当血液中的疟原虫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会引起疟疾发作。 疟疾发作的典型症状包括发冷、发热、出汗3个连续阶段,经过一段间歇期后再次发作。发作周期对应于疟原虫在红细胞内完成一轮增殖的时间,可为间日、三日或周期不定的发作。多次发作和经过治疗后,疟原虫逐渐被人体清除,疟疾症状随之停止。但如果有残存的虫体,还会在一段时间后重新繁殖,引起疟疾的复发。重症疟疾包括脑型疟、严重贫血、呼吸窘迫等症状,虽只占临床病例的2%,但病情凶险,尤其是脑型疟造成了90%的疟疾患者死亡,因此必须立即救治。 疟疾曾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目前仍位列热带病之首,主要流行于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东和南美等地区。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将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列为全球三大公共卫生问题,每年发布《世界疟疾报告》。2017年全球疟疾发病人数为2.19亿人,死亡43.5万人,其中非洲的病例占93%,5岁以下婴幼患儿约占60%。2017年疟疾的防治经费达31亿美元,全球仍有31亿人受到疟疾的威胁。 疟原虫有近300个种和亚种,分别感染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动物。感染人体的疟原虫有5种,分别引起恶性疟、间日疟、三日疟、卵形疟和诺氏疟,其中以恶性疟*常见,目前约占90%,其次为间日疟,其他疟疾少见。疟原虫必须生活在宿主体内,不能通过空气、水、食物、土壤、接触等方式传播,只能靠血液传输来感染新宿主。人体疟原虫的传播媒介是某些种类的雌性按蚊,因此,避免蚊虫叮咬和消灭传疟按蚊是防止疟疾传播的关键措施。 人体疟原虫的生活史和遗传机制很复杂,需要依次生活在雌性按蚊的胃腔、胃壁和唾液腺内,然后依次侵入人的血液、肝细胞和红细胞内,才能完成其配子生殖、孢子增殖和裂体增殖的世代交替。疟原虫在发育中产生很多种不同形态的虫体,自1880年 Laveran发现疟原虫和1897年 Ross证明疟疾通过蚊媒传播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人们才逐渐认清了疟原虫的生物学基础和疟疾发病的内在机制。而在此之前,疟原虫早已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节 早期人类疟疾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疟疾带来的痛苦和死亡可能超过了其他任何疾病。据估计,早期人类可能有50%死于疟疾。遗传学研究揭示,疟原虫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人类的遗传、进化和迁徙的历史,并在人体的基因组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一、疟疾溯源 有学者推测,疟原虫的始祖可能是一种浮游的单细胞藻类,常附在水中蚊虫的体表。雌蚊吸血时,这些藻类常常落入动物伤口中,然后死去,但这种藻类终于有一次在动物伤口处活了下来,演变为嗜血寄生虫。*早的疟原虫化石记录可以追溯到3000万年前,因为在那时形成的一些琥珀中,发现蚊的胃壁上有几个类似疟原虫卵囊的寄生物。 疟原虫与智人的**次接触可能发生在20多万年前的部落火堆旁,此前的“人体疟原虫”由猿类和古人类供养。*早的人类疟疾是三日疟,三日疟原虫对人体并不适应,只能感染血液中不到1%的衰老红细胞,虫体发育缓慢,潜伏期长,只有在夏季,当蚊虫的体温超过20℃时,三日疟原虫才能在蚊的寿限之内勉强发育出感染性子孢子。遗传学研究表明,三日疟原虫是*早的人体疟原虫,由于它们的适应机制不够完善,一直以来只能勉强维持着物种不被灭绝。 间日疟原虫在气温逐渐升高的冰河期之末出现,并进化出新型蛋白质,能有效侵入人类的幼红细胞,感染后只需3天就能产生感染性配子体,蚊虫期发育也较短。间日疟原虫对早期人类宿主进行了残酷的筛选,使很多部落灭绝。到了大约6万年前,少数非洲人发生了 Duffy抗原的阴性突变,使红细胞的表面更平滑,各种疟原虫难以侵入。这些 Duffy抗原阴性人群在非洲获得了生存优势,并扩展到阿拉伯半岛和中亚。从大约1万年前开始,由于 Duffy阴性抗原的普及,间日疟退出非洲,使非洲处于数千年无疟疾的平静状态。 在非洲之外,大多数人是 Duffy抗原阳性,间日疟广泛流行。有人认为,早期 Duffy抗原阳性人群向北迁移,动力之一就是为了到更冷的地方去躲避疟疾。在温带,按蚊体内的疟原虫熬不过冬天,但间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进化出休眠子,可在肝细胞内休眠数月,然后在气候转暖后启动生长繁殖,导致疟疾的复发和传播。间日疟原虫可以长期折磨被感染者,常在夏秋季节引起疟疾的暴发性流行。 恶性疟在4000多年前兴起于非洲中部的雨林村落。当地的班图人不养牲口,而是毁林种植地瓜和大蕉,导致阳光直射的地面上杂草丛生。一种按蚊来到地面的雨水洼里产卵,避开了林中的天敌,得以大量孳生。随着村落人口增多,这种按蚊演变成专门吸人血的新蚊种,称为冈比亚按蚊。恶性疟原虫原来缺少蚊媒,经过适应性改变后,转而以冈比亚按蚊为宿主,并攻克了非洲人的 Duffy抗原防御。恶性疟原虫不仅感染力很强,而且免疫逃避机制多样化,因而致死率很高。非洲人在经历了数千年无疟疾的平静之后,恶性疟原虫的兴起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二、古代疟疾 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各文明古国都有关于疟疾的大量记载。这些早期描述虽不可能道出疟疾的真正病因,但已能清晰分辨疟疾患者的症状,并知道疟疾常发生在温暖潮湿地带,某些文献还给出了有关疟疾防治方法有价值的信息。 苏美尔和古埃及的疟疾记载可以追溯到4700年前,苏美尔人认为疟疾是由“瘟疫之神”涅伽尔带来的。至今保存*早的疟疾病例是两具3500年前的木乃伊。经 DNA及计算机断层扫描( CT)检查揭示,公元前14世纪的图坦卡蒙法老并非死于传说中的谋杀,而是死于疟疾。 古印度人在3500年前就称疟疾为疾病之王塔克曼。吠陀圣人在2000多年前对疟疾的描述颇为准确:“冷酷的塔克曼使人战栗,继而高热,让人畏惧,他可能第二天回来,或第三天回来,或第四天回来。”印度是疟疾的重灾区,1942年疟疾患者曾多达1亿人,20世纪50年代的抗疟疾运动曾取得短期成功,1961年患者减少到5万例,但1976年又回升到600多万例。2017年印度报告959万例疟疾,占非洲以外疟疾病例的50%。除印度之外,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和邻近的东南亚地区也是传统的疟疾多发地区。 古希腊人很早就知道间歇热常在收获季节暴发,诗人荷马称之为“罪恶之星(天狼星)的热病诅咒”。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将间歇热描述为“沼泽地区的常见病”,并分为第三日发热(间日疟)和第四日发热(三日疟)两种类型,还将热病与脾大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曾统一希腊,占领埃及,荡平波斯帝国,远征印度河流域,使古希腊文明得到广泛传播,但他却在33岁死于疟疾。 古罗马的兴衰与疟疾有着密切的关系。始建于2700年前的罗马城一直流行间日疟,本地人对疟疾已形成了一定的免疫力和有效的防治文化,而外来军队攻打罗马时,却屡屡在城外的沼泽地带被疟疾击退,得到疟疾“护佑”的罗马被称为“永恒之城”。然而从公元3世纪开始,繁荣的罗马吸引了地中海南岸开来的大量运输船,逐渐改变了当地的按蚊分布,恶性疟在公元4世纪开始暴发,并迅速击溃了罗马人的免疫力,尤其是儿童和外出劳动者的死亡率很高,罗马周边的农村几乎无人种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古罗马的衰落和灭亡。后来意大利人将 mala(恶)和 aria(气)两词合并为 malaria,专指疟疾,这个词在1740年被引入英语。 古印第安人在1.1万年前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由于当地缺少蚊媒,疟原虫无法生存,因此美洲曾是无疟疾的净土。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欧洲和非洲的船只将疟原虫和蚊媒带入美洲。据传说,在1630年,秘鲁总督 Chinchón的妻子染上疟疾,印第安人用一种树皮粉治愈了这位夫人,这种树因此被命名为金鸡纳( Cinchona)。由于疟疾患者众多,树皮被剥光,树皮粉供不应求,金鸡纳树一度濒临绝种。后来荷兰人花了30多年时间,终于在印尼的爪哇岛实现了金鸡纳树的大规模种植,随后垄断了这种药材的全球销售。1820年,法国医生 Pelletier和 Caventou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纯了抗疟疾成分奎宁,又名金鸡纳霜。 三、中国古代文献 中国3600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已有“疟”字,其繁体为“虐”加一个“疒”字头,刻画出疟疾的痛苦。2000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 素问》,篇三十五为疟论,开篇就对疟疾作了精彩的描述:“黄帝问曰:夫痎疟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何也?岐伯对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素问的篇三十六为刺疟论,将疟病分为14类,各有其不同的症状和针刺疗法,开篇写道:“足太阳之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熇熇暍暍然,热止汗出,难已,刺郄中出血。” 除了《黄帝内经》,在《周礼》《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痎疟论疏》《瘴疟指南》等古代医书中,均对疟疾的症状、流行和治疗作了较详尽的描述。关于抗疟药方,《神农本草经》有治疟恒山(即常山)的记载,曾被认为是国内外*早的抗疟药,其有效成分常山碱的化学结构在1950年查明。但在更早(公元前168年)的西汉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已有青蒿治疾病的记载,因此青蒿可能是*早使用的抗疟药。值得一提的是,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有“治寒热诸疟方”,第二方即为青蒿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为后来研制青蒿素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于“瘧”字,《康熙字典》收录了很多古籍记载,其中包括:《说文解字》虐亦声,鱼约切;《玉篇》或寒或热病;《释名》疟,酷虐也,凡疾或寒或热耳,而此疾先寒后热,两疾似酷虐者也。《礼书纲目》卷五十五,寒热不节,民多疟疾。有趣的是,康熙皇帝本人在1692年御驾亲征噶尔丹时染上疟疾,几乎送命,*后却是用法国传教士从印度带来的金鸡纳粉治愈的。 第二节 疟疾研究历程 古人认为疟疾是恶浊瘴气引起的疾病,直到19世纪末才找到了疟疾的真正病因,又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才基本搞清了疟疾的复杂致病机制。进入21世纪以后,得益于分子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新进展,人们对于疟疾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本节从疟原虫的发现开始,简要介绍疟疾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方向。 一、疟原虫的发现 1880年11月6日,人类**次在显微镜下看到了疟原虫。法国军医 Alphonse Laveran在阿尔及利亚的部队医院里研究间歇热,他直接用间歇热士兵的新鲜血样进行显微检查,发现了一种新月形的虫体(恶性疟原虫的雌配子体),他还观察到从另一种较圆的虫体中伸出会游动的鞭丝(雄配子出丝现象,图1-1)。他检查了192例患者,在其中的148例患者中发现新月形虫体,而未发现虫体的患者都已经被奎宁治愈。 Laveran因发现疟原虫和锥虫而获得19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意大利学者在5年后证实疟原虫的发现,并描述了多种虫体的差异,提出这些寄生虫在红细胞中进行无性繁殖,而人体发热是由红细胞破裂后释放虫体导致的。1890年 Grassi和 Feletti命名了间日疟原虫和三日疟原虫,同年 Sakharov、Marchiafava和 Celli鉴定了恶性疟原虫。至1918年已经知道,人类疟疾是由多种疟原虫侵入红细胞后繁殖而引起的病症,可分为间日疟、三日疟、恶性疟和卵形疟。 图1-1 疟原虫的发现者 Alphonse Laveran和他在1880年描绘的疟原虫 Lavera
-

临床常用百药精解-国医精粹口袋书系
¥9.9¥32.0 -

黄帝内经
¥29.9¥76.0 -

杏林传习十三经:伤寒论 注解伤寒论
¥20.1¥59.8 -

联袂药性赋白话解-国医精粹口袋书系
¥9.3¥18.0 -

彩色图解黄帝内经
¥17.9¥49.8 -

彩绘版国学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精装)
¥24.3¥76.0 -

中医入门必背歌诀
¥16.4¥38.0 -

外科急救常识图解
¥4.7¥4.0 -

脉因证治
¥6.3¥13.0 -

国医大师张磊中医基础理论讲稿
¥14.7¥39.8 -

杏林传习十三经:灵枢经
¥14.7¥39.8 -

杏林传习十三经:脉经
¥14.7¥39.8 -

本草纲目
¥25.3¥76.0 -

伤寒论
¥12.7¥13.0 -

常见急救常识图解
¥4.7¥4.0 -

中医专家大讲堂
¥17.1¥39.8 -

成方切用
¥15.2¥39.0 -

内外伤辨惑论-局方发挥
¥4.9¥5.0 -

扶正祛邪抗癌瘤
¥7.0¥16.0 -

中医基础理论
¥12.3¥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