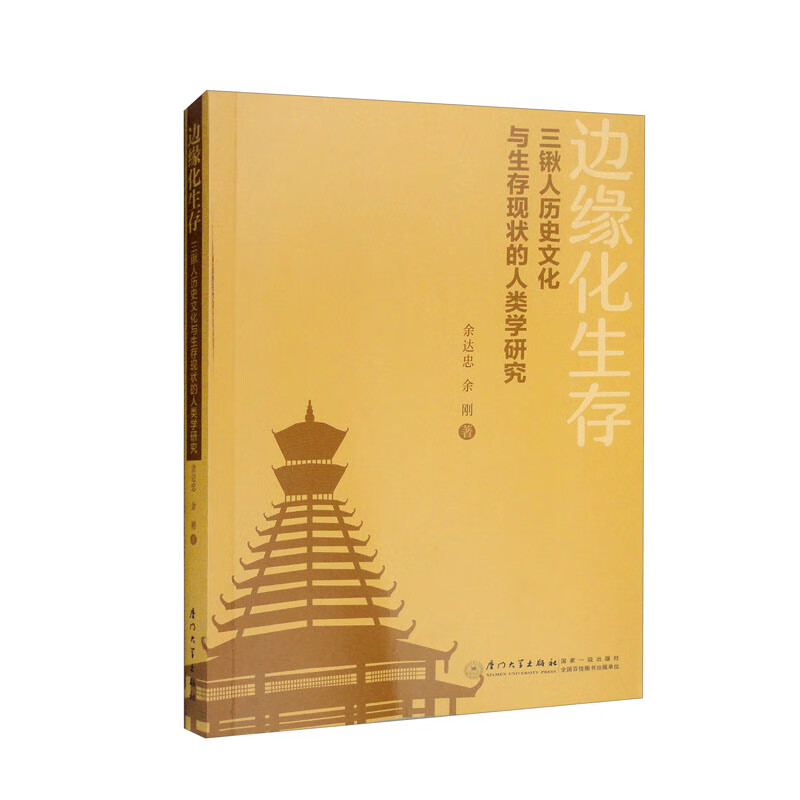- ISBN:9787561586341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24cm
- 页数:322页
- 出版时间:2022-10-01
- 条形码:9787561586341 ; 978-7-5615-8634-1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扎实的人类学田野调研,从区域史切入,将三锹人二百多年来的生存发展置于黔湘桂边区多族群互动环境和清水江流域山地开发的封建商品市场环境中考察廓析,对三锹人的形成、族群意识、族群认同、迁徙落寨、生计方式、婚姻习俗、社会交往、生存现状等进行细致描述和深入分析;从核心与边缘的新视角认识族群、族群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指出元明清时期黔湘桂边区的形成过程和各族群生存互动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形成的缩影。全社会有责任对处于边缘状态和贫困状态的三锹人予以更多关注和关怀。
目录
**章 黔湘桂边区的开发、多族群社会的建构与三锹人的形成
**节 作为地理与文明边缘的黔湘桂边界区域
第二节 黔湘桂边区的开发与多族群社会的建构
第三节 上、中、下三锹:作为地域和人群符号的三锹人的形成
第二章 三锹人的族群意识与族群认同
**节 三锹人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
第二节 族群认同的建构与消解:一座三锹人村落的当代裂变
第三节 岑趸村九组:三锹人都市生存的人类学考察
第三章 三锹人的迁徙落寨和生计方式
**节 清水江流域的开发和三锹人的迁徙
第二节 族际居住隔离:三锹人的迁徙落寨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第三节 三锹人的生计方式:吴相宇家族发展史
第四章 三锹人的婚姻习俗、婚姻圈和婚姻生态
**节 三锹人的恋爱与婚姻习俗
第二节 三锹人的社会交往与婚姻圈
第三节 现代化进程中三锹人婚姻圈的解体与婚姻生态的失衡
第五章 多族群社会中三锹人的祖先崇拜和丧葬习俗
**节 神圣的神龛:多族群社会环境中三锹人的祖先崇拜
第二节 “交拿”与“走亲”:三锹人丧葬习俗的人类学分析
第六章 三锹人的语言、语言交际和社会秩序的建构
**节 会说三种话的人:汉锹、侗锹、苗锹
第二节 三锹人的语言交际和社会秩序的建构
第七章 三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现状
**节 边缘性生存:三锹人的生存环境
第二节 边缘化生存:三锹人的生存现状
第八章 生态性贫困与社会性贫困:三锹人生存困境的人类学思考
**节 生态性贫困:三锹人生存困境的生态人类学思考
第二节 社会性贫困:三锹人生存困境的社会人类学思考
结语 走出生存困境:脱贫攻坚中三锹人的期待
附录 三锹人族属的调查报告
参考文献
后记
节选
人是以群体为单位生存的社会性存在,是在与不同群体的互动和冲突中发现自身的,人类社会生活面的不断扩大,群体与群体间的交往就越来越不可避免,这就由此形成了早期的氏族和部落,赋予人类必然具有的一种社会归属感。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说:“人类行为的另一个遗传特质是对*初归属的集体有着强烈的本能性冲动。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大部分社会性动物中。如果被强制性地孤立于群体之外,个体会陷入长久的痛苦中,并有可能走上疯狂之路。一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比如在他所属的部族中拥有的地位,是他个性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给成员以优越感。”①人类必须生活于群体中的事实,以及群体间必然发生互动和冲突的结果,决定了在人类社会中,族群的存在几乎是作为人类存在而与生俱来的现实。 族群作为一个概念被使用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族群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则是一种社会存在。族群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其实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人类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与民族、民族国家始终是关联在一起的。 从19世纪开始,以欧洲为起点,人类社会开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始于19-20世纪的一场泛世界的政治文化运动,肇端于欧洲,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而影响到整个世界。迄今为止,全球普遍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说:“从根本上说,这种有计划的‘民族建构’是一种现代的过程,在1789年之前找不到类似的实例……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现代主义不仅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的现象。民族、民族的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整个‘民族国家国际’共同体都是现代的现象。”①现代化强化了世界更广泛深远的联系,具备了将不同文化身份和不同文化认同的人群聚集于一个共同的空间,或者通过印刷科技的形式创造出一个具有无限想象力的空间的可能性。印刷资本主义的这种超越以往传统时代的超强的传播性表面上将世界带向一种同质性,而实质上,则是将各种人群间文化上的“异”更好地呈现出来,让世界呈现出一种显在的多元性状态。正是这种多元性和符号性上的林林总总,人和人群间的身份与认同就显得特别迫切和有必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阐述道:“只有当很大一群人能够将自己想成在过一种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算彼此从未谋面,但却当然是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前进的,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新的、共时性的崭新事物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出现。”②而这种对于远方、对于异域、对于从未谋面的很大一群人的了解、认知、认同或者拒绝、排斥、对抗,只有在印刷资本主义时代、在航海时代、在机械时代、在现代科技引导生活的时代才会大范围地发生,这也才会普遍地导致人们文化上和身份上的焦虑感,才会表现出强烈的认同上的需求。安德森进一步说:“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态观之,这种新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的登场预先搭好的舞台。”①正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泛世界的思潮,使得人们普遍渴望有明确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需要在文化上和身份上获得归属感和认同,由此,现代意义的民族就产生了。安德森也正是在这个视角中对民族进行阐述,将民族看成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开始,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②。在安德森和史密斯的理解中,民族始终是一个体现出鲜明政治诉求的人群实体,是一个既体现出文化的共同性,又更多地表达政治诉求的政治共同体,很多时候,民族与领土、疆界等国家概念联系在一起,是现代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而比民族低一个层级的族群概念,则更多地被看成是一个文化上的人群团体,强调和注重的更多是人们文化上的共同性和人们的文化身份,族群可以存在于民族之中.或者可以与民族并存。族群的存在,作为一种事实,是早于民族的。他们二位更多地倾向于民族是现代性的建构,而族群则可以包含和体现出历史性的延续。史密斯分别将民族和族群定义为:民族是“具有名称,在感知到的祖地上居住,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法律与习惯的人类共同体”。族群是“与领土有关,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与祖先,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民族占有土地,而族群则仅仅象征性地与之相连”。③
作者简介
余达忠,侗族,贵州黎平人。现任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三明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事人类学、客家文化、黔湘桂边区多族群文化研究。著有《走向和谐——岑努村人类学考察》、《侗族生育文化》、《侗族民居》、《原生态文化:资源价值与旅游开发——以黔东南为例》、《两个人的乡村——作家通信》(合著)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规划基金项目2项,省社科规划项目2项;发表学术沦文60余篇;获贵州省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三等奖,贵州省文艺奖三等奖,三明市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贵州文学乌江文学奖等。
-

两张图读懂两宋
¥16.0¥76.0 -

你不知道的古人生活冷知识
¥14.7¥49.0 -

清朝穿越指南
¥14.4¥45.0 -

人类酷刑简史
¥20.1¥59.0 -

万历十五年
¥16.3¥25.0 -

唐潮:唐朝人的家常与流行
¥23.1¥68.0 -

朱元璋传
¥14.0¥39.0 -

从三十项发明阅读世界史
¥11.7¥39.0 -

汉朝其实很有趣
¥9.7¥38.0 -

两晋其实很有趣
¥9.2¥35.0 -

胡同里的姑奶奶
¥27.8¥78.0 -

至道无餘蕴矣:梁漱溟访谈录
¥24.1¥68.0 -

创造圣经的城市
¥19.7¥58.0 -

中国近代史
¥6.0¥20.0 -

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
¥16.0¥45.8 -

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第七部
¥8.9¥29.8 -

硬核原始人
¥21.0¥65.0 -

中国通史
¥18.5¥45.0 -

谁是剽窃者:牛顿与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战争
¥15.8¥45.0 -

中国庭园记
¥13.5¥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