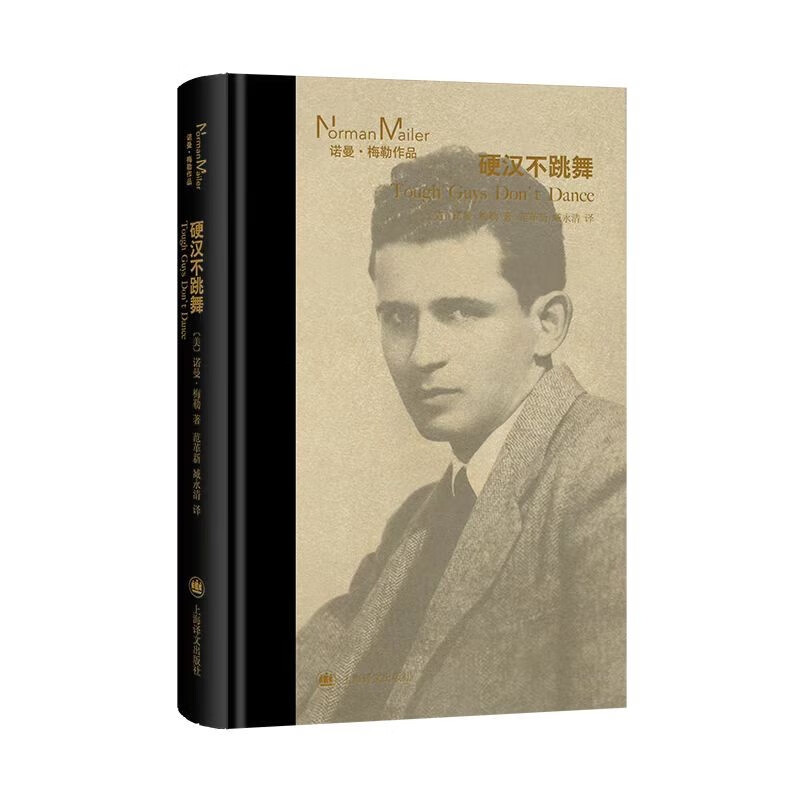- ISBN:9787532791255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350
- 出版时间:2023-05-01
- 条形码:9787532791255 ; 978-7-5327-9125-5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大众读者美国著名作家,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美国“全国文学艺术院”院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 两获普利策文学奖的文坛鬼才和数届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 上过前线,当过导演,参加过纽约市长竞选,还结过六次婚,育有九个孩子,同时也是 “硬汉文学”、非虚构写作的践行者与新新闻主义写作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一个集小说家、政客、文化名人、随笔作家、记者、文学批评家、诗人、导演、编剧、演员、社会活动家、运动迷于一身的时代偶像,梅勒毕生将写作当成一项英雄般的事业。 他不仅苛求自己与同时代的同行竞争,更把自己视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因此被称作“美国*伟大的当代作家”。一位与海明威并驾齐驱的重量级作家。1923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4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4年至1946年在太平洋地区服役;1948年写出了成名作《裸者与死者》;1968年,《夜幕下的军队》获普利策奖;1980年,《刽子手之歌》)再获普利策奖;2005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的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创作灵感日益枯竭的作家马登陷入了苦闷,终日饮酒寻欢。一日他邂逅一位美艳动人的金发女郎,与她一夜狂欢后却陷入了离奇凶杀案。他种植的地莫名出现一颗金发女郎人头,同时,他胳膊上的纹身、家中和车内的血迹、通灵朋友的证词都表明凶手非他莫属。诸多巧合令马登毛骨悚然,而破碎混乱的记忆又让他茫然无措。为揭开凶手之谜,马登卷进了爱欲、血腥、谋杀的漩涡。然而,每一条蛛丝马迹都显示,身边每个人都与凶杀有难以分割的关系,每个人都不排除凶手的可能……包括他自己。死者是谁?凶手是谁?蒂姆陷入了理智与疯狂的双重煎熬。?
节选
是薄雾还是枯叶 抑或是死人—十一月之夕。 —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 有些错误太严重了,我们无法懊悔…… —埃德温·阿林顿·鲁宾逊 一 天快亮时,如果海滩是低潮,我一睁眼就能听到海鸥的叫声。碰上天气糟糕的早晨,我总会觉得我像是死了,鸟儿在啄食着我的心。之后,我闭上眼又眯一会儿,再次醒来的时候,潮水就要漫上海滩了,迅疾得像太阳落山时小山上那向下滑落的阴影。不久,**批海浪就要开始撞击我窗台下面平台的挡水墙了。巨大的冲击不时从防波堤那边升起,涌向我肉体中那*隐秘的航线。轰!海浪打在防波堤上,我开始像个飘零者孤独地守在漂于昏暗的大海之上的货船里。 实际上,我已经醒来,在我妻子逃走后的第二十四个清晨那令人凄凉的时分,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当晚,我会庆祝这第二十四个夜晚的,我独自一个人庆祝。可能已经证明了那是个蛮不错的时机。这事后的日日夜夜,每每在我冥思苦想,要为那几件可怕的事儿找一条线索时,我就试图拨开记忆的浓雾,回想在第二十四个夜里我会干出或没干出些什么事儿来。 可是,我*终还是没有想起起床后我究竟干了些什么。那天可能同往日一样。有则笑话说,有个人头一次去看一位新来的医生。当医生问起他每天都做些什么时,他张嘴就来:“我起床,我刷牙,我吐了,我洗脸……”这时医生问:“你每天都吐吗?” “噢,那当然,医生,”那位病人回答说,“难道别人不吐?” 我就是那个人。每天早晨,吃完早饭后,我并不去点着烟。我顶多把烟叼在嘴上,然后准备呕吐。丢了的老婆的那股臭味死缠着我。 十二年了,我一直设法戒烟。正像马克.·.吐温说的那样—现在有谁不知道那句话?—“戒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都戒了一百次了。”我过去总觉得这句话就是我自己说的,因为我确实在十个不同的场合戒过十次烟,有一次一年,有一次九个月,还有一次四个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戒烟,几年来足有一百来回,可我还是又抽了起来。因为,在梦里,或早或晚,我总要划根火柴,点着烟,随着**口烟,我吸进我所有的渴望。我感到我被牢牢地钉在这种欲望上了。那帮魔鬼困在我胸中,高声尖叫,再抽上一大口吧。改改习惯吧! 所以我可知道上瘾是个什么滋味儿。一头野兽咬住了我的咽喉,它们在我的肺脏里翻腾。我同那头野兽搏斗了足有十二年,有时我打跑了它。我通常是在令自己也令他人罹遭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得胜的。因为不吸烟时,我脾气就变得相当坏。我的反射作用就在划火柴的那个地方,而且我的大脑往往会把那些让我们保持冷静沉着的知识(至少,如果我们是美国人的话)忘个一干二净。不抽烟带来的痛苦使我可能去租一辆小汽车开开,我从不注意它是福特牌的还是克莱斯勒牌。这可以被看成结束戒烟的前奏。有一次,我没抽烟,同一位我热恋着的名叫玛蒂琳的姑娘赶了好长一段路,去见一对想过上一次换妻周末的已婚夫妇。我们让他们玩了个痛快。回来时,我和玛蒂琳吵了起来,我把小汽车弄坏了。玛蒂琳的内脏伤得厉害。我便又开始吸烟了。 我过去常说:“自杀要比戒烟来得容易。”可我又怀疑这样说是否正确。 就在上个月,二十四天前,我妻子溜了。就在二十四天前。这让我对烟瘾又有了新的认识。放弃爱情可能要比戒烟简单些。然而,当你向那爱与恨缠在一起的混合物挥挥手道声再见时—啊,那让人头疼的可靠的救命仙丹,那爱与恨的纠缠!—我说,结束你的婚姻同戒掉尼古丁一样费事,没什么两样,因为我可以告诉你,十二年过后,我开始憎恨那些又脏又臭的玩意儿,程度绝不亚于痛恨该死的老婆。甚至早晨起来的**口烟(它给我带来的满足曾经是我一辈子也不会丢掉它的原因。这个原因难以根除)现在也带给我一阵阵咳嗽。除了上瘾之外,什么乐趣都没有了,而上瘾仍是打在你心灵*底层的一个烙印。 我的婚姻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帕蒂.·.拉伦走了。如果我在知道她那些可怕的缺陷时还曾爱过她—甚至在我俩像一对快乐的魔鬼似的吸着烟,把几十年后可能会得肺癌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时,我总是觉得,在某个始料不及的夜晚,帕蒂.·.拉伦将成为我的末日,不过,即使真是这样,我还喜欢她。谁知道呢?爱情会刺激我们变得迷狂。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前一两年,我们一直试图改掉习惯。夫妻间的厌恶跟着季节的推移不断增长,直到将旧情全部耗尽。我开始讨厌她,讨厌早上那支烟,*终我真的戒掉了那支烟。只有在十二年后,我才终于感到我从我生活的*大嗜好中挣脱了出来。一直这样,直至她离我而去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我发现,失去妻子也是一次万分痛苦的旅行。 她出走之前,我整整一年没抽一支烟。正因为这样,我和帕蒂.·.拉伦可能会什么也不顾地打起来,但我*后还是连骆驼牌烟也不抽了。然而希望不大。她开车走后两小时,从帕蒂丢下的只剩了半包的香烟盒里,我又拿了一支棺材钉a。思想斗争了两天,*后还是又抽了起来。因为她走了,每天我都是在灵魂的骚动不宁中开始度日。天哪,痛苦的瀑布就要把我吞没了。伴随着这个不争气的习惯而来的是我与帕蒂.·.拉伦之间的每一点旧情都来噬咬我的心。在我嘴里,每支香烟都有股烟灰缸味儿,可我吸进去的并不是焦油而是我自己那烧焦了的肉。这就是抽烟与丢了的老婆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儿。 我刚才说过了,我想不起我是怎么消磨掉第二十四天的。记得*清楚的是,我打了个呵欠,想抽那**支烟,然后往下硬咽那口烟。过了一会儿,四五点钟后,我有时才能安安稳稳地抽起来,用烟烧灼我生活中的创伤(没把我自己当回事儿)。我多么渴望见到帕蒂.·.拉伦啊。在那二十四天里,我想尽办法不见任何人,待在家里,也不常洗漱,喝酒喝得好像我们血液的长河里流着的全是波旁威士忌,而不是水。我自己呢,要是用个不好听的字眼来形容的话,成了个邋遢鬼。 要是在夏天,别人可能很容易就会看出我处境的可怜,可 a 美国俚语,指香烟。 现在是晚秋,天总是灰蒙蒙的,镇子上一个人都没有。在十一月那些短暂的下午,你可以拿上个保龄球,往我们那条窄窄的主街(一条名副其实的新英格兰小街)的单向道上一扔,保证连一个行人或一辆汽车也碰不着。小镇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要是用温度计来量,寒冷些是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用温度计来量,马萨诸塞州那边的海岸还不如波士顿西边那几座石山冷)。它只是冰冷的海风与无底之寒两相交加的结果。那无底之寒存在于神魔小说那隐遁的心之中。或者,确实如此,它藏在降神会中。老实说,我和帕蒂九月末参加了一次降神会,其结果令人不安。那次降神会时间不长,却阴森可怖,结束时,又来了一次疯狂的尖叫。我怀疑,如今我失去帕蒂.·.拉伦,形单影只的部分原因是,就在那一时刻,有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无疑又让人厌恶的东西已附在我们的婚姻之上了。 她走后足有一个星期,天总也不变。十一月的天空冰冷而阴森,日复一日,都一个样儿。你眼前的世界灰蒙蒙的。夏天,这里的人口能达到三万,并且到了周末还会翻个番儿。好像科德角的汽车都驶到有四个行车道的国家公路上来了。这条公路的尽头就是我们住的那片海滩。那时,普罗文斯敦就同圣.·.特佩兹一样绚烂多彩了,但到了星期六晚间,它便脏得与贡内岛没什么两样。可是一到秋天,人都走了,小镇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现在,人口数量不似以前那样与日俱增,从三万一下子跳到六万,而是降到了*低限:三千。你可能会这样说,在平时那空荡荡的下午,居民的实际数量一定只有三十个男人加上三十个女人,而且他们也还都躲了起来。 在这个世界你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镇子了。要是你对人群过敏的话,那么在夏天,人口的稠密可能会把你憋死。而另一方面,如果你shou不了孤独的煎熬,那么在漫漫寒冬,你便会饱尝恐怖的滋味儿。从这儿往南与往西走不到五十英里a,有座马撒葡萄园,它目睹了群山的上长与风化,耳wen了大海的涨潮与退潮,经历了森林和沼泽的生长与死灭。恐龙曾路过马撒葡萄园,它们的骨头被深深地压进了基岩。冰川来了又去,忽而将小岛吸向北,忽而又像推渡船似的把它推到南边。马撒葡萄园地底的化石足有一千万年的历史了。科德角北岬却是一万年之前由大风与海浪吹打而成的。如果从地质学上的时间算,那还不到一夜工夫。我的房子就坐落在那儿,我就住在那块土地上,那里,狭长而起伏地覆满了灌木的沙丘盘旋地向上爬,直至科德角顶端。 也许这就是普罗文斯敦如此美丽的原因吧。它在黑夜里孕育而成(因为有人曾发誓说,普罗文斯敦是在一场黑暗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它的细沙浅滩在黎明时分仍然闪闪发光,散发出湿漉漉的芬芳,那芬芳是**次把自己奉献给太阳的原始土地所特有的。多年来,艺术家们接踵而至,想要将普罗文斯敦的迷人的光彩捕捉下来。人们把它比作威尼斯的环礁湖,要不就是荷兰的沼泽地。可等夏天一过,大部分艺术家就都走了。灰蒙蒙的新英格兰的冬天便穿起它那件又长又脏的内衣,灰蒙蒙的就像我的情绪,到这儿来惠顾 a 1英里约合1 609.344米。 我们了。这时,人们会想到,这片土地仅有一万年的历史,他们的灵魂还没有根基。我们没有古老的马撒葡萄园地底那残存的化石来镇住每一个灵魂,的确没有,没有我们灵魂的藏身之所。我们的灵魂随风飘舞,歪歪斜斜地飞向我们镇上那两条长街。这两条长街好似两位漫步去做礼拜的老处女,佝偻着盘在海湾。 如果这是一个公正的例子,能证明第二十四天我究竟是怎样想的话,那么很明显,我一直是处在一种内省、颓废、沮丧与坐立不安之中。二十四天没见到你又爱又恨的老婆了。毫无疑问,是害怕令你紧紧地依恋着她,就像你依恋那让你上瘾的烟屁股一样。我又开始抽烟了,我是多么讨厌那股香烟味儿啊。 那天,我似乎走到了镇子上,而后又转了回来,回到我那幢房子里—她的房子—这幢房子是帕蒂.·.拉伦用钱买下来的。在灰蒙蒙的下午将尽的时候,我独自一人沿着商业大街走了有三英里路,不过,我记不起我曾跟谁搭过话了,也记不起有多少人从我身边开车驶过,要我搭他们的车了。不,我记得我走到了镇子的尽头,走到了*后一幢房子与海滩相接的那个地方。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们就是在那儿上的岸。是的,他们不是在普利茅斯而是在这儿上的岸。 好多天来,我一直在反复琢磨这件事儿。那些清教徒们,在横渡了大西洋之后,所见到的**块土地便是科德角的峭壁悬崖。科德角后岸,拍岸的惊涛*汹涌时可卷起十多英尺a高。就是在 a 1英尺约合0.304 8米。 风平浪静的日子,危险也十分之大。无情的海潮会将船只卷上岸,而后把它们拍碎在浅滩上。是流沙而不是岸边岩石,在科德角,吞没了你的航船。听到波涛那永不歇息的咆哮声,那些清教徒们不知要有多么害怕。谁还敢乘着他们那样的小船靠岸呢?他们掉转船头向南驶去,那片白色的荒凉的沙滩仍旧是老样子,冷酷无情,根本就不像是海湾,仅只是一片无垠的沙滩罢了。于是他们又试着向北航行。然而有一天他们发现,海岸向西弯了过去,又继续弯向西南,甚至后来又弯向南边去了。大陆究竟在耍什么把戏?现在,他们又向东驶去,从向北航行算起,船整整走完了三个方位。难道他们是在围着大海的一个耳湾兜圈子吗?他们绕过一个小地角,找到避风处抛了锚。那是个天然港,确实,它就好像人们耳朵里面的耳孔,受到大自然的保护。在那儿,他们放下小舢板,划向岸去。纪念这次登陆的是一场瘟疫。依靠防波堤的前部堤坝才使镇子边上那片沼泽地得以逃脱大海的蹂躏。那儿就是公路的尽头,在科德角,旅游者*远也只能把车开到那儿。在那儿,他所能看到的便是当年那帮清教徒们登陆的地点。在他们上岸之后,阴晦的天气盘旋着,许久不肯离去,并且他们又发现,这儿猎物很少,可耕的土地也不多,于是仅仅住了几星期,他们便又向西航行,横渡海湾到了普利茅斯。 然而,他们是在这儿,在科德角,怀着发现新大陆后的恐惧与狂喜,首次登陆的。尽管它是新大陆,历史还不足一万年。还只是一堆散沙而已。在他们到达陆地*初的那些黑夜里,该有多少印第安人的鬼魂在他们四周嚎叫啊。 每当我走到镇边那片翠绿的沼泽地时,我就会想起那帮清教徒。在沼泽地附近,岸边的沙滩十分平坦,你一眼就能看到地平线上的那些船只,甚至都能看到那一排排露出地平线的半截桅杆。钓鱼船的驾驶台一个接着一个,看上去就好像行驶在沙滩上的大篷车队。要是我多喝了几杯的话,我就会发笑的,因为离**批清教徒染上瘟疫的地方不到五十码a—美国的诞生地—便是大型汽车旅馆的入口。这座汽车旅馆即使不比其他大型汽车旅馆丑陋,也绝不能说比它们漂亮。人们给这家旅馆起名叫“客栈”,表示对那批清教徒的敬意。它的柏油停车场有足球场那么大,同样表示向**批清教徒敬礼。 不管我怎么冥思苦想,关于第二十四天的下午,我所能想起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我走出家门,步行穿过镇子,思索着我们这片海岸的地质情况,想象着**批清教徒们的所作所为,再把普罗文斯敦客栈嘲笑一顿。之后,我想我可能是走回家去了。我躺在沙发里,忧郁的心绪始终缠绕着我。在这二十四天里,我总是好久好久地盯着这面墙。不过,真的,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绝不能忽视的,那天晚上,我钻进我那辆保时捷小汽车,驶向商业大街,我开得很慢,就好像我害怕那天晚上我会变成个小孩子。大雾漫天,一直开到望夫台酒家我才把车停下来。在那儿,在离普罗文斯敦客栈不远的地方,有一间黑得分不清本色的小松木板房,上涨的潮水在轻轻地拍打着房基。这也应当是普罗文斯敦的一种夺人心魄的魅力吧。 。。。。。。
作者简介
美国著名作家、两届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在美国文坛,梅勒被人们视为一个怪才,如果不是“全才”的话。他上过前线,打过仗;当过导演,拍过电影;参加过纽约市市长的竞选。他的作品之多创作期之长,让其他作家惊叹;他参政的热情之大,也许会让真正的政治家咋舌。几乎每一场政治运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身上贴满了各种标签:运动迷、随笔作家、记者、文学批评家。
-

生死场
¥7.6¥36.0 -

莫言的奇奇怪怪故事集
¥18.0¥59.9 -

地下室手记
¥26.9¥48.0 -

炖马靴-短篇小说30年精选
¥21.4¥49.8 -

长安的荔枝
¥36.5¥45.0 -

倒悬的地平线
¥12.6¥42.0 -

(精)苦妓回忆录(八品)
¥11.2¥35.0 -

月亮与六便士
¥9.0¥36.0 -

告白
¥11.0¥36.8 -

老人与海
¥5.0¥15.0 -

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18.3¥46.0 -

神秘列车之旅
¥15.7¥38.8 -

焦渴
¥14.7¥49.0 -

局外人-亲近文学大师.阅读世界经典
¥4.2¥12.0 -

烟与镜
¥15.9¥48.0 -

遮蔽的天空
¥14.7¥49.0 -

人性的因素
¥21.6¥65.0 -

安忆六短篇-短篇经典文库
¥8.6¥32.0 -

月亮与六便士
¥10.0¥38.0 -

沉睡的人鱼之家
¥11.9¥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