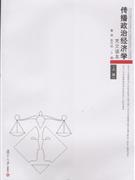
包邮传播政治经济学-(上下册)(英文读本)

温馨提示:5折以下图书主要为出版社尾货,大部分为全新(有塑封/无塑封),个别图书品相8-9成新、切口有划线标记、光盘等附件不全详细品相说明>>
- ISBN:9787309058000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855
- 出版时间:2009-01-07
- 条形码:9787309058000 ; 978-7-309-05800-0
本书特色
将近半个多世纪,伴随大众媒体在文化政治、意识领导与经济领域的分量有增无减,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各种学科,从文学与文化研究至公共政策与财经、法学,全面展开对话,从中演绎合适的实践路径。这本文集以传播政治经济学所主要关切的研究议题为核心,分别从该学派的历史起源与理论基础,方法思索与跨学科对话,广告的权力与受众商品的塑造,产权与盎格鲁—美国语境下的控制,资本主义整合的全球、民族与本土动力,转型的场域、能动性与进程等六个方面建构这个学派批判性的阐释路径。 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世界观,对于阶级的、民族与社会性别的关系,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有其深入与全面的观照角度,它与近代四百年的历史变迁,同步进展,为记录与更新社会的体质,贡献良多。将近半个多世纪,伴随大众媒体在文化政治、意识领导与经济领域的分量有增无减,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也得不成为活力生猛的知识范畴,它对各种学科,从文学与文化研究至公共政策与财经、法学、全面展开对话,从中演绎合适的实践路径。这本文集的编纂与出版,意义重大。通过赵月枝与曹晋博士的辛勤挑选,传播政治经济学从此将在神州大陆有效推进,全书搜罗既简约又繁复,读者逐步拾级、次第开卷后,信心与能力定会倍增。假以时日,学人当能发展独特眼界,对于流转眼前的各色传播现象,是否符合人们的需要,自有从容的领悟与定见。对于书报期刊至广电与互联网所组合成就的,由传媒所中介的信息、娱乐暨教育环境,究竟应该如何因革摔损益,学子必然能够从学习、对话、批评与建言的步骤中,逐步提炼自己的见解。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冯建三教授
内容简介
读本以传播政治经济学所主要关切的研究议题为核心,分别从该学派的历史起源与理论基础,方法思索与跨学科对话,广告的权力与受众商品的塑造,产权与盎格鲁—美国语境下的控制,资本主义整合的全球、民族与本土动力,转型的场域、能动性与进程等六个方面建构这个学派批判性的阐释路径。读本的论文组织以英美为主,兼顾其他国家与地区,主流批判中涵盖另类建设,突出对话,在传播与政治经济相互关联、作用的过程中关注多样化的论题,并贯穿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国家与区域的研究视野。
目录
节选
nbsp; 言
曹 晋 赵月枝
每一种学术思想的发端都不是孤立于社会情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其学
术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急剧扩张以及与之相抗争的社会运动的
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任何一个学科身份与地位的确立,除了其内在学理与研究路径的
充实与丰富之外,更重要的推进源泉还在于社会行动与实践力量的相互建构,以及学术
流派之间的对话与交锋。莫斯可(Vincent Mosco)以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
(spatialization)和结构化(structuration)切入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Mosco,1996);赵月枝
把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传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分析模式解构为四个相互关联的主要组成
部分,即提供语境(contextualizing)、图绘(mapping)、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与干预
(intervening)(赵月枝,2007a;赵月枝、邢国欣,2007)。这个读本,因篇幅局限,难以囊
括传播政治经济学范畴全部的认识论、方法论与全球各地本土实践的经验成果,仅以传
播政治经济学所主要关切的研究议题为核心,分别从该学派的历史起源与理论基础,方
法思索与跨学科对话,广告的权力与受众商品的塑造,产权与盎格鲁一美国语境下的控
制,资本主义整合的全球、民族与本土动力,转型的场域、能动性与进程等六个方面建构
这个学派批判性的阐释路径。读本的论文组织以英美为主,兼顾其他国家与地区,主流
批判中涵盖另类建设,突出对话,在传播与政治经济相互关联、作用的过程中关注多样
化的论题,并贯穿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国家与区域的研究视野。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一天起,资本主义在带来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社会财
富的高度积聚的同时,也带来了剥削、压迫、不平等和血腥,包括殖民暴力、法西斯主义、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文化和生态系统的侵蚀。因此,意识形态
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构建和合法化、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的问题,包括丹·席勒(Dan Schiller)在《罗伯特·A·布莱第的遗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
反法西斯起源》一文中所提到的社会文化传播系统是如何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直觉
(revolutionary instincts)平复和淡化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后马克思学者们上下
求索的问题。这些学者不断从各自社会情境的“当代性”出发,讨论马克思理论的内容
指向和实践品格。马克思理论文本历经着不同国籍的学者解读、诠释与实践,已在世界
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追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渊源,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其重要的源泉。从
卢卡奇(Georg Szegedy von Lukacs,1885—1971)、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
到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80),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为传播政
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卢卡奇是匈牙利现代卓越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一生曲折、
磨难重重,他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和重新界定奠定了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的地位。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敏锐体悟到马克思描述与揭示资本主义
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从商品开始,“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终
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中文
版《历史与阶级意识》,1995:170)。他以“物化”概念直接发挥厂马克思著作中的有关商
品拜物教的论述,并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经济物化,需要
政治上层建筑里的物化的保障,更需要意识形态领域里物化的掩盖、论证和说明,反之
亦然。物化意识对资产阶级所寻求的经济物化、政治物化以及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起
着论证、说明、合理化的作用,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来说,则起着把掩盖、隐匿、麻
痹变为似乎是反映现实本质的既定现实,使其丧失真正的阶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功能
和作用(中文版《历史与阶级意识》,1995:170--304)。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自己的政治运动实践反思为什么意大利北部的工人阶级不是必然的革命者?
他克服了其生存时代共产主义理论中流行的“经济论”与“唯心论”的弊病,而以“霸权
构成”的过程阐释统治阶级的历史因由,揭示了统治阶级为巩固其霸权统治而从事的意
识形态抗争过程。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髓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反对实证主义,包
括马克思主义包含的实证主义传统,认为启蒙运动是对理性的背叛而不是发扬,是这一
背叛导致了工具理性霸权,为垄断资本主义兴起铺平了道路。此外,他们也反对盛行的
自由主义观点,后者认为法西斯主义乃是一次特殊的历史偏离。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一
种充满危机的后期资本主义结构的逻辑延伸。所以,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勾勒出一个
既“科学”(可用材料验证),且具有“批判性”(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更持久、理性和公平
的社会秩序)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观(1ansen,2002:44--45)。该学派的**代学人霍克
海默和阿多诺(Max Horkeheimer&Theodor w.Adorno,1972)在1944年的《文化产业:
欺骗公众的启蒙精神》一文中指出(此文后来收入《启蒙辩证法》一书):在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即商品形式或商业模式的文化)的过滤,认为文化
工业的总体效果之一是反启蒙,作为不断进步的对自然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变成了大众
欺骗,转变成束缚自觉意识的工具。它妨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人的发展,不利于一个
民主社会的建设(Max Horkeheimer&Theodor w.Adorno,1972)。也就如詹森所说:霍
克海默和阿多诺揭示了文化工业已经侵入集体的无意识中,使得大众的希望、梦想、欲
望以及乌托邦式的幻想都带上了文化工业世界总部好莱坞的烙印。他们相信资本的支
持者不仅通过所有权控制着大众文化机构,也对人们的想象力操演着支配作用。他们
都认为20世纪的大众媒介和大众娱乐(也就是“文化工业”)已经深植于工业化民众的
意识中,使他们甚至无法想到抵抗,更不用说构连(articulate)社会解放变革的平台了
(1ansen,2002:45)。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风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理论
(Theory ofIdeology),他在《保卫马克思》中说:“意识形态就是意象表现(印象、神话、思
想或观念)的制度,它有自身的逻辑和严密性,这种制度在存在的社会内具有存在和历
史的作用。”(转引自曾枝盛,1990:164)这一定义重申了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特定
的逻辑和独特的结构),强调了意识形态的表象性质及其重要作用——“不是生产真正
的知识的作用(理论作用),而是对个人行动来说用做指导的模式和社会集团(实践社会
的作用)”(曾枝盛,1990:164—165)。也就是说,阿尔都塞强化了马克思所缺乏的部分,
“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扮演何种功能和角色,以及它如何内化为主体的规范等。除此之
外,他更在观点上提出关键性的转变,即他不再将意识形态视为‘观念’(ideas)或‘意
识’(consciousness),而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社会效应的具体(materiality)表现”(张锦
华,1994:101)。
在此基础上,西方文化传播领域的批判学术以宏观视觉和思辨性的分析揭示资本主
义制度下传播、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以及相关的社会权益关系问题。它着重关注传
媒技术发展的社会性,主流意识形态在媒介的形成及合法化机制,社会传播资源和话语
权在各阶层的分布,媒介与阶级、性别、种族的身份认同的关系,以及在自由民主的政治
体制下,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被维护、强化、抗争、挑战的过程等问题。批判学
术研究以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终极关怀,以构建克服不平等的传播制度和传播行为为目
标,追寻社会变革的知识动力,为个人与社会的解放创造源泉,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
色彩。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西方传播研究的批判流派之一,涵盖了上述学术取向与价
值理念(赵月枝、邢国欣,2007)。
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亦即媒介与传播系统及
内容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关系,并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
关系的影响。审视所有权、支持机制(如广告)和政府政策对媒体行为与内容的影响,强
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过程对传播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影响”(McChesney,2000:111)。
更进一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
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
式的;(2)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Schiller,
1999:90)。这样的学术视角也就是莫斯可所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探讨“传播如何在
社会中建构,形成传播渠道形态的社会因素,以及通过这些渠道传播信息的范围。这种
讨论有助于建立一个有关商业、国家以及其他结构势力如何影响传播实践的重要研究
实体,再者,这也有助于将这些结构与传播实践置于资本主义、贸易以及国际分工的更
宽广领域中”(Mosco,中文版2004:72),其“要求一种厂解那些接受现实观念与现实观
察的路径,从而剔除在很多理论中十分盛行的观点——那就是所有的解释*终都可以
被化约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经济的原因或者是文化的原因。反思政治经济学同样
强调社会的变迁、社会的进程,以及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趋势下,社会关系如何从社会
结构与制度发展而来”(Mosco,2006)。这些论述弥补了实证研究与宏观的社会分析相
脱节,抛开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权力关系抽象地研究传播现象与过程的弊端。
如果说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渊源,那么,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母体学科则是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美国学者奥斯卡·甘地(Oscar H.Gandy,Ir.)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种批判性的挑战》
中提到了四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取向:(1)以冯·米塞斯(Von Mises)和冯·哈耶克(Von
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他们坚持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假设,注重平衡和理性的选择;
(2)以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l·R·康芒斯(j.R.Commons)和I·K·加尔
布瑞什(1.K.Galbraith)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学派,他们注重权力在经济体制中的角色;(3)当
代或现代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主张阶级、资本这些概念作为一种强制的社会关系;
㈣公共选择理论的现代功利主义思想,他们发现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存在着所谓的
市场的作用”(Gandy,1992:23)。
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创立了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系统学说,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资产阶级的隐蔽结构(马
克思,中文版1974:181),斯密从价值论已经找到对资本雇佣劳动、利润、资本、地租等的
解释,但他从三种收入价值论直接简单地把因果关系相等同,即工资、利润和地租都是
决定价值的原因,而并非剩余经济的积累所致,这是斯密学说的局限性表现。另一位重
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 772—1 823)对斯密的三种收入论进
行了批判,他以为价值由劳动创造是一个既定的前提,不能因为它会再分为三种收入而
改变这一前提,斯密的失误在于把三种收入这个结果看成原因,并以之阐释价值的分配
问题。到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
工资、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等等当作前提”(马克思,中文版
1979:89),系统地概括了雇佣劳动者(主要是产业工人)的共同利益和意识,体察了被剥
削的工人阶级与依靠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抗,对经济矛盾有
了深刻的发现。正如冯建三教授所论:“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批判前两者的
马克思,他们都采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他们也都秉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具
有客观决定的基础。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差异,在于马克思宣称他发
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也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来自无偿占有部分的劳动成果(剥削的存
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则因阶级立场的限制,未见于此。”(冯建三,2003b:
105)具体而言,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较,在历史、
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等概念范畴方面都存在差异,如下表所示:
┏━━━━━━━━━━━━━━━━━━━━━━━┳━━━━━━━━━━━━━━━━━━━━━━━┓
┃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 ┃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 ┃
┣━━━━━━━━━━━━━━━━━━━━━━━╋━━━━━━━━━━━━━━━━━━━━━━━┫
┃历史变化:具有历史感,变化是指质的改变。其 ┃历史变化:历史已不再有本质的变化,有的是数 ┃
┃过程虽然缓慢,但仍可查知。举例:媒体历经主 ┃量上的增加,经济成长的正负起落,商业周期的 ┃
┃权控制到现在为资本家主导,未来仍有变化的 ┃荣枯盈亏。举例:媒体的变化只剩下新科技产 ┃
┃ ┃品取代旧媒体,如彩色置换黑白、数位置换 ┃
┃可能。 ┃ ┃
┃ ┃类比。 ┃
┣━━━━━━━━━━━━━━━━━━━━━━━╋━━━━━━━━━━━━━━━━━━━━━━━┫
┃社会整体: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层面 ┃社会整体:通过特定价格而表现的消费行为(如 ┃
┃彼此相关,既有冲突矛盾,也有扣连接续,因此特 ┃看特定报章、电视)是*重要的研究单位,既能 ┃
┃定(如媒体)时,不应拘泥学科门户之见,而应将 ┃存在,必有道理。市场价格反映出来的个人偏 ┃
┃媒体文本的生产机制、文本的内涵及文化的消 ┃好才是研究的对象,社会总体的偏好也就只能 ┃
┃费,合并考察。 ┃是个别消费选择的加总。 ┃
┣━━━━━━━━━━━━━━━━━━━━━━━╋━━━━━━━━━━━━━━━━━━━━━━━┫
┃道德哲学:研究者必然有其价值承诺,并且认定 ┃道德哲学:价值等同于企业经营效率的高低,资 ┃
┃从市场关系反映出来的价值,缺陷众多。比如, ┃本家*大的道德律令是利润的不断往*大化增 ┃
┃近用媒体资源的不平等,以及众多有价值的意见 ┃值。数量之众多已等同于多元。因此,英国 ┃
┃ ┃……600多家报纸,将近8 000家杂志……代表 ┃
┃或资讯,不是被边缘化就是无法见到天日。 ┃ ┃
┃ ┃了我们所可以想见的各种利益和观点。 ┃
┣━━━━━━━━━━━━━━━━━━━━━━━╋━━━━━━━━━━━━━━━━━━━━━━━┫
┃实践:根据前述价值而来的论述或社会、政治参 ┃实践:虽然声称价值中立,只进行“学术”研究, ┃
┃与活动,并不排斥实证的、量化的或一般可能称 ┃不涉政治。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新古典经济学 ┃
┃之为行政研究的政策研拟活动,也不排斥服务于 ┃作为当前价值表现的一环,其研究成果,以及其 ┃
┃产业界或政界,但前提是这些活动均得有助于前 ┃典范从事者的进出学界、政界、产业界,对于其 ┃
┃述价值的彰显、成为议题,乃至于缓慢实现。比 ┃免除遭受有效的挑战、稳定,乃至扩张,都在发 ┃
┃如,有关政府握有主要股权的电视台应当先走向 ┃生作用。比如坚持政府持有股份的电视台应当 ┃
┃产权的公有化之论述或游说活动。 ┃释出作为私人投资标的之论述或游说活动。 ┃
┗━━━━━━━━━━━━━━━━━━━━━━━┻━━━━━━━━━━━━━━━━━━━━━━━┛
莫斯可(2006)进一步阐释了政治经济学的要义:“而就卡尔·马克思来说,他认为
为了对*终导致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变迁过程的认识,政治经济学主要研
究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动力的认识,以及对资本主义与其他政治经济组织形式
的关系的探究。在19世纪晚期出现的经济学,即通常所谓的与政治经济学背道而驰的
正统经济学,为了将政治经济学变成‘经济科学’,其可以像物理科学一样,提供广泛适
用的(如果不是静态的话)理论解释,但对动态历史与社会变迁的关注不屑一顾。根据
经济科学的观点,经济学可以精确地解释购买者与销售者如何聚集在一起,并在市场上
确定价格,但是它不能解释社会与经济上的变迁决定价格的广泛过程。当前的政治经
济学家,成了与主流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异端,他们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以探
究社会变迁与转型为己任,集中关注诸如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与信息型经济转型的领
域。有关大众媒介与传播技术的研究则在这些探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被这些领
域所涵盖的产业成了今天社会经济的主要创造力量。”(Mosco,2006)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具体化,传播政治经
济学在北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发展过程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各
有偏重,互为补充,并在建设性的理论交锋中发展,阐述信息文化传播在资本主义经济
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双重意义。在北美,文化传播产业的高度商业化和信息传播在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这两位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传播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传播技术的演变
和劳动者对传播技术的掌握)和文化传播在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和消费资
本主义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斯麦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
传媒制度下,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媒介所生产的商品不是广播电视节目,而是
受众这一特殊商品。节目只是提供给顾客的免费午餐,目的是要将观众吸引到节目上
来,再把观众的眼球注意力卖给广告商。这样,观众就被当作商品卖给广告商,斯麦兹
在与欧洲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交锋的“盲点辩论”(blind spot debate)中阐明了
“受众商品理论”(Smythe,1977,1978;Murdock,1978)。斯麦兹认为,欧洲批判研究片面
关注传媒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作用,因此忽略了传媒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关键性的经济作用,忽略了垄断和消费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
媒体如何将受众制造成为商品,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中的“盲点”。他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大众传播系统应该提出的首要问题是,它们在服务于资本时有什么
样的经济功能,从而试图理解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延续中扮演什么角色”
(smythe,1977:1)。斯麦兹主张,通过广告促销,商品的价值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正是通
过传媒资本,其他的产业和商业资本得以实现其剩余价值,从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延
续。在这个意义上,斯麦兹认为,要理解传媒的经济学意义,也即“唯物”的意义,应该把
受众而不是文本定位于传媒资本的“产品”(赵月枝、邢国欣,2006)。加利(Sut Jhally)、
米汉(Eileen R.Meehan)和甘地(Oscar H.Candy,1r.)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和丰富了有关广
告在消费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地位和受众商品与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的构建关系。
与此同时,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奠基人赫伯特·席勒则描述了“二战”后,
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如何不但通过把信息文化传播领域集中发展为新
的资本积累场域,而且通过全球扩张和“文化帝国主义”策略来克服制度性的危机这一
角度,阐述了信息文化传播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意义。赫伯特·席勒(1969,中文版
2006)所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关于“传播体系的全球商业化”议题的敏锐批判认
为,全球商业化的传播体系是通过整合与兼并、跨领域经营与国际化三个相互联系的维
度实现的,作者列举了集团化形式之一的水平整合(horizontal,即横向集中)的实例——
英国*大的培生一朗文公司对企鹅图书公司的收购;以及集团化形式之二的控制整个
传播产业流通与消费的垂直整合(vertical)的案例——英国*重要的报刊出版商IPC与
里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高度集团化之后的巨无霸(Mega-Mergers)大公司直接参与
出版产品的生产、供应和销售,从而全面宰制文化市场的消费。如此格局,形成了市场
的绝对壁垒,竞争与准入的条件对小型出版公司来说是不敢问津的。这些因素也是型
塑南北差距的核心力量之一。在此基础上,丹·席勒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信息商品化
的本质,并通过对信息社会理论的批判捍卫了“信息社会”时代劳动价值论,而莫斯可、
萨斯曼与棱特等(Gerald Sussman,John A.Lent)则关注传播产业中的劳工状况、劳资关
系以及信息文化传播产业国际劳动分工中劳工的从属地位和他们争取权益的种种努
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还从制度经济学中的公用事业议题入手,视传播媒介为公共资
源,批判信息商品化过程和资本如何通过对公共资源——信息传播文化资源的剥夺
(expropriation)而导致对公共利益的侵蚀与损害,以及阶级分化与传播资源和技术手段
的不平等社会分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斯麦兹有矫枉过正倾向的“受众商品理论”曾招致英国学者的批评,后者认为此理
论流于“经济简化论”(economy reductionism)(Murdock,1 978;Garnham,1 979;Mattelart
&Schmucler,1985)。而英国学者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也从欧洲立场出发,以
同情的姿态对赫尔曼和乔姆斯基(Edward Herman and Noam Chomsky)影响深远的“宣
传模式”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设性的修正。在这一模式中,西方媒体由于广告资助、
资本所有权、政府信息源和强势利益团体信息干预等结构性因素以及反共意识形态的
影响,起到了为精英统治制造共识的作用。然而,与某些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
曲解和误读相反,大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有关文化传播领域商品化过程和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分析中力图避免机械的决定论(determinism,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和经济简约论的偏颇。他们不但强调社会冲突和抗争在这些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
及这一过程的未完成性,而且指出资本把信息文化传播领域作为*新积累场域的“机会
主义”性质(Schiller,2007)、其危机四伏的状态和加利(Sut Jhally)所指出的消费资本主
义制度的脆弱性。正因为如此,这个读本在多篇文章中,尤其是在*后一部分的文章中
强调公共利益原则、专业主义精神、另类媒介以及劳工、国际市民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
会民主化和社会正义力量对资本逻辑的调节、抗衡和在不同层面与场域正在进行的超
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的各种努力。
同时,政治经济学者们不仅强调抽象的“资本逻辑”的作用,而且在分析中关注国家
和政策机制的重要作用。例如,在他们的著作中,赫伯特·席勒和丹·席勒反复强调美
国国家在推动文化信息产业的商品化和国家通过管制机制和法规行使资本积累保证者
的基础性角色。他们指出,美国公司在信息技术方面几乎所有的创新与发展都有美国
国家军工研发的投入。而正是这些投入使美国的信息产业有了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和
市场竞争力。随着信息传播资本势力的壮大,信息化资本主义的“酋长”们对国家政策
的走向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作为回应,美国国家把这些要求发展为国策推广到美国国
内外。国家干预在信息文化传播的加速商品化过程中起着关键而持续的作用,这包括
国家对研发持之以恒的投入,对信息传播产业放松管制,对公共信息的私有化的推进,
对信息领域的私有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的强化,以及使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更有利于
信息文化传播业所属的服务业(赵月枝,即将出版)。在这一读本中,英国研究者弗雷德
曼(Des Freedman)、美国学者古贝克(Thomas Guback)、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卡拉布里斯(Andrew Calabrese)、贝蒂格(Ronald Bettig)、葛本纳(George
Gerbner)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与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动态相互构建关系,
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批判学术中的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在英国,詹姆斯·库瑞(1ames Curran)在《资本主义与报业控制》这一传播政治经济
学的经典文献中展示了报业市场自由化的政治意义,即资本家阶级通过改变报业的经
济基础来建立本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的政治目的。这项以英国报业史为背
景的研究表明,英国历史上对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对报业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一种
简单的经济行为,更不单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叙事中所说的新闻出版自由对政府控制
的胜利。詹姆斯·库瑞对英国议会就此问题的辩论的分析证实,英国统治者中的改革
派希望通过全面对资本开放市场来达到对社会话语权实施有效控制的政治目的。当
时,英国劳工阶层正通过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己的话语空间,冲击现有
的精英话语体制。在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地下刊物及其声音的问题上,一部分统治精英
主张用政府的力量来“堵”,而另一种策略则主张放开市场,通过资本的力量来达到支配
主流话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的。道理很简单,作为一般原则,传媒资本与广告商是不
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没有消费能力的下层劳工阶层的报刊注资和在这些报刊上大量
投入广告费的。在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中,这些声音会“自然而然”因为没有资本的青
睐而被边缘化。这一策略在辩论中以及随后的政策与事实发展中获胜了,因此,在一个
开放的市场里,广告成了事实上的报刊执照颁发机构。这一有关传播业中资本的所有
权和广告商资助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支配意识形态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如下论段及其实现机制提供了雄辩的实证: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卜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
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马克思,中文版,1960:52)詹姆斯·库瑞
的奠基性研究与斯麦兹的见解以及这个读本在广告一节中收录的北美学者的各项研
究,尤其是贝克(c.Edwin Baker)关于广告对报业结构和内容的影响的研究相得益彰。
得益于“盲点辩论”,英国传播学者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有意识要
超越机械的决定论和经济简化论,在《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贡献》论文中集中讨论了
精神生产与资本主义商业生产之间的重叠关系,把政治经济学引入文化工业的分析,探
索文化的剩余价值的汲取与分配。尼古拉斯·加汉姆认为文化工业“运用了特有的生
产方式和行业法人组织来生产和传播符号,这些符号以文化商品和服务为形式,虽然不
是一律作为商品”(Garnham,1990:155—156)。当然,他的这种领悟是建立在强调“分
析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利结构的关系,而且,尤其是关注分析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
体系的独特性”(Garnham,1990a:7)基础之上。同样,英国学者戈尔丁和默多克(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在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阐述中也强调了政治经济分
析与意识形态分析、制度分析与内容分析的有机结合。
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意味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视角。同时,跨国资本在全
球的扩张过程又必然与民族国家和本土文化有同化、吸纳、妥协和抗争等复杂关系,而
传播政治经济学本身在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性则意味着非西方国家背景的学者在发展本
土化的政治经济分析方面有广阔的空间。在本读本的国际部分,芬兰学者诺顿斯壮
(Kaarle Nordenstreng)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结盟国家争取国际信息和传播
新秩序运动的努力和挫败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拉美学者马丁一巴贝娄(16sus Martin—
Barbero)对美国强势商业文化在拉美的扩张和拉美本土商业文化发展过程有深度的经
典描述,而有非洲背景的加拿大学者阿哈森(AmiD_Alhassan)则通过把后殖民国家作为
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分析单位和理论构建对象来丰富和拓宽基于西方的主流传播政
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就亚洲而言,萨斯曼(Gerald Sussman)与棱特(10hn A.Lent)这两
位美国学者就亚洲在全球传播秩序和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提出了问题,而两位有印度背
景的学者则分别从*基层的村庄和全球性的知识产权层面展示了政治经济分析在国际
传播领域的广泛发展空间。
总之,当代学者已经服膺了政治经济学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必要性。正如卡拉
布里斯(Andrew Calabrese)在《迈向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文化的政治经济学
“是在媒介政策与管制,以及‘新媒介’的发展前沿,检视我们所说的‘公共空间’的物质
基础,理解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新闻与娱乐产业”(Calabrese:2003:3)。当今世界,文化
传播已成了资本积累的新场域,意识形态控制成了缓减并克服社会政治危机的重要手
段。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产权、广告、市场与社会控制,而且意识到了文化工
业对公共利益与民主社会的操纵与损害。同时,学者们也在现实生活里,亲眼目击了技
术创新和全球化市场景观中,文化被生产、传播、消费的方式以及其导致的社会后
果——“*明显的、致命的、难以驾驭的阻碍当然是大众媒介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
工业已经形成的各种权力。在当前的媒介组织结构和公司经济对国家政治的挟制下,
至少在美国,想通过中性对话自上而下地改革国家政治完全是空想。新的媒介兼并不
断改变力量组合,使少数几个全球化传播公司越来越集中、整合、合作、控制着整个世界
的大多数媒介”,“此外,通过清除了解情况的公民所依赖的共享话语世界,新的便于用
户使用的媒介技术,后福特时代(Post-Fordian)的生产方式(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
的),以及个性化的市场技术指令,使公共领域的*后一点堡垒也岌岌可危”(Jansen,
2002:58)。贝蒂格(Ronald Bettig)在《法兰克福学派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指
出——“文化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的中心任务是检视资本的
逻辑如何型塑文化工业的结构和内容,作者指出——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内部“诠
释的转向”(interpretive turn)造就f一种经济、政治与传播体系之间关系的制度分析的
必要性。这一制度分析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工业扮演了一个重
要的压制社会变迁的角色”(Bettig,2002:84),贝蒂格还列举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观点进行阐述,经典地指出“资本主义霸权背后的真正力量不是
意识形态,而是强制性的资本的权力”(Bettig,2002:87),这也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文
化工业的认识的要领所在。这种权力不仅在传统媒体的结构与生产中淋漓尽致地表
现,而且在被大家认为众神狂欢的数字化时代,所谓权力已经被消解,使用者已获得充
分的媒介近用权,但曼索敏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权力在新媒体的生产与消费领域仍
然牢固,在新媒体的结构中也如此(Robin Mansell,2004:96—105)。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术流派的对话
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说:“在每一个理论体系中都隐藏着另外一个
体系在不断挣扎。因此每个体系都有一个噩梦,即那个被束缚的体系会破笼而出。”
(Gouldner,1980:380)。任何有创造力的学术,也都是批判性的学术,已形成的知识机构
和体系都需要在胸怀交流与修正的进程中发展其论述的有效性。正如詹森所言:“我们
应该认真对待当代认识论中所提倡的‘新的谦逊’(new humility):我们用这种谦逊为我
们的学术对话注入一种对新发现的接受,让我们能够欢迎而不是害怕越来越多发言者
加入这个对话并使得对话不断发展。比如,我们可以借鉴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
在愤怒的功能主义的僵化症把许多有意义的学术对话都结束之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对
后实证主义研究的探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跃而极富创造性的对话和学术探索活动。”
(Jflllsen,2002:248)
功能主义社会学把媒介看成现代民主的新工具,其在管制社会的过程中担负着关
键角色,而富有批判性思想的学者则对上述命题提出了质疑,拒绝传播新科技必然带来
民主,反而认为传播媒介和新科技革新是权力和控制的工具,并且导致社会不同群体或
是不同国家的劳动分工与地位区隔,深化了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20世纪40年代流亡
于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给予了有别于美国经验研究的批判性思考;20多年
后,兴起于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潮以新的强调意识形态来反对实证主义的方法;20世纪
6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对意识形态角色与本质的探索都建构了一种能够
与美国功能主义分析的假设相抗衡的理论,并为批判性传播研究的新形式奠定了基础。
在此读本中,米尔斯(c.w.Mills)、吉特林(Todd Gitlin)和霍尔(Stuart Hall)的文章从不
同的层面对美国实证主义方法论进了深刻的检讨。
如霍尔在《“意识形态”的重新发现》一文中所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是批
判传播研究中侧重不同的两翼。然而,随着文化研究从英国到美国的扩散和文化研究
对美国自由多元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接纳,两者在研究议程和政治取向方面的
分歧在20世纪90年代日益明显。莫斯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1996)、道格拉斯·凯
勒(Douglas Kellner)在《逾越鸿沟: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Kellner,1995b:102—
120)、冯建三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对话》(冯建三,2003:97—104)等研究
论述中都澄清了双方论争的内容与互相对话的必要性。在一定意义上,传播政治经济
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可以追溯到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1977年发表的《传播: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针对性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即文化马克思主义者)
在探讨媒体传播现象时,存在盲点,即他们的媒体研究只聚焦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功能,没有探讨媒体为资本服务的经济角色,因此,辜负了彰显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特点
的机会。1978年,默多克与戈尔丁(Murclock,1978;Golding&Murdock,1979)回应此
文,他们辩解说——虽然他们以政治经济学者自居,但认为达拉斯·斯麦兹的分析,抹
煞了文化研究者的价值与贡献,不仅不明智,并且也不正确,他们对于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及霍尔(Stuart Hall)等文化研究者的微词,在于后者在实际分析时,没有能
够遵照其在理论上的允诺,也就是产权、经济分析的必要与优先。尼古拉斯·加汉姆
(Nicholas Gamham)一开始就连续引用三位文化研究者的著作,指出他们都错误认识了
政治经济论,都将政治经济论等同于经济化约决定论(下层基础、经济决定了上层基础、
文化政治等),因为,虽然政治经济论者在分析时,仍然认定决定论的分析必须坚持,但
并不、也从不主张两者之间存在着简单的直线对应关系。
20世纪后半期至今,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在西方传播学术领域中颇有建树。,
当然,这样分类思考与叙述是为了暂时性地勾勒并比较主要学术传统,并不是要将“真
理”价值特别赋予某种取向的研究(曹晋、周宪,2006)。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
的历史渊源来说,同宗同祖,双方的交战不过是同室操戈而已。进入新世纪以来,彼此
已趋于融合与借鉴。一方面,传播业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构变迁强化了政治经济分析的
重要性和相关性;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议程的碎片化、文化研究所依附的后现代主义和
后结构主义的相对论认识论困境、许多研究者避重就轻和对文化商品消费者主观能动
性的盲目乐观而滑入“文化民粹主义”(cultural populism)和“语义学上的民主”f semiotic
democracy)的唯心主义泥潭也使这个领域的一些学者反思自己的研究取向(赵月枝、邢
国欣,2007)。例如,道格拉斯·凯勒(Douglas Kellner)在《错失的构连:法兰克福学派与
英国文化研究》一文中就提出,生产和政治经济学在*近很多文化研究的模式中被忽
视,但将文本插入文化生产和分配的系统有助于阐释文本的特征和效果,而这往往是单
纯的文本分析可能遗漏而且不予重视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和文化研究相对立的研究
方法,事实上它有助于文本的分析和批评。生产系统常常能决定哪种产品可以生产,指
出对于什么可以说、可以展示而什么不可以会有怎样结构上的限制,以及文本会产生怎
样的受众效果。而且,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网络是在利润和集团
霸权的驱动下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的。政治经济学虽然相当重要,如果我们想要全面
地理解媒介文化的性质和效果,就必须发展更多的方法来分析其更广泛的意义和效果。
实际上,文化研究看到了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的问题,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政治经
济基础的问题,两者都在探讨问题,只是面向不同而已。如果想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传播
现象与传播制度,必须构连两者才可以洞察其问的真理。
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与前沿探索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发达的和*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
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
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中文版1979:43)。因此,充分认识资本主
义传播体系也是学界的当务之急,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规模的增长与集中已经成为当
前的时代传播业的核心特征,全球传播体系的商业化、国际化,以及全球经济的重构突
破了传统产业分工,出版、广播、电信、信息服务日益交融,*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手段包
括生产、营销、金融以及会计等流程与技术已渗透到媒介的各个面向。另一方面,“当媒
介改革家们还陷于派系纷争的时候,媒介大亨们正不断兼并、整顿、融合。他们运用其
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改革’传播法,解除诸如联邦传播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这样的管制机构的指令,中断关于可进一步推进他们全球霸
权的国际贸易协定的公开辩论。如赫伯特·席勒早就指出的那样,随着全球化以及‘新
电子工业,工业生产厂址的迁移,以及迅捷的国际传播的同时发生,一个新形式的等级
组织结构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转引自Jansen,2002:58)。迈入21世纪,巨无
霸的“全球扩张”已经达到空前的状况,传播产业的商业化、私有化、集中化和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不是被削弱了,而是更加剧烈。“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思潮
正在支配冷战的公共记忆的形成,推动着全球化进程,利用它前所未有的权力维护它的
统治,并且应用霸权于未来大众媒介观之上”(1ansen,2002:241)。伴随西方传媒产业的
私有化、放松管制、集中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从传媒产业的政治经济结构入手,就传
媒商业化问题进行了透彻的批判研究,其领域主要聚焦于考察资本主义体制内,各类媒
体在经营中过度强调市场因素和盈利性因素(广义的商业化);以及国家减少对各类媒
.体的公共投入,使国营媒体的财政收入中国家拨款或收视费的比重相对下降,而广告费
与其他商业性收入增加(狭义的商业化)。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培育下,西方国家传媒
“放松管制”的市场化制度和传媒政策由公众利益向商业利益的倾斜,导致商业性媒体
以绝对优势参与公营、私营媒体的竞争,传媒产业被纳入更加广泛的国际性广告与营销
市场,追逐*大利润成为媒体的唯一目标,广告成为传媒产业的核心支持机制,损毁了
传媒在保障西方民主制度、维护公众利益方面的作为。学者们都体察到商业化的直接
后果是传媒集团把新闻作为市场利润的手段,而不是一种具有自身价值的文化和政治
形式,新闻仅仅是吸引消费者的副产品,而且,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更
加加速催生了传媒产业的彻底商业化,诸如媒介产权的高度集中化(媒介公司的纵向整
合与横向整合),导致了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公共”服务完全转换成为由市场竞争者
提供的“以成本为基础”的服务;再如广告严重制约传媒的内容生产与受众的共识,以及
传媒技术的更新再造新的国际传媒分工利益的不公正(涵盖阶级、种族与社会性别范
畴)等等,所有这些都腐蚀了媒体从业者的操守(业界职员需顺应广告商和产权所有者
、的效益要求,否则被裁员或解雇),摧折了媒介产品的质量(因媒介商需要节约成本,减
:少经营预算与采编投入),削弱了民主社会的根基,压制和排斥了民众的意见表达。如
马克·米勒(Mark Miller,1997)在《美国出版业》论文中对美国出版业的垄断集中化现
状的分析:“除了诺顿出版公司(Norton)和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
后的两家主要的独立机构)、一些大学出版社与许多严阵以待的二流出版机构以外,如
今,美国的出版商都列入f八大媒介集团旗下。这八家公司中,似乎只有霍兹布林克
(Holtzbrinck)在经营方面还将读者的阅读内容纳入考虑范围(迄今为止)。至于其他的
大媒介集团,对读者的阅读内容关注甚少,就赫斯特报业集团、时代华纳、鲁伯特·默多
克的新闻集团、英国皮尔森集团、德国的贝塔斯曼、维亚康姆、前进出版而言,它们用于
图书生产与经营的费用,远少于电视、多媒体等流通环节上的费用。”李赫·宾德(Leah
F.Binder,1996)在《图书市场寡头垄断及其文化后果》论文中,强调在世界图书出版变
革中,我们真正的演讲和文化危如累卵,他对“图书市场寡头集团垄断及其社会、文化后
果”深表忧虑:“图书市场的全球化和商业化向民族文化的整合以及维护民族历史遗产
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图书馆、基础设施、学校受日益为市场价值所宰制的力量所威
胁。然而,联合大公司出版方面的垄断兼并、连锁书店的主导力量、畅销书和非畅销书
之间的隔离、名人效应的日益渐增,对图书的定位和设计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近期
研究首推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2004)的力作《媒体问题:21世纪
美国传播政治》一书,其一针见血地批驳了当前美国媒体系统及建立并维续此系统的决
策过程全然受制于企业财团的支配,毋庸质疑,美国新闻与娱乐媒体的表现自然受制于
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力量之控制,美国媒体之所以受企业财团之操纵且受到保护,主因是
政策制定的堕落。这对民主与健康文化的运行,业已构成严峻的挑战,作者身体力行,
提倡壮大公共媒体和推进改革媒体的运动来挽救商业化倾向带来的种种危机。
传播产业的彻底商业化并不是以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为出发点,而当商业的价值
和权力体系侵蚀并腐化了公共空间,那么它便会让有效的等级控制体系在公共空间中
运作。并且,“资产阶级思潮把新的经济理性奉为一种绝对价值,试图使新的社会组织
形式合法化。在此过程中,它认为新的组织形式是永恒的建构,而且某种程度上,就像
某些评论家*近非常天真地写到的那样标志着历史的终结”(Samir Amin,1997)。直面
这样的社会情境,如果知识分子还信仰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推崇的西方文明中知识社会学的*根本动力——“建立在对于美,对于知
识分子的独特性及责任的尊重的基础上的高尚的不满”。那么,知识分子就不应该仅仅
以专业人士自居,在日常教学与科研之外,去尽情享受消费主义带来的舒适与快乐,尤
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所称的“天堂里的布波族”(bobos in paradise)的幸福
感,不经意地放弃了作为社会的精神生产者与知识传播者的激情与警惕,重蹈朱利安·
班达(1uhen Banda)所预言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的覆辙(Banda,1969);而是以自己的勇
气和雄辩,担当责任,揭穿大众传播媒介的迷思,促进公共利益的完善,履行葛兰西所示
范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无疑都选择了后者实践自己的天
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学术研究与社会运动参与两个领域,始终活跃着洋溢政治热
情与学术坚韧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除了透彻批判传播产业商业化的诸多后果,
如赵月枝(2007a)已论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论文的论题包括: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
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全球政治经济由各国公司、政府机构和影响全球和本土
权力关系的阶级组合的构建;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
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传播中的社
会运动、日益私有化的视听空间中的公共领域状态、一个把人们主要当作消费者的世界
中的公民身份状态等等,从方法论层面,学者们也正在从聚焦阶级主体到关注多元社会
变革主体,反思阶级权力关系与其他权力关系(社会性别、种族、民族国家等)的主次轻
重问题,克服西方中心与男权中心的倾向;在分析中既聚焦结构又关注主体性,在方法
论上寻求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使宏观全球政治经济与微观的个人主体性塑造相连接。
这一问题现在更为迫切,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不仅是通过“全球扩张”(planetary
expansion)而更多的是通过“细胞渗透”(molecular infiltration)来运作(政经研究与文
化研究结合,政治经济学家采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回到具体的社会场景中洞察社会变
化)。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以政治经济学就版权问题的分析为例,提纲携领地论述这一分
析的内核和所引发的相关本土化思考。贝蒂格(Roland Bettig,1996)所著《版权文化:知
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哈克特和卡罗尔(Hackett&Carroll,2006)的《再造媒介:民
主化公众传播的抗争》的论著中,都指出在出版产业领域,版权作为限制知识生产与传
播的手段,可以说这就是版权产业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圈地和对信息与知识的私有化。
版权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知识的商品化过程密切相关。虽然市场逻辑下的
版权话语让人认为,版权保护个体文化生产者,鼓励创造,人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下一直在创造和发明,而当代世界,版权主要保护的不是人类的精神创造本性,而是版
权产业的利润。通过世贸组织,以美国为主导的文化产业商业化程度高的西方国家把
它们的版权制度国际化,使原来相对宽松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版权管理制度进
一步屈从于跨国公司的商业利益。而且,强大的西方媒体宣传使版权问题几乎成了发
展中国家的一些个人和经济实体对跨国公司产品的盗版行为的同义语,从而掩盖了跨
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传统社会从原来处于公共领域的传统知识到生物基因的“盗版”
和掠夺性占有。这种资本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新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原
始“圈地运动”的继续。更重要的是,以跨国公司利益为核心的版权体制,与以促进文化
教育和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合理使用”原则的张力日益加深,使低收入国家和群体接近
信息和知识的代价增高。数字时代一方面提供了无限复制的技术可能性,一方面也为
版权拥有者提供了以单一节目、单张网页、单条短信收费的现实性,从而使信息传播的
商品化进程进一步深化和精细化(赵月枝,2007b:58—59)。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一针
见血地指出,著作权法是媒体所有权政策的核心议题,他认为在理论上,对著作权的保
护已经纳入宪法,以确保作者对其作品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控制权;在著作权的保护
下,作者有创作激情去生产新的作品,但如果作者的版权收入达到一定量度,其作品就
应属于公共范畴,为大众免费享用。因此,著作权是一种独占权,由政府创造与强制执
行,直接限制某种竞争性市场的形成。这导致了文化遗产的私有化(McChesney,2004)。
因此,从版权的商品本质来看资本的逻辑,不难发现版权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
部,信息与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关系,版权建构并维护着市场的优势。
由此延伸出来的对本土产业的反思充满了忧患——市场的全面开放将会危及中国
本土资源的严重损耗,我们的森林、印刷业为西方出版公司供应了便宜的物质资源与廉
价的劳动力,西方在中国找到*大数量的阅听人,倾销其精神产品;同时,出版与中国学
术的成长相辅相成,一旦放弃中国原创学术的培育,盲目引进外版书,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的自主性将面临被歼灭的境地,文明的断裂也就不言而喻了。在探讨市场逻辑主导
下的文化产业与文化多样性的复杂关系和张力时,需要厘清文化市场上“消费者主权”
与“公民文化权利”之间的关系,赵月枝已经从国外人文知识界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
制下的文化产业的*新批判分析,敏锐探索了新世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需要什么
样的公共传播政策的重要议题(赵月枝,2006:1--7;2007b:56--62)。我们不禁会问:
市场逻辑是否可以全面解放中国出版产业的生产力?西方高度垄断的产业集团化模式
是否完全适合中国本土的需要?把媒介产业的权力交给市场,中国出版产业就能充分
得到发展吗?那么,我们能否排除二元思维,在综合各种制度优势的前提下,寻找适合
中国出版产业转型的另一种模式呢(曹晋,2007:55—57)?
资本主义的扩张造就了市场的开放,资本开放边界,但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却仍然
受到全球化时代科技愿景中的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地方与国家的边界的制约,传播产
业把人的主体性塑造为消费潜力。在西方传媒已经产生严重后果的商业化教训值得中
国重视,国家不应把建立有效率的商业媒体市场当作社会主义媒体改革的*佳结果,传
媒政策必须限制媒体的垄断性经营与垄断性利润,对传媒市场体系进行必要的公共干
预,从而纠正完全依赖市场所造成的失衡。各级政府应该增加公共资源的投入,实行媒
体的多样化经营,如保留公营的电视台,相关出版政策定期给予高水准的本土学术图书
出版资助,严格编校质量审查等等,从而造就全面辐射并服务各阶层民众的多元化传媒
景观,避免传媒产业成为少数人或者西方跨国传媒公司牟取暴利的权力工具,防范传媒
市场化逻辑再度损害党的传媒事业的公信力,并扩大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从而导致社
会对立力量积聚的报复行为破坏和谐社会的建构。
从高校的传播学学科建制来看,“如果学者要超越描述层次到解释层次,政治经济
学一定处在事业的中心地位。它并不仅仅是传播学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整个传播
学的基石”(McChesney,2000:115)。至今,中国大陆的传播领域,涉足批判的传播政治
经济学的学者甚为罕见,但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来临,国家对传播产业的改革逐步深化,
各类媒介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必然任重而道远,其所担
当的诠释、分析及转变之角色,也自然会得到中国大陆的学者与传播业内人士的重视与
首肯。
参考文献
[匈]卢卡奇(中文版1995),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
证法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法]阿芒·马特拉(中文版2001),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
[法]路易·阿尔都塞(中文版2007),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
[美]赫伯特·席勒(中文版1994),王怡红译,《思想管理者》,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美]赫伯特·席勒(中文版2006),刘晓红译,《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
[加]文森特·莫斯可(中文版2004),胡正荣等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
下》,北京:华夏出版社。
[德]卡尔·马克思(中文版1974),《剩余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1页。
[德]卡尔·马克思(中文版1979),《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89页。
[德]卡尔·马克思(中文版1979),《(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页。
[德]卡尔·马克思(中文版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第52页。
欧力同、张伟(1990),《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
曾枝盛(1990),《阿尔都塞》,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曹晋(2007),北京:《中围出版》,2007,7,第55页。
曹晋、周宪(2006),新世纪传播研究译丛总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赵月枝(2007a)《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前沿与路径》,范敬宜,李彬(编),《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15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第235--258页。
赵月枝(2007b),《文化产业、市场逻辑和文化多样性》(上、下),《新闻大学》,2006
冬季号总第90期与2007春季号总第91期。
赵月枝(2008),《信息时代的资本论》,丹-席勒《信息与资本》(How fo Think about
Informatton)中译本序言,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赵月枝、邢国欣(2007),《传播政治经济学》,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11--538页。
冯建三(2003b),《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新闻学研究》,2003,04,总75
期,第103—140页。
冯建三(1992),《资讯、钱、权:媒体文化的政经研究》,台北:时报出版公司。
冯建三(2003a),《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对话》,《传播与管理研究》,2003,
01,第2卷,第2期。
Amin Samir(1997), Capitalism in the Globalization: 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Zed Books.
Banda, Julien(1969), The Treson of the Interllectuals, New York: Norton.
Bettig, Ronald V. (2002),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Jeffrey T. Nealon and Caren Irt, eds. Rethinking the Frankfurt School:
Alternative Legacies of Cultural Critiqu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p.
81-94.
Bettig, Ronald V. (2003)," Copyright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Media
Development, 2003, No. 1, pp. 3-9.
Ronald. V. Bettig (1996), Copyrighti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Binder, Leah F. (1996)," Speaking Volumes: The Book Publishing Oligopoly and its
Cultural Consequences," George Gerbner, Hamid Mowlana, Herbert I. Schiller (eds.), Invisible
Crises: What Conglomerate Control of Media Means for America and the Worl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p. 35-44.
Curran ,James and Jean Seaton ( 2003 ),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London: Routledge.
Gandy Jr. Oscar H.(1992) , "The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A Critical Challeng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 Summer1992, pp. 23-42.
Garnham, Nicholas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ln{brmation, edited by Fred Inglis, London:Sage.
Hactett,Bob and Carroll, Bill(2OO6),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Jansen, S. Curry (200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Power, Media, Gender, and
Technolog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o
Kellner, Douglas(1995b), "Media Communications vs. Cultural Studies: Overcoming the
Divide," Communication Theory, Five, Two (May):162-177.
Mansell, Robin(2004 ),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New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 Vol. 6(1), 2004, pp. 96-105.
McChesney, Robert W. (2004),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U.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N. Y.: Monthly Review Press.
McChesney, Robert W.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 22, No. 1,2000, pp. 109-116.
Miller, Mark Crispin (1997),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Erik Barnouw, et al.
Conglomerates and the Medi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p. 107-133.
Mosco, Vicent( 1996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Sage.
Mosco, Vincent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 A Ten-Year
Upda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urdock, G. (1978),"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09-119.
Schiller, Dan (2007),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mythe, D.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 (3), 1-27.
Smythe, D. W.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20-127.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mass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
have become more concentrated in ownership, more centralized in
operations, more national in reach, more pervasive in presence,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media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theme of the
relative powerlessness of the broadcasters. Just as the national television
networks- the first in history -- were going to work, American
sociology was turning away from the study of propaganda. In this essay I
argue that such a strange conjunction of events is not without its logic. I
argue that' because of intellectual,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mmitments sociologists have not put the critical questions; that behind
the idea of the relative unimportance of mass media lies a skewed, faulty
concept of "importance," similar to the faulty concept of "power" also
maintained by political sociologists, specifically those of the pluralist
persuas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nd that, like pluralism, the dominant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 has been unable to grasp certain
fundamental features of its subject. More than that: it has obscured them,
scanted them, at times defined them out of existence, and therefore it has
had the effect of justifying the existing system of mass media ownership,
control, and purpose.
The dominant paradigm in media sociology, what Daniel Bell has
called the "received knowledge" of "personal influence," ~ has drained
attention from the power of the media to define normal and abnormal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ty, to say what is politically real and legitimate
and what is not; to justify the two-party political structure; to establish
certain political agendas for social attention and to contain, channel, and
exclude others; and to shape the images of opposition movements. By its
methodology, media sociology has highlighted the recalcitrance of
audiences, their resistance to media-generated messages, and not their
dependency, their acquiescence, their gullibility. It has looked to "effects"
of broadcast programming in a specifically behaviorist fashion, defining
"effects" so narrowly, microscopically, and directly as to make it very
likely that survey studies could show only slight effects at most. It has
~ ,, ~. ,,
enshrined short-run " effects" as measures of importance largely because
these "effects" are measurable in a strict, replicable behavioral sense, thereby deflecting
attention from larger social meanings of mass media production. It has tended to seek "hard
data," often enough with results so mixed as to satisfy anyone and no one, when it might have
more fruitfully sought hard questions. By studying only the "effects" that could be
"measured" experimentally or in surveys, it has put the methodological cart ahead of the
theoretical horse. Or rather: it has procured a horse that could pull its particular cart. Is it any
wonder, then, that thirty years of methodical research on "effects" of mass media have
produced little theory and few coherent findings? The main result, in marvelous paradox,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oing paradigm itself.2
In the process of amassing its impressive bulk of empirical findings, the field of mass
media research has also perforce been certifying as normal precisely what it might have been
investigating as problematic, namely the vast reach and scope of the instruments of mass
broadcasting, especially television. By emphasizing precise effects on "attitudes" and
microscopically defined "behavior," the field has conspicuously failed to attend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act that mass broadcasting exists in the first place, in a corporate housing
and under a certain degree of State regulation. For during most of civilized history there has
been no such thing. Who wanted broadcasting, and toward what ends? Which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have been generated because of mass broadcasting, and which going institutions
-- politics, family, schooling, sports -- have been altered in structure, goals, social meaning,
and how have they reached back into broadcasting to shape its products? How has the
prevalence of broadcasting changed the conduct of politics, the texture of political life, hopes,
expectations? How does it bear on social structure? Which popular epistemologies have made
their way across the broadcasting societies? How does the routine reach of certain hierarchies
into millions of living rooms on any given day affect the common language and concepts and
symbols? By skirting these questions, by taking for granted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order, the
field has also been able to skirt the substantive questions of valuation: Does the television
apparatus as it exists fulfill or frustrate human needs and the social interest? But of course by
failing to ask such questions, it has made itself useful to the networks, to the market research
firms, to the political candidates.
I. The Dominant Paradigm and Its Defects
The dominant paradigm in the field since World War II has been, clearly, the cluster of
ideas, methods, and findings associated with Paul F. Lazarsfeld and his school: the search for
specific, measurable, short-term, individual,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effects" of media
content, and the conclusion that media are not very important in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Within this whole configuration, the most influential single theory has been, most
likely, "the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s": the idea that media messages reach people not
so much directly as through the selective, partisan, complicating interpolation of "opinion
leaders." In the subtitle of Personal Influence, their famous and influential study of the
diffusion of opinion in Decatur, Illinois in the mid-Forties, Elihu Katz and Lazarsfeld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3 One
technical commentator comments with due and transparent qualification: "It may be that few
formulation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have had more impact than the two-step flow model." 4
Daniel Bell, with his characteristic sweep, calls Personal Influence "the standard work." s
As in all sociology, the questions asked and the field of attention define the paradi~n
even before the results are recorded. In the tradition staked out by L~zarsfeld and his
associates, researchers pay most attention to those "variables" that intervene between message-
producers and message-receivers, especially to the "variabl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They
conceptualize the audience as a tissue of interrelated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as isolated point-
targets in a mass society. They see mass media as only one of several "variables" that influence
"attitudes" or voting choices, and they are interested in the measurable "effects" of media
especially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 variables" like "personal contact." They measure
"effects" as changes over time in respondents' attitudes or discrete behaviors, as these are
reported in surveys. In a sequence of studies beginning with The People's Choice, ~' Lazarsfeld
and his associates developed a methodology (emphasizing panel studies and sociometry)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concern for mediating "variables" like social status, age, and
gregariousness. But in what sense does their total apparatus constitute a "paradigm," and in
what sense has it been "dominant"?
I want to use the word loosely only, without history-of-science baggage, to indicate a
tendency of thought that (a) identifies as important certain areas of investigation in a field, (b)
exploits a certain methodology, more or less distinctive, and (c) produces a set of results which
are distinctive and, more important, come to be recognized as such. In this sense, a paradigm is
established as such not only by its producers but by its consumers, the profession that accords
it standing as a primary outlook.
Within the paradigm, Katz's and Lazarsfeld's specific theory of "the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the idea that 6, opinion leaders" mediate decisively between mass
communicators and audiences, has' occupied the center of scholarly attention. In any discussion
of mass media effects, citations of Personal Influence remain virtually obligatory. As the first
extended exploration of the idea -- "the two-step flow" appears only as an afterthought, and
without much elabo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earlier The People's Choice -- Personal Influence
can be read as the founding document of an entire field of inquiry. If the theory has recently
been contested with great force on empirical grounds,? the paradigm as a whole continues to be
the central idea-configuration that cannot be' overlooked by critic~. Joseph T. Klapper's The
Ef~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1960) is the definitive compilation of the field's early stages;
but the Decatur study, spread out as it is in detail, seems to me a better testing-ground for a
reexamination of the whole paradigm. By having the power to call forth citations and critiques
at its own level of generality, it remains central to 'the field. For twenty years replicating
studies have proliferated, complicating and multiplying the categories of the Decatur study,
looking at different types of behavior, different types of "news function" (" relay,"
,6 information," and so on), some of them confirming the two-step flow on a small scale,~ but
most of them disconfirming or severely qualifying it.'~ All these studies proceed from the
introduction into an isolated social system of a single artifact -- a product, an "attitude," an
image. The "effect" is always that of a controlled experiment (such, at least, is the aspiration),
but the tendency is to extrapolate, without warrant, from the study of a single artifact's
"effect" to the vastly more general and significant 6, effect" of broadcasting under corporate
and State auspices. Whatever the particular findings, the general issues of structural impact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re lost in the aura, the reputation of the "two-step flow."
作者简介
p>主编简介
曹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国际
出版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新闻传
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副研究员.美国耶鲁
大学高级访问学者.致力于批判传播理论与
书刊出版研究。
赵月枝.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
-

曾国藩的经济课
¥33.2¥68.0 -

经济学通俗读物:北大经济课(受益一生的经济学智慧)
¥9.7¥35.0 -

全球贸易摩擦与大国兴衰
¥19.4¥68.0 -

经济学反思
¥17.8¥56.0 -

国富论
¥9.7¥35.0 -

国富论
¥16.7¥58.0 -

世界贸易战简史
¥17.9¥52.8 -

中国经济思想变迁与制度发展概论
¥16.0¥50.0 -

文化经济学
¥22.6¥60.0 -

经济学通识-第二版
¥38.7¥58.0 -

让财富找到你:有温度的经济学
¥19.4¥68.0 -

高韧性社会:应对不确定危机的八种能力
¥23.1¥69.0 -

账本里的中国
¥15.4¥48.0 -

中美贸易摩擦:怎么看 怎么办
¥16.7¥58.0 -

郎咸平说萧条下的希望
¥12.7¥39.0 -

经济常识一本全
¥10.4¥35.0 -

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
¥9.3¥15.0 -

思考.快与慢
¥51.4¥69.0 -

理性的非理性:生活中的怪诞行为学/郑毓煌苏丹
¥19.6¥58.0 -

置身事内 : 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37.4¥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