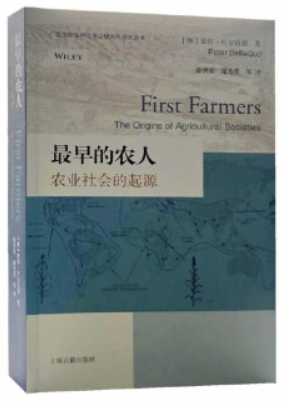
包邮最早的农人:农业社会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al societies

- ISBN:9787532597062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524页
- 出版时间:2020-09-01
- 条形码:9787532597062 ; 978-7-5325-9706-2
本书特色
本书原著者为彼得?贝尔伍德,英文版出版于2004年,曾荣获2006年美国考古学会全球*佳考古学著作、考古学和人类学*佳专业出版著作两项殊荣,目前已出版有日文和越南文等版本。农业起源是整个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步骤,有“农业革命”之称。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奠定了1万年来人类社会飞速发展、人群跨越性迁徙的基础。本书以全球视野,综合运用考古学、比较语言学、生物人类学的理论和材料,探讨了农业多重起源的原因。在本书中,贝尔伍德根据考古学、遗传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农业—语族扩张理论,这一理论在解释那些拥有早期农业,特别是中东、非洲下撒哈拉沙漠北部、中国、中美洲、安第斯山中部及亚马孙流域等核心地区的发展与人群迁徙、语言变迁有独到见解。尤为难得的是,本书关注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的农业起源问题,有助于国内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了世界上不同地区早期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所使用的资料和方法包括考古学、比较语言学、生物人类学,研究对象集中在世界上几个关键的早期农业中心,包括中东、中国、北非、新几内亚、中美洲和安第斯中部。贝尔伍德教授据此提出了农业—语族扩张理论(language- farming model),认为那些特别核心的早期农业地区,是农业社会起源的中心,人群的迁徙带动了农业、语言和人种的传播,造就了后世人类文化分布的版图。
前言
中 文 版 序
《*早的农人》英文版出版于2004年底,至今已经有15年了。虽然2004年版后来没有做过修订,但我很有信心,15年以来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推翻该书的主要观点,食物生产方式的转变仍然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变革之一。《*早的农人》出版以来反响甚佳,2006年获得了美国考古学会*佳著作奖(Book Award from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引用率一直颇高。但争议也不少,特别是针对农业人群迁徙理论,以及使用多学科方法解释农业传播的可行性等方面(Bellwood et al. 2007)。基于过去15年来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今天大多数史前学家都已经认识到,人群迁徙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都是普遍现象,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古代社会是静止和固化的,迁徙只是一种例外。这个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读者可以参看我2013年出版的著作《*早的移民》(First Migrants)。该书讨论了人类史前时期各个阶段的迁徙状况,其中第六章至第九章是关于农业扩散的内容,与《*早的农人》相近,所列参考文献截止到2012年。我主编的《史前世界人类迁徙史》(The Global Pre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Bellwood 2015),参考文献也更新到2012年,收集了世界多个地区的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资料。我的著作《*早的岛民》(First Islanders, Bellwood 2017)也使用了中国华南和东南亚的新材料,特别是关于南岛语族人群从中国华南扩散到岛屿东南亚和太平洋方面的内容。自《*早的农人》出版以来,我们对于早期农人问题的认识有了几项重要突破,尤其是关于野生动植物驯化的年代。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促使动植物从野生型转变为驯化型的人类选择过程经历了数千年,*终才开花结果(Bellwood 2009)。农业起源的一些关键地区,例如西亚(Willcox 2012)、东亚(Stevens and Fuller 2017; Ma et al. 2018)、中美洲(Piperno 2011a, 2011b)和南美洲(Kistler et al. 2018),其考古证据都表明了这一点。《*早的农人》一书曾经提到作物驯化在开始阶段进展相对缓慢的现象,但是未做深究。在东亚,可识别的驯化稻*早出现在距今9400年前的浙江北部(Zuo et al. 2017),这个年代接近了距今11000年前西亚纳图夫文化晚期和前陶新石器时代A段开始初步(驯化前)栽培行为的时间。在长江以北的华北地区,粟和黍*早栽培的时间也与之相当。但完全驯化的水稻(特征为颗粒饱满、抱穗不脱、同步成熟,《*早的农人》第二章对之有所解释),直到大约距今6000到5000年时才在新石器时代作物群中占据主导地位(Stevens and Fuller 2017),这意味着从野生到驯化的转变需要大约30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尽管如此,长江下游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上山文化到中晚期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其间三四千年里的人口仍有显著增长。当前中国学者针对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遗址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很多资料。从遗址的面积和数量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人口普遍增加(Cohen 2011;Wagner et al. 2013;Yu et al. 2016)。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农业核心区,从距今9000至5000年,人口数量增长了10倍以上。世界各地的民族学和历史学资料都充分证明,人类正是通过垦殖周边环境使得自身快速繁衍,人口得以增长,《*早的农人》第二章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例如,早在5000年前,浙北良渚这一重要遗址就已经接近城市状态,人口多达3万,建立了灌溉稻作农业经济体系(Bin et al. 2017)。如果要为新石器时代华南向东南亚的移民假说寻找人口增长的时代背景,那实在不难找到。根据2015年以来的古DNA全基因组研究结果,甚至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这种现象(Lipson et al. 2018; McColl et al. 2018; Bellwood 2018),但是中国国内目前还没有发表过关于人类迁徙的古DNA研究成果。人类为什么要发展粮食生产?这仍然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比2004年并没有多少进展。是否存在一个全局性的环境背景动因对所有地区都发挥了作用?不少人认为冰期后气候的改善(趋向温暖湿润)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随着狩猎采集人群数量和密度的提高,催生了家族“私有(Private)”财产观念的产生,并使得聚落规模扩大,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Gallagher et al. 2015;Bowles and Choi 2018; Kavanagh et al. 2018)。是不是在狩猎采集人口密度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而非强制共享的观念推动了种植作物的需求?今天,这成为一个流行的假设,比2004年时更甚。2004年时多数学者更赞成生存压力和风险管理是农业发生的原因。常说的一个例子就是新仙女木事件,导致了在距今11000年时全球变冷,这是一个短暂但非常剧烈的气候逆转时期,在冰期后的普遍改善中触发了*早的耕作活动(Moore and Hillman 1992)。这些根本的和潜在的全球性“动因”,如果它们确实存在的话,应该激发粮食生产在世界各地同时发展起来,特别是许多众所周知的农业起源地,如西亚、东亚和中美洲。尽管这些转变本身是在不同的地方独立发生,但是,这些地区向农业的转变是否足够共时,可否表现出是一个单一原因在发挥作用?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我们完全看不出全世界在同一个时期一致转向粮食生产。在公元前10000年时,从开普敦到乌斯怀亚和霍巴特,整个世界并没有突然都变*新石器时代,虽然这些地方的环境条件当时都具有发展农业的可能性。世界各地农业发展的轨迹在年代和速度上千差万别。如果我们把农业与欧亚大陆新石器时代画等号,那么毫无疑问,这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如定居村落、磨制石器、陶器技术、驯化动植物,在各地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英国的新石器时代比叙利亚晚了5000年,比长江流域晚了3000年,质疑测年数据存在偏差似乎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所以,结论是很明确的: 世界各地的史前农业,其起源地区、传播年代和传播速度都各不相同。当然,栽培行为在植物形态呈现驯化很久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人们可以通过强调这一事实来掩盖农业起源的问题。这个观点将某些地区包括美洲的农业起源上推很早,甚至到了更新世全新世之交(Piperno 2011 a; Kistler et al. 2018)。但是,很难找到这个时期农业广泛起源的确凿证据,而且,当人们意识到世界上(如华北和日本)新发现的许多陶器的年代都早于新石器时代,并且属于狩猎采集社会,这个说法就更难以成立。我们不能再简单地用有无陶器代表食物生产的存在与否。例如中美洲和西亚地区农业的*初发展就是在没有陶器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否存在食物生产,只能通过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的证据材料来确定。正如我在本书中的论述,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即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年代早晚差异很大。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人类开始从食物采集转向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农业只在世界上几个特定地区发生,然后传播到其他地区。传播通常会覆盖一整块大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终点。速度缓慢是因为每次传播都需要大量的人口迁移,相应地这要求农业人群自身不断繁衍,传播并非完全是土著狩猎采集者接受农业的结果。现在我们从人类体质和语系方面的研究来考察这一问题。自2015年以来,*重大的进展来自对古人类耳内岩骨提取DNA的研究(Reich 2018)。由于这一进展,2004版《*早的农人》关于遗传学内容的第十一章是所有章节中*过时的一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当今世界76亿人口中的大多数,他们的血统、文化和语言都是由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早期农耕和畜牧人群扩散而来,可能只有一直居住在极不适宜耕作之地(如沙漠、高山、高寒地区)的人类例外。这个结论在2004年肯定没有现在这么清楚。自2002年以来(Bellwood and Renfrew 2002),这个观点被称为“农业/语言扩散假说”,或“早期农人扩散假说”,本书使用后一个术语。然而,从古DNA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农业兴起之前,史前人类也曾多次进行跨越世界的迁徙。即便今天,世界上所有人的基因并非都来自同一个祖先。早期农业人群确实传播了其语系的底层语言[在语言学上称之为“原语言(protolanguages)”],例如原始印欧语、原始南岛语和原始汉藏语,但后来同语系的农人和游牧者在前期语言层之上又覆盖上了新的语言层。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扩张范围遍及今天整个中国,特别是从战国(周朝末年)到秦汉时期,大约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300年之间,汉语的传播极其迅速(Bo Wen et al. 2004; La Polla 2015)。另外一个例子是颜那亚人(Yamnaya),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大草原扩张到中欧和北欧部分地区(Reich 2018)。这并不是整个印欧语系的源头,但颜那亚人可能将古波罗的海语和斯拉夫语传播到了以前由印欧语系其他人群占据的欧洲某些地区(Bouckaert et al. 2012; Heggarty 2019)。回首2004年,在我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我是如此描述“早期农业扩散假说”背后的动因的。世界*后一次走出冰河时代,热带和温带地区的很多居民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向食物生产,驯化动物和植物。随着食物生产水平的提高,某些(但不是全部)区域的农业人口迅速增加,尤其西亚、东亚、热带西非和中美洲*为突出。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需要开拓更多土地以种植作物和放牧家畜,于是造成了向新区域的移民。随着人群迁徙,他们的语言、基因和生活方式也随之传播开来。语言和语系在这里尤为重要。30多年前,很多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始意识到,世界上许多特大语系的起源与对食物生产的日渐依赖有关。各大语系在殖民时代(从1492年美洲伊利比亚移民点建立算起)之前的分布,与人群种族和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高度重合。这些农业、基因和相关语言的传播深深植根于史前时代,远早于希腊、罗马、汉朝等文明的兴起和帝国的征服。在世界许多地区,这个时期大多相当于农业起源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我和其他同行*初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了“早期农业扩散假说”,并在《*早的农人》一书中做了详细阐述。今天,在考古学、语言学和进化生物学或遗传学带动科学研究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人们开展相关研究,对于我们的观点,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早期农人扩散假说”在30年后的今天还有说服力吗?新的发现对于农人和狩猎采集者之间长期的复杂关系有没有新的阐释?本书的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但是,不管答案是什么,没人能否认,如果没有食物生产,今天的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也不会存在。
2020年2月彼得·贝尔伍德
英 文 版 序
重建全球性的人类史前史实非易事。本书主要关注古代农业的起源和人群的扩散。即便如此,恐怕当世学者也很难有谁能全部通晓本书涉及的所有学科,我自己也只是对考古学有所专攻。考古学确是重建人类历史的核心学科,但同时还必须参考其他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书任务艰巨。关于人类史前时期在全球范围内温带和热带地区的农业传播,其假说的主要基础是多学科研究结果的相互印证。虽然它们本身并非直接证据,但却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有力的理论的一部分呈现给读者,具体内容我会在导论章节中详细阐述。下面,作为背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如何对人类文化、语言和生物多样性这种宏观研究变得如此痴迷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还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学生,主要研究罗马帝国西北诸省考古,以及后罗马时代(日耳曼人迁徙)考古。当时,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领导下的剑桥大学人类学系*热门的方向是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所以我可能是选了一匹黑马(黑马之黑,倒不是因为我研究的是日耳曼黑暗时代)。之所以选择研究欧洲西北部晚期考古,是因为我希望研究现代欧洲人的直系祖先。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既可以参考历史文献,又有丰富的考古资料。在剑桥学习的*后一年,我开始意识到,虽然罗马和盎格鲁撒克逊考古研究极有价值,但这个领域并不能带来对世界范围内古代人类历史的革命性认识。我已故的老师,琼·利弗斯奇(Joan Liversidge)和布赖恩·霍普泰勒(Brian HopeTaylor),可能会赞同我的看法。由此我的兴趣开始转移。1964年,我和诺曼·哈蒙德一起参加了一个大学生考察活动,去调查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一条罗马大道,随后在1966年,又和塞顿·劳埃德和克莱尔·戈夫去了土耳其和伊朗进行考古调查。总之,我打算在更为偏远和有趣的地方寻求一下刺激。机会很快来了。1967年,我被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聘为讲师。我用了6年的宝贵时间来研究波利尼西亚,特别是跟随篠远喜彦(Yosihiko Sinoto)在马克萨斯群岛和社会群岛工作,后来在新西兰和库克群岛又开展了我自己的研究项目。在此期间,我发现了历史语言学的价值,还发现所谓波利尼西亚人实际上是有共同起源而且起源很晚的一群人。我开始想了解,分布范围如此广大的一群人到底来自何处?定居各个岛屿之后又是如何分化的?当然,即使在1967年,我也不是唯一一个对波利尼西亚人起源研究感兴趣的人。沿着18世纪70年代库克船长和福斯特开创的探索传统,在奥克兰大学,我和两位优秀的同事罗杰·格林和安德鲁·波利共同开展研究工作,他们两个也强烈赞同使用考古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史前史(Pawley and Green 1975)。1973年,我转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20世纪70年代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群岛和澳大利亚移民研究热的高潮时期。在约翰·穆瓦尼的鼓励下,我开始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并以一手材料证实了我在新西兰时候萌发的学术观点。分布广泛的波利尼西亚人,实际上只是整个南岛语族扩散现象中的一个片段。同时,通过本科教学、季节性田野工作和学术休假旅行,我对世界上多个主要区域的考古研究有了切实的认识,特别是对亚洲和欧洲新石器考古,以及美洲形成期考古。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开始认真思考农业人群扩散在人类史前时代的意义。当时大多数考古学家对柴尔德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嗤之以鼻,认为早期农业在绝大多数地区只是一种缓慢而艰难的发展过程。考古界根深蒂固地认为: 世界上所有族群起源以后基本上没有动过地方,全部文化特征都是在原地独立发展出来的。西方的学术界,正处在对帝国主义的深刻反省中,故而将文化进化论平等地运用到全世界各个族群。但我关于罗马帝国、日耳曼野蛮人和波利尼西亚移民的知识,令我对以上说法表示怀疑。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我开始质疑真实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如此顺利,特别是出于以下两个重要方面。首先,近几个世纪,就族群而言,形态千变万化,变革剧烈,但考古学家津津乐道的史前社会,变化缓慢,不相往来,长期保持静止状态,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怎会如此悬殊?其次,世界各地几乎都有人居住,但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分布范围如此广大的人群,其语言却只属于极少数几种语系,这是怎么回事?对许多人来说,后一个问题可能看起来很奇怪,特别是它来自一个考古学家。但是,正如我后来试图证明的那样,一个广泛分布的语系必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起源地,其扩散历史必然涉及使用此母语的人群的迁徙,至少部分原因会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下,语系或人群扩散的广泛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在民族志或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世界史中见到的任何政体、帝国或贸易体系的活动。事实上,语言的历史揭露了大多数非语言学者完全不了解的一些重要史实。我开始意识到,人类过去的某些方面必定与考古学家构建的渐进式历史完全不同,后者的观点建立在对民族学调查中人类行为的观察,但在我看来,民族志这个资料库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我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把所有这些零碎的想法拼合为一个整体的,但显然是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这十年(Bellwood 1983, 1988, 1989)。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 1987)之后提出了关于印欧语系扩散的观点,还有人研究班图语在非洲的传播(Ehret and Posnansky 1982)。我振作精神,全力以赴,搜集了多个学科的大量资料。我也经常感到心灰意冷,因为我发现,基于其他学科构建起来的貌似很有说服力的假说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情形和基于考古学建立的那些假说别无二致。所有历史学导向的学科都面临着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以及利用这些资料进行推理的可信性问题。考古学家在利用语言学和遗传学重建历史方面能否发挥自己的作用?今天,对我来说答案已经很清楚,考古学家确实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考古资料,如同体质人类学家的人骨标本一样,是人类过去历史的直接证据。大多数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所依据的都是现代资料,除了特殊情况下得以保留下来的古代文本和古代人骨DNA之外(这两种材料都不常见)。能够直接反映过去的材料十分珍贵,对于现代大学中的“历史学”学科尤其如此。但是,单纯根据出土材料和古代文献,或者根据现代语言学或遗传学资料推导出的谱系树,重建古代历史都不太可能。这两方面的材料都很重要。两方面都需要对方的独立视角作为必不可少的补充,就像本书中涉及的考古学、比较语言学和生物人类学这三个学科的关系一样。在此向大家表达我的谢意。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和亚洲研究院制图组的珍妮·希恩,她绘制了大部分地图,这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另外一些地图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其他同事们绘制的,包括地理系的克莱夫·希尔克、考古学和自然史系的林恩·施密特和多米尼克·奥亚。没有这些地图,本书将黯然失色。多位同行阅读过部分手稿,这里按照章节顺序而不是字母顺序把他们的芳名排列如下: 尼克·彼得森、欧弗·巴尔约瑟夫、劳埃德·埃文斯、苏尼尔·古普塔、迪利普·查克拉巴蒂、瓦桑特·辛德、维伦德拉·米拉、大卫·菲利普森、诺曼·哈蒙德、科林·伦福儒、罗杰·布伦奇、简·希尔、安德鲁·波利、罗伯特·阿滕伯勒。对大家的真知灼见我深表感激,任何错误都由我个人承担。*后,我要感谢我所在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我就职的两个系(考古学和人类学系、考古学和自然史系),它们为我提供了便利的设施、充足的时间、丰富的图书资料和出色的助手进行这项研究。澳—美教育基金会(富布赖特基金会)和英国国家学术院分别资助了我在伯克利(1992年)和剑桥(2001年)的访问,这对拓宽我的视野非常有帮助。无数的学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多年来提问了数不清的问题,他们问起问题来恰如那些不赞成我观点的同行,对我有很大启发。*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克劳迪娅、塔内、汉娜和查理,能够支持我对人类过去的探索,希望他们都喜欢这本书。
目录
英文版序1
**章早期农业扩散假说1
概述1
相关学科3
主要观点5
指导原则10
第二章关于农业起源与扩散的思考14
农业的意义: 生产力和人口数量16
为什么农业会在某些地区率先发展?23
农业相对于狩猎采集的重要性32
在什么情况下史前狩猎采集者采纳了农业?36
**类: 非洲和亚洲的“小生境”狩猎采集者38
第二类: 澳大利亚、安达曼群岛和美洲地区的
“开放型”狩猎采集者44
第三类: 农人退化为狩猎采集者48
一项比较研究: 为什么民族志中的狩猎采集者没有采纳
农业?51
关于考古资料55第三章西南亚农业起源57
新月沃地的植物驯化59
公元前19000年到前9500年黎凡特地区的狩猎采集者63
前陶新石器时代和驯化作物崛起69
谷物驯化是如何在西南亚开始的?74
西南亚农业考古资料的宏观考察76
前陶新石器时代A段77
前陶新石器时代B段79
新石器革命的真正转折点85
第四章走出新月沃地: 农业在欧洲和亚洲的传播89
新石器经济在欧洲的传播90
欧洲南部及地中海地区93
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93
巴尔干半岛98
地中海地区99
欧洲温带地区与北欧100
多瑙河流域和北欧中石器时代102
漏斗杯文化与波罗的海地区104
不列颠群岛106
欧洲史前时期的狩猎者与农人107
农业从西南亚向东亚的传播109
中亚109
印度次大陆112
印度次大陆的驯化作物114
从狩猎采集到农耕: 南亚地区的农业发展之路115
梅赫尔格尔文化的成果115
印度西部: 从巴拉塔尔到乔威118
印度南部120
恒河流域和印度东北地区122
欧洲与南亚的比较125
第五章非洲: 又一个农业起源中心?127
西南亚农业文化传入埃及129
非洲本土驯化的起源135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业的发展与传播139
非洲中部和南部农业的出现140
第六章东亚农业起源146
环境因素与中国的作物驯化过程153
中国早期农业考古156
黄河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资料158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的发展160
长江以南——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163
浙江南部的农业传播164
第七章农业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传播168
东南亚农业传播的背景170
大陆东南亚的早期农人171
台湾岛和岛屿东南亚的早期农人176
太平洋地区的早期农人184
新几内亚的农业发展轨迹及其在太平洋殖民中的作用186
第八章美洲早期农业192
背景概况195
早期农业地理环境及文化轨迹197
关于美洲农业起源的主要观点201
驯化作物203
玉米204
其他作物207
美洲的早期陶器209
美洲的早期农人210
安第斯山区210
亚马逊地区217
中美洲218
美国西南部223
高速公路和管道建设带来的考古发现228
美国西南部农人来自中美洲?230
美国东部林地农业的独立起源232
第九章如何通过语言研究人类史前史?239
语系及其研究方法240
语系发生及其网络244
语系的识别与种系关系246
相关语系252
语言和语系是怎样传播的?254
语言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258
超大语系,以及关于时间因素的进一步讨论261
语言的竞争: 语言转换262
语言竞争: 接触引起转变265
第十章农业传播: 考古学与语言学的比较研究268
欧亚大陆西部和中部,以及北非269
印欧语系269
印欧语系来自东欧大草原?271
原始印欧语的真正起源地在哪里?我们能够
了解多少?273
科林·伦福儒对印欧语系研究的贡献276
亚非语系278
埃兰语和达罗毗荼语,以及印度雅利安语282
多学科视野下的南亚史前史286
印欧语系,亚非语系,埃兰达罗毗荼语系,以及泛欧亚
大陆语系290
撒哈拉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尼罗撒哈拉语系和
尼日尔刚果语系293
尼罗撒哈拉语系293
尼日尔刚果语,班图语294
东亚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298
中国和大陆东南亚的语系298
南岛语系304
东亚概观306
“阿尔泰语系”谜团307
跨新几内亚语系309
美洲——南部和中部310
南美洲312
中美洲和美国西南部317
乌托阿兹特克语系320
北美东部327
阿尔冈琴语和马斯科吉语328
易洛魁语、苏语和卡多语332
*早的农人传播他们的语言吗?336
第十一章遗传学、体质人类学和人类生理特征338
人类生物学特征与语系之间是否相关?340
基因记录了历史?341
西南亚和欧洲343
南亚351
非洲353
东亚354
东南亚和太平洋: 以南岛人为例355
美洲363
早期农业是通过人口迁徙扩散的吗?364
第十二章早期农业扩张的性质366
起源地、迁徙区、摩擦区和回归区367
农业起源与扩散过程的各个阶段371
注释375
参考文献392
索引503
译后记523
相关资料
在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之后,人类开始改变其生活方式,从采集狩猎转向农业,结果就是人口迅速增加并向周围地区扩散。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终奠定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本书从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等相关证据入手,探讨农业社会的起源和扩散,论述缜密,精彩纷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长久不衰的盛誉。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早的农人》一书*大的贡献是从考古学、语言学、生物学多重角度深入研究了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史前史和农业起源。希望此书中文版的面世能有助于扭转和弥补我们在南岛语族起源和扩散研究领域的短板,进一步推动华南沿海的史前考古研究。期待!
——李水城(北京大学 教授)
彼得·贝尔伍德的《*早的农人》大胆地将全球范围内早期农业的传播与人口和语言扩散事件联系起来。它提供了一个关联性极强的视角,针对人类历史上*重大的问题之一进行了新颖简洁的解释,富有挑战性。
科林·伦福儒(剑桥大学 教授)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第二届世界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彼得·贝尔伍德《*早的农人》是当代史前史研究领域*伟大的著作之一。彼得对于农业起源与扩散的全球性叙述,是理解人类社会、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乃至当今不平等现象的基础。
——贾雷德·戴蒙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教授)
(普利策奖获奖者,著有《枪炮、病菌和钢铁》等畅销书)
作者简介
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
国际著名考古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曾任该校考古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长期担任印度—太平洋史前协会(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秘书长。主要学术专长是从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角度研究东南亚和太平洋史前史、全球农业起源及人类迁徙等。著有《人类征服太平洋》(1978)、《印度—马来群岛史前史》(1985)《*早的移民:古代世界人类迁徙》(2013)、《*早的岛民:岛屿东南亚史前史和人类迁徙》(2017)等重要著作
-

中国近代史
¥14.3¥39.8 -

汉朝其实很有趣
¥10.5¥38.0 -

你不知道的古人生活冷知识
¥15.7¥49.0 -

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
¥15.7¥49.0 -

万历十五年
¥15.3¥26.0 -

发明里的中国(平装)
¥8.8¥25.0 -

人类酷刑简史
¥21.1¥59.0 -

正说明朝十六帝
¥17.9¥49.8 -

资治通鉴
¥12.2¥35.0 -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36.8¥65.0 -

罗马考古-永恒之城重现-发现之旅.历史卷
¥11.5¥35.0 -

两张图读懂两宋
¥17.0¥76.0 -

历史十讲-走进王朝深处
¥11.8¥36.0 -

名家小史——中国历代党争史(图文版)
¥14.7¥29.8 -

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
¥10.6¥32.0 -

两晋其实很有趣
¥10.1¥35.0 -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15.7¥42.0 -

帝国的终结
¥21.4¥68.0 -

不忍细看南宋
¥15.7¥49.0 -

史趣(书里书外的历史)
¥14.4¥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