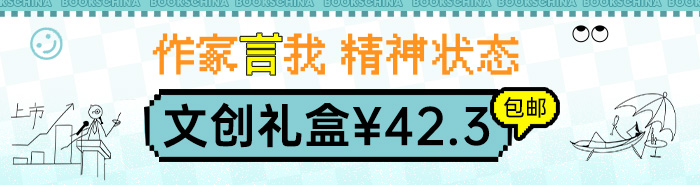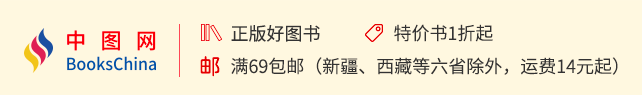- ISBN:9787806956137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228
- 出版时间:2007-12-01
- 条形码:9787806956137 ; 978-7-80695-613-7
内容简介
这是雅皮的黄昏。
有围墙的青春如何狂欢?自恋镜像中的遗址,那群高智商的年轻动物讨着美人欢心。聪慧、无聊、生猛、自负,他们历经梦想与人性、肉身的短兵相接。
阳光之下,万物都在疯狂生长,一如热带雨林的藤蔓,遮天蔽日,却掩藏着怎样的失落与惶恐。
目录
**章 洗车
第二章 人体
第三章 处男
第四章 哥伦布
第五章 女友
第六章 柳青
第七章 银楼
第八章 银街
第九章 肉芽肿的手指
第十章 我肮脏的右手
第十一章 初夜
第十二章 垂杨柳
第十三章 包书包
第十四章 口会
第十五章 一地人头
第十六章 大酒
第十七章 概率统计
第十八章 阴湖阳塔
第十九章 昔年种柳
第二十章 清华男生
第二十一章 永乐五年
第二十二章 非花
第二十三章 洗车
节选
**章 洗车
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
“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冼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儿,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喝点儿什么,聊聊天,后来便有了“洗车酒吧”。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要上座桥,过一条水渠,穿一片柏树林子,挺深的。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洗车房现在还接洗车的活。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砖墙上铆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给人仿佛是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确保车牌还在——至少我是。酒吧不大,稍稍上点儿人,就满了。天气不冻脸的时候,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闻到柏树的味道。
现在,三里屯、工体附近,酒吧很多,三五成群,占了几条街,一家没位子可以溜达到另一家。入夜,在东大桥斜街左右,杨柳依依,烟花飘摇,各色妇女倚街而站,多数不像本地人氏。或薄有姿色,或敢于暴露,也分不清是卖盗版VCD的还是卖鸡蛋的,或者索性就是“鸡”。我过去在这一带上的小学和中学,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只有卖汽车配件的。匪类聚集中纺路,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售。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么些东西,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我是有潜质的。我妈妈回忆说,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亲,从小就是个淫坯。我从小学读到博士,兼修了个工商管理硕士,一身经世济民的本事,现在争名逐利,津津有味。我老婆英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英文、古文的功底都不错。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我敛了些密戏图和瓷质的密戏玩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种姿势都有,旧货贩子讲这是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教具用的,姑娘出嫁之前,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免得什么都分不清,让亲家笑了去,说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但是想想只是想想,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同我的假账和黑钱放在一起,体现相似的性质。
我老婆五短身材,孔武有力,浓眉大眼,齐耳短发一丝不乱,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结婚已经五年了,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长穗的头发,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她云飞雪落地说,她*近读了本书,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性爱带回家,生意就是生意,公事公办。而我是个变数,公文包即使是空的,也要往家带,在办公室,连手淫的迹象都没有发现。我的秘书还问我,和老婆那么熟了,小便都不回避,属于近亲,行房的时候,有没有负罪感?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因为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是上级使用权力占便宜。这里我是上级,我的秘书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她对香水过敏。我以前并不知道,只是简单地认为,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没必要用香水。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她才来见我,让我知道。我说:“我初中时就知道你有宜男相,一定能当英雄母亲。”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她香气扑鼻。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她仔细嗅我的皮鞋、西装、衬衣、内裤和袜子。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像小时候蒸漏了糖的糖三角。她告诉我她香水过敏,她说我不如杀了她,她拨电话给她爸爸喊“救命”!她爸爸是公安局局长,常年扎巴掌宽的板带。之后她后悔地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停二十分钟,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个太监。
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我喜欢坐在“洗车”里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从角落里看得见酒吧里的各路人物。我觉得酒吧像个胃囊,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然后小便出去,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浸了啤酒,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泡酒吧的日子长了,它渐渐变得很有经验。吸毒的比较好认,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有些涂眼影、唇膏的想模拟的那种效果,但是不可能学得像。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吸毒者的颜色从肉里来,从血里来,从骨头里来。同性恋不好认,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常常会闹误会。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关键还是要看眼睛,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我静静坐在木椅子里,音乐和人声像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松柏、流水、香水、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黏稠而透明。我像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感觉不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我们在里面折腾,慢慢地消磨,*后归于共同的虚无——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会有几个脸熟的男人,都是苦命人。偶尔打打招呼,一起喝一杯,各付各的账。这样的聊天很少涉及彼此的具体情况,不谈公司的进存销。
我习惯坐在这个角落,我有很多习惯。公司的洗手间,我习惯用*靠东边的那个坑位,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坑位风水*好,拉出的大便带热气。但是连续几天我在“洗车”的角落都被一个少年占了,他又高又瘦,也用一个方口杯子喝燕京啤酒。如果我在公司的坑位总被别人占据,我会便秘的。我被他迷惑。他的眼睛很亮,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光,像四足着地的野兽。我老婆告诉我,我刚出道做生意时,眼睛里也放绿光,只是现在黯淡到几乎没有了。我在这个少年身上隐晦地察觉到我少年时的存在状态,或许这个少年的头脑里也有一个怪胎,这个发现让我心惊肉跳。
我走到他对面坐下,我告诉他我常常坐这儿,他说“是吧”。我问他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总吃鱼肝油胶囊,他说他是学医的,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从事使某种情况下死亡的人起死回生的研究,涉及多种空间、时间等等曾经困惑过我的概念。他姓秋,叫秋水,与庄周《华南经》的一章相同。
以前我也在“洗车”里和陌生人聊过天,听过不少人的故事。有些人像报纸,他们的故事全写在脸上;有些人像收音机,关着的时候是个死物,可是如果找对了开关,选对了台,他们会喋喋不休,直到你把他们关上,或是电池耗光。秋水不是收音机,他是一堆半导体元件。我费了很多时间设计好线路,把他们组装起来,安上开关。他的眼睛那么亮,我想音色应该不俗。
秋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生长的故事,让我那天晚上心情异常的烦躁,甚至至今都分不清故事的真假。他说他不清楚这个故事的主题,也无法理解所有重要细节的意义。我告诉秋水,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一种是明白了;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心中了无牵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我付了酒账,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向前走,很晚才回到家。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情人,问她孩子*近怎么样了。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的老情人告诉我,孩子正睡着,挺香。
第二章 人体
我是学医的,我认识柳青是在《人体解剖》课考试之前。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感觉烦闷,我没有理由还在这个地方待着,我想离开。
考试前的宿舍没法待,我决定离开。
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医学院里,《人体解剖》课是用英文讲的。
“要知道,百分之五十与医学有关的专业词汇都是解剖词汇。如果你们用英文学好这门课,以后就能很轻松地和国际接轨,阅读专业文献、和国际友人交流就不会有太多语言障碍了。”自先生用英文说道。白先生说英文像金鱼吐水泡一样,是一种生理需要。自先生是这门科的主讲,他一手拿烟,一手拿粉笔。他十四岁开始抽纸烟,二十四岁开始教解剖,今年他六十二岁。一手黄,一手白,无论黄白,都不是肥皂洗得掉的颜色。
“那我们就可以当假洋鬼子了。”我们齐声用中文兴奋地说。
“不知道中文名词,那以后怎么给中国人看病呀?校长说我们学校是医学界中的黄埔,要把我们培养成医、教、研三位一体的全才,二十一世纪中国医学的领军人物。我们将来要给中国的老爷爷、老奶奶、大闺女、小媳妇看病,不能光想着出国开会、收外国药厂红包、和外国教授吃宴会呀。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呀?”厚朴是个胖子,他举手提问,胖脑门上渗出细细的汗珠。
“这叫什么?”白先生指着厚朴的胖脑门,用中文问。
“屁股。”我们齐声回答。
“还有别的关于中文名词的问题吗?”
“没了。”
血管、神经、肌肉、骨骼。血管有分支,神经有变异,肌肉有附着点,骨骼有隆起。我们暗恨爹妈为什么把自己生成这个样子。学了这门课之后,我才开始坚信外星人的存在,人类绝对只是生命进化中的一个环节,远远没有到达终点。
生命的进化应该是螺旋状上升的,在某一点上会具有比过去的某一点更高层次上的相似。一百万年后,人类没准又像低级动物一样,只由不分化的内、中、外三个胚层组成,像蒋某人教训的一样:生活简单,思想复杂。到了那时候,没有人再学人体解剖了,白先生这种人被称为古人类学家,一个国家只许养俩,放在国家自然博物馆里,帮助小学生们感受人世沧桑,讲解人的由来。
其实,我们不怕考试。六岁上学,至今几乎已经念了二十年的书,有过三四十个老师,大小百来次考试,变换花样骂过各种老师几千次祖宗。我们对考试是如此熟悉,以至于考试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考试会呈周期性地到来,仿佛榆叶梅开花,元旦、春节、每月的补贴。已经习惯,没有任何新鲜,可以麻木地对待,仿佛榆叶梅花开去照相、月经前买卫生巾和春梦后洗内裤。再说,我真是无所谓。
几乎从十岁以后,我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竞争心。我没有学过,所以一直也不懂如何和别人争,*主要的是我找不出和别人争的理由。我老妈说,我因此注定不能成为富甲一方的人物。我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一些仿佛不可或缺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孔丘没有笔记本电脑、手提电话,却照样伟大;李渔没有盗版的淫秽视盘、蕃石榴味的避孕套,却照样淫荡。没有熊掌,可以吃鱼。没有鱼,可以去天坛采荠菜。饭后没有保龄球、KTV等等娱乐,我们可以散步,体会食物在身体里被消化、吸收的感觉,然后我们大便。大便不仅仅是一种娱乐,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行方式。还有很多人在大便中升天,更多的人死去。当然,这一切需要智慧。抬头望望天上数不清的星星,想想生命从草履虫进化到狗尾巴草再进化到人,再琢磨一下心中患得患失的事情,你也会有一点儿智慧。争斗的人、追逐的人、输的人、赢的人,都是苦命的人、薄福的人。事物的本身有足够的乐趣。C语言有趣味,《小逻辑》有趣味,文字有趣味,领会这些趣味,花会自然开,雨会自然来。如果你含情脉脉地注视一个姑娘三年,三年后的某一天,她会走到你身边问你有没有空一起聊聊天。
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曾经含情脉脉地看了我的初恋情人三年。初中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学校,我已经听说过她的名声。关于她如何美丽的传闻和《少女的心》、《曼娜回忆录》等手抄本一起,在我周围流传,和做不完的习题、翻修不断的东三环路共同构成我少年生活的背景。高中的时候,她坐在我眼角能扫到的位置。如果她是一种植物,我的眼光就是水,这样浇灌了三年,她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如此湿润的原因。
三年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简直有三辈子那么长,现在回想起来,搞不清是今世还是前生。
我很难形容这三年中的心情,有时候想轻轻抱一下,有时候想随便靠一靠,*终都一一忍了,心似乎一直被一簇不旺却不灭的小火仔仔细细地煎着。听说有一道味道鲜美无比的猪头大菜,做法早已经失传,行家讲关键是火候,那种猪头是用两寸长的柴火煨三天三夜才做成的。每隔半小时添一次柴,一次只添一根柴火,三天三夜之后才熟。三年高中,一天一点儿的小邪念就算是两寸长的柴火,三年过后,我似乎也应该成熟了,像猪头一样。
后来她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上大学,于是通信,因为同学过三年,有一起回忆的理由。记得忽然有一封信,她对我的称呼少了姓氏,只是简简单单一个名字。她原来浅浅深深、云飞雪落的基调却变得严肃起来,开始谈起国内形势、艺术表现和学业就业等等重大问题。我回信说,国内形势好啊,有空来玩儿吧,洋鬼子建的旧燕京大学味道很好。那是一个夏天,在北大的静园,我们坐在一条长凳的两端,四下无人,周围尽是低矮的桃树和苹果树,花已落尽,果实青小,远未成气候的样子。我们的眼睛落在对方身体以外的所有地方。她长发长裙,静静地坐着,头发分在左右两边,中间一帘刘海低低地垂着,让我心惊肉跳。我说我索性讲个故事吧,话说一个男孩如何听说过一个女孩,如何看了她三年,如何在这种思路中长大。她说我也讲个故事吧,话说一个女孩如何听说过一个男孩,如何想了他三年,如何在这种思路中不知所措。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在狂喜中一动不敢动。我想,这时候,如果我伸出食指去接触她的指尖,就会看见闪电;如果吐一口唾沫,地上就会长出七色花;如果横刀立马,就地野合,她会怀上孔子。
两年后,我上了生物统计之后才明白,这种超过二十七个标准差的异类巧合,用教授的话说就是:扯淡。
我虽然不喜欢争夺考试的名次,但是我喜欢看热闹,看别人争,从中体会色空。从小就喜欢。
我家对面,隔一条马路,是一所中学,文革的时候以凶狠好斗而闻名。喊杀声起,我马上会把正在看的课本扔到一边,一步蹿到阳台上,马路上旌旗飘扬,顽劣少年们穿着深浅不一的绿军装。斗殴有文斗和武斗。文斗使拳脚,关键是不能倒地,倒在地上就会被别人乱踢裆部和脸,以后明里暗里都没办法和姑娘交往了。武斗用家伙,军挎里揣着菜刀、管叉和铁头木把的手榴弹,家伙使得越朴素的人越是凶残,我见过一个蓄一撇小黑胡子的人用一个手榴弹把别人的脑浆子敲出来,白白的流了一地。文斗常转化成武斗,被拳脚打得鼻青脸肿的人从地上爬起来,用军装的下摆堵着流血的鼻子,冲着打他的人喊:“你丫有种别走,在这儿等着。”打他的人多半会一边轻蔑地笑着,一边等着,武斗往往就在之后进行,仿佛幕间休息一阵,下一幕接着开始。斗殴的缘起有时候会非常简单——一个新款的军挎,相争的两人一手扯住军挎带子,另一手抡着板砖砸对方的头。谁也懒得躲,谁的头抗不住板砖先倒下去,军挎就归另一个人。有时候涉及女人,两路人马在马路中间厮杀,充当祸水的女人在一边无能为力地哭,眼泪落到土地上,溅起尘土,没人理她,更没人听得见她的哭声。她长得可真美,两把刷子垂在高高的胸前,又黑又亮又顺,随着哭泣的动作一跳一跳的。要是我有一身绿军装和菜刀,我也会忍不住冲到楼下为她拼命的,可是我家的菜刀被妈妈锁起来了。斗殴比现在的进口大片好看多了。我的多种低级趣味都是“四人帮”害的,但是相隔时间有些远,不能像哥哥、姐姐那辈一样,把自己不上进的原因都推给那四个家伙,然后自己心安理得。
我的同学们应付着《人体解剖》考试,这也有热闹看,他们用尽杀招,彼此歃血为盟,考试时不许装聋作哑,答案不许写小,否则私刑伺候——你的被子里会发现死老鼠,你的女友不会再相信你遇见她之前是处男。各自出动,向高年级的学长咨询:“你们解剖课都考了些什么?”老师们其实是很懒的,每次考试试卷之间的差别不大。学长的记忆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模糊不清,但是不同的人模糊的地方也不同。咨询来的信息汇总,就是一张很完整的藏宝图。
当然,还有美人计,央求些环肥燕瘦或是声音婉转莺啼如寻呼台小姐的女生去迷惑白先生,把重点套出来。“以后考妇产科、儿科的时候,我们再替你们献身,尽遣酷哥猛男将老太太们迷倒。”男生保证。
作者简介
冯唐,男,1971年生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妇科肿瘤专业,美国Emory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居香港,就职于麦肯锡公司(McKinsey&Co.),从事旧时被称为军师、幕僚或师爷的工作。
著有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欢喜》、《北京北京》,散文集《活着活着就老了》。
-

三重门
¥7.7¥24.0 -

科学?
¥18.1¥42.0 -

华胥引
¥25.8¥86.0 -

听说桐岛要退部
¥11.6¥35.0 -

锦堂风月落花尘
¥11.2¥32.0 -

时光会记得/独木舟
¥17.8¥48.0 -

好想告诉你-9
¥10.4¥14.8 -

鸡小说集
¥14.4¥38.0 -

黑莲花攻略手册
¥26.5¥69.8 -

时间租赁馆:陪你把孤单变成温暖
¥15.2¥40.0 -

人生电影院
¥30.7¥39.8 -

草月译谭:青春的反证(长篇小说)
¥18.8¥43.8 -

一路繁花相送-(全二册)-完美纪念版
¥18.4¥49.8 -

四海鲸骑.下(九品)
¥15.1¥39.8 -

第十二夜-中国当代作家获奖作品典藏
¥9.8¥28.0 -

桐花中路私立协济医院怪谈
¥15.5¥42.0 -

余生,请多指教/柏林石匠附时光日记本
¥14.7¥39.8 -

急诊室女神
¥31.1¥36.0 -

哑舍-贰
¥15.1¥35.0 -

南方有令秧
¥11.8¥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