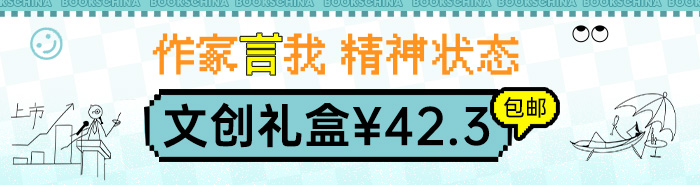5分
中央典藏版((羊脂球))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豆瓣8.8分推荐!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是自自然然地讲故事的典范,也是以世俗故事登上经典殿堂的典范。柳鸣九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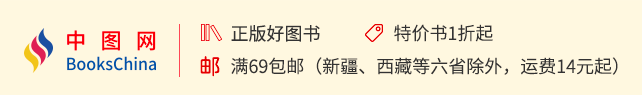
- ISBN:9787511725479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304
- 出版时间:2015-02-01
- 条形码:9787511725479 ; 978-7-5117-2547-9
内容简介
《羊脂球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世界名著典藏》收录莫泊桑多篇短篇小说。莫泊桑讲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小人物,这些人物构成了法国社会的主体,他们身边发生的故事,便构成世俗社会的万象。他写作的很多篇目,如《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都已成为世界名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是自自然然地讲故事的典范,也是以世俗故事登上经典殿堂的典范。
目录
幸福
戴奥菊尔·萨波的忏悔
在旅途上
项链
一个诺曼底佬
两个朋友
骑马
西蒙的爸爸
在一个春天的夜晚
小狗皮埃罗
羊脂球
瓦尔特·施那夫斯奇遇记
我的叔叔于勒
勋章到手了
绳子
小酒桶
烧伞记
一个儿子
莫兰这头公猪
一个农庄女工的故事
珠宝
壁柜
港口
一次郊游
爱情
修软椅的女人
附录莫泊桑:《论小说》
一个被逼出来的译本
节选
羊脂球
一连数日,败军残部乱哄哄地从城里穿过。这哪里还像军队,简直就是一群零乱不堪的散兵游勇。一个个胡子拉碴,脏乎乎的,军服破破烂烂,既无军旗,又无番号,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走。他们都显得垂头丧气,精疲力竭,而且脑子也麻木了,不能思维,没有主意,仅凭简单的惯性,机械地移动脚步,只要一停下来,就会因为太累而倒在地上。看起来,这些被征入伍的,大多数本来都是生性平和、与世无争、安分度日的年金领取者,而今一个个被枪支压得腰弯背驼;另外还有一些年轻力壮的国民别动队队员,他们容易激昂慷慨,也容易惊慌失措,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仓皇逃命;同时还零星夹杂着穿红色军裤的士兵,他们是不久前在一次大战役中被击垮的某师团的残余;也有一些穿深色军装的炮兵,同形形色色的步兵并列往前走;偶尔,还有个把头戴闪亮军盔的龙骑兵,拖着沉重的步子,跟着负荷较轻、走路较为轻快的步兵,显得格外吃力。
随后,一批批游击队员也穿城而过,每队都有一个英勇神武的称号,诸如“报仇雪耻军”、“公民掘墓团”、“英勇敢死队”,等等,但他们的神情作态却像是土匪。
这些游击队的长官,过去都是布商、粮商、油脂商、肥皂商之类的生意人,时势造英雄,凭着有钱或蓄了长长的唇髭,就被任命为军官。且看他们全身披着法兰绒军装,佩戴军衔,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老见他们在讨论作战方案,出言不凡,自称法兰西的胜败存亡全系于他们的肩上。但他们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却心存畏惧,这些兵痞本来就是偷鸡摸狗之徒,勇起来命都可以豁出去,但抢掠奸淫,无所不为。
有传闻说,普鲁士军队很快就要占领鲁昂城了。
两个月以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城郊附近的树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人的动静,有时还神经过敏地误击自己的哨兵,有时荆棘丛里有一只小兔稍动一下,他们就准备浴血奋战。可是,普军即将攻占的消息一传来,他们就纷纷逃回家了。他们的军服、枪械、装备,所有这些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行头,原来还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之内的路碑,现在都不翼而飞,丢失不见了。
*后一批法国正规军总算渡过了塞纳河,准备从圣塞威尔与阿夏尔镇方向退守奥德梅桥。殿后的是一位将军,他由两名副将陪伴左右,也是徒步前行。他神情沮丧,率领着这支残兵,实在无力回天,一个善于征战、攻无不克的民族,竟然惨遭大败,全线崩溃,他本人陷身其中,岂能不沮丧懊恼。
法军既撤,随后城中便是一片沉寂,在静悄悄而又惶惶不安的气氛中,人们在等着将要降临的事。许多大腹便便的生意人,早已在商场上磨尽了男子汉的气概,正惴惴不安地等候占领者的到来,但一想到普鲁士人也许会把店里的烤肉铁扦与切菜刀误认为是武器,便胆战心惊了。
生活似乎停顿了。商店都关门停业,街上寂无人声。偶尔,有个把居民上街,也被这种沉寂吓了一跳,旋即沿墙根匆匆离去。
等待所引起的焦虑不安,反而使人盼望敌军早日进驻。
就在法军撤离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几个普鲁士轻骑兵,疾速穿城而过。没过多久,从圣卡特琳山坡上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与此同时,从通往达尔内塔尔与布瓦纪约姆的两条大道上,另有两大股侵略军潮水般地涌现出来。这三支大军的先头部队,恰好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合。随后,德军大部队就开到,从周围的大街小巷里鱼贯而出,一营营排列整齐,迈着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踏得石板路面嘎嘎作响。
一种陌生而喉音很重的口令声,沿着那些看似空荡而死寂的房舍升起。其实,此时在那些紧闭着的百叶窗后,正有无数双眼睛紧盯着进驻的胜利者:他们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人,可以根据“战时法”任意处置全城人的生命财产。居民们躲在自家昏暗的房间里,惶恐不安,胆战心惊,如同遇到了洪水泛滥与强烈地震,任凭有什么智慧与能耐,都无能为力。诚然,每逢事物的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人类的法律与自然的法则所保护的一切,遭到某种疯狂凶残力量的摆布时,人们都会产生这种惶恐感、战栗感。大地震将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之下,泛滥的洪水冲走了被淹死的农民与耕牛以及房屋的梁木;同样,打了胜仗的军队就要屠杀继续自卫的人,要押走俘虏,要以战刀的名义进行掠夺,要用大炮的轰鸣向上苍表示感恩。所有这些可怕的灾难埋葬了我们对永恒正义的信念,使我们不再像有人教导的那样,去信赖上天的保佑与人类的理性。
在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德军小分队在敲门,接着,他们就进入屋内。这就是入侵之后的占领。战败者的义务由此开始,招待战胜者,当然必须和颜悦色,温良恭顺。
过了一段时间,入侵后的初期恐怖消失了,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许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与主人一家同桌吃饭。有的军官很有教养,出于礼貌,还对法兰西表示表示同情,说自己参加这场战争,并非自愿,心里实在是反感。普鲁士军官竟有这份情感,房主一家自然感谢不已,何况说不上什么时候,还得仰仗他的保护呢。再说,把他侍候好了,也许可以少给几个士兵供饭。既然好事坏事都取决于他,那又何必去冒犯他呢。真要去冒犯他,那就不是勇敢,而是鲁莽了。想当年,鲁昂城的市民确曾鲁莽过一次,英勇保卫了这座城市,使它名扬四海,但物换星移,今非昔比,鲁昂人再也不会犯此种鲁莽的毛病了。从法兰西的处世智慧中,他们总结出这么一个至高无上的结论:只要不在公共场合跟敌对国士兵亲近热乎,在自己家里客气一些并不为过,于是,在外面,彼此装作不认识,但一到家里,就谈笑风生了,每天晚上,大家围炉而坐,德国人久久也不离去。
指15世纪,鲁昂人反抗英王亨利五世的统治。
即使是这座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和平时期的常态。法国人固然不大出门,但普鲁士士兵在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况且,那些蓝色轻骑兵的军官虽佩戴着又长又粗的杀人武器,在马路上大摇大摆,其实他们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并不比去年在那些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轻装兵更为盛气凌人。
不过,空气中多了点什么东西,某种不可捉摸的、陌生的东西,某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异样气息,这种气息扩散开来,无孔不入。它充斥于每家每户之中,广场街道之上,它改变了饮食的味道,使人仿佛觉得离家远行,来到了野蛮而可怕的部落。
战胜者索取钱财,贪得无厌。城里的市民无不如数缴纳,幸好他们确也殷实富足。不过,诺曼底商人越是有钱就愈加吝啬,越舍不得拔毛出血,只要看见自己的财富有一点落进他人手里,就特别心疼。
但是,出了城,沿河往下走两三法里,到克鲁瓦塞、迪耶普达尔或比萨尔一带,船长与渔民经常从水底打捞上来穿着军服的德国人的尸体,他们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有的是被人踢死的,也有被石头砸死的,或是被人推下水淹死的,都已经被水泡得肿胀了起来。河底的淤泥掩藏着不少此类野蛮而合情合理的地下复仇行为,这些无名英雄不声不响地抗敌,比光天化日之下的战斗更要危险,但又得不到扬名天下的荣耀。
因为凡是对外敌的仇恨皆有无穷的感召力,总能激起一些英勇的义士,他们全都出于信念而视死如归。
虽然普鲁士人侵占了全城后实施了铁腕统治,但并没有干过任何一件传闻他们在进军中所犯的那类暴行。于是,城里的市民胆子壮起来了,当地商人重开买卖、招财进宝的欲望又蠢蠢而动。有几个商人原本在勒阿弗尔港有大笔投资,那个港口至今还在法军的手里,所以,他们打算从陆路先到迪耶普,然后再乘船去勒阿弗尔。
他们利用所认识的几名德国军官的关系,从占领军司令部获得了离城特许证。
于是,一辆四匹马拉的旅行大马车整装待发,有十位客人订了座位,他们决定星期二早晨天亮之前就动身,以免招路人围观。
几天以来,气候寒冷,地面也冻硬了。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光景,北风猛吹,刮来大片大片的乌云,大雪纷飞,从傍晚起一直下了一个整夜。
凌晨四点半,旅客们都聚集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他们要在这里上车。
一个个都睡眼惺忪,身上披着毛毯,却也冻得浑身发抖。在一片昏暗中,彼此看不清楚,身上又都穿着臃肿的冬装,看上去就像身着教士长袍的胖神父。有两个男人终究还是认出了对方,第三个人也凑上去,于是,他们就谈开了。一个说:“我这次带老婆一道走。”另一个说:“我也一样。”第三个说:“我也如此。”**个又说:“我们再也不回鲁昂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再逼近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去英国。”三人的打算不约而同,如出一辙,实在是气味相投。
但是,迟迟不见有人前来套车。一个马夫手提一盏小灯,不时从一扇黑洞洞的门里走出来,又立即钻进另一个门洞。马厩的地上有垫草与肥料,马蹄磕地的声音就不响亮了,从屋里传出一个汉子骂骂咧咧地跟牲口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表明有人在搬弄马具,这轻微的声音很快就变成了清脆、持续不断的颤音,节奏随着牲口的动作而有所变化,有时寂静无声,有时又突然猛响一阵,同时伴随着马蹄磕地的沉闷声。
那扇门猛然关上了,一时鸦雀无声。那些有钱人冻得发僵,也都沉默下来,直挺挺地待在那里。
绵绵不断的雪花织成了闪闪发亮的帷幕,徐徐向大地降落,它使万物模糊不清,给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像泡沫一样的雪花。全城一片寂静,一切声响都被严冬埋葬了,只听见雪花落下时的窸窣之声,它微细不清,飘忽不定,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感觉,这细小轻微的动静,仿佛充塞了整个寰宇,覆盖了世界大地。
提风灯的那人又出现了,他牵来一匹垂头丧气、不愿受驱使的马,把它拉到车辕前,系上绳套,转悠了好些圈,总算把马具套好,因为他一手提着小灯,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干活。正当他要去牵第二匹时,他注意到旅客们全都站在那里不动,身上都飘满了雪花,便对他们说:“你们怎么还不上车,车里至少可以避避雪。”
显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听此话就一拥而上。那三个男人先把自己的妻子扶上车,随后也跟了上去。另外还有几个形貌模糊的人,也上车在空位子上就座,一言不发。
车厢的底板上铺了麦秸,旅客都把脚插了进去。坐在里头的那几位太太,带了烧炭暖手的小铜炉,她们点燃其中的化学碳,开始低声数说这种暖炉的优越性,其实她们如数家珍所说的种种,都是老生常谈,无人不晓的。
马车终于套好了,原定四匹马拉,考虑到路滑难拉,又加套了两匹马。这时,有人在车外问道:“人都上齐了吗?”车里有人应道:“全上来了。”于是,马车就出发了。
马车慢吞吞地前进,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轮子陷在积雪里,整个车厢咯吱咯吱作响,像是在呻吟哀鸣。拉车的马老是打滑,气喘吁吁,全身冒热气。车夫不断甩响他的大鞭,四面飞舞,颇像一条长蛇,时而蜷缩,时而伸展,突然一下,长鞭抽在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那马的臀部便往上一拱,用力拉车。
车里人不知不觉,外面天已经亮起来了。那漫天飞舞的大雪,刚才还被车里一位在鲁昂土生土长的旅客形容为棉花雨,现在已经停了。一道昏昏的光线从乌云里透射出来,在厚重乌云的反衬下,雪野显得格外明亮耀眼,地面上时而闪现一排着霜衣的大树,时而出现一座戴雪帽的茅屋。
马车里,借着黎明这种清幽的光线,旅客们开始好奇地互相打量。
车厢里头*舒适的座位上,是大桥街一家葡萄酒批发商行的老板鸟先生及其太太,他们面对面坐着,正在打瞌睡。
鸟先生从前给人当伙计,趁东家做生意失利破产,把店铺盘过来,从此就发了财。他经常以极低的价格,把劣质酒批发给农村的小贩,因而,在朋友与熟人的眼里,他是个狡猾刁钻的奸商,是个脸上笑嘻嘻、肚子里全是花花肠子的地道诺曼底佬。
他的奸商名声已经家喻户晓,以致成为了公开的笑料。兹有一例:在省政府某次晚会上,本地的骄子图奈尔先生,他文思敏捷,见地犀利,专爱编写寓言与歌谣,当时见与会的女士们无精打采,困意甚浓,就拿这位奸商开涮,他提议大家来玩“鸟飞”游戏;此一双关妙语当即不胫而走,传遍了省府的每个客厅,很快就扩散到了全城,引得省内人士整整一个月笑得合不拢嘴。
鸟先生闻名遐迩,还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爱搞恶作剧,爱开各种各样的玩笑,有文雅的,也有粗鄙的;因此,任何人提及他,无不马上补充一句:“这只鸟,真是个无价的活宝。”
他身材矮小,挺着一个圆球似的大肚子,两片灰色的颊髯之间,夹着一张赤红赤红的脸。
他的老婆人高马大,神态凌厉,嗓门洪亮,处事果断,在自家店铺里体现了井井有条与精于算计的风范。她的老公则以自己嘻嘻哈哈的做派,来活跃店铺的气氛。
坐在这对夫妇旁边的,乃卡雷-拉马东先生,他出身于更高的阶层,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棉纺业里颇有声望,举足轻重,他开了三个纺织厂,得过荣誉团骑士的称号,又是省议会的议员。在整个第二帝国时期,他一直是温和反对派的领袖。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历来的行事方式不过是,先持反对立场,用钝器虚晃一招,然后再附和主流派,以求自己得到较高的身价。
卡雷-拉马东太太比丈夫年轻得多,鲁昂驻军中出身贵族的军官,经常从她那里得到安慰。她坐在自己丈夫的对面,娇小而漂亮,蜷缩在毛皮大衣里,正用沮丧的眼光,瞧着这寒碜破旧的车厢。
坐在她身旁的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与夫人,他们的姓氏要算是诺曼底*古老、*高贵的姓氏了。伯爵是个派头十足的老绅士,并且刻意修饰打扮,竭力突出他在相貌上与亨利四世国王的相似之处。根据他的家族引以自豪的一种传说,亨利四世曾使布雷维尔家族的一个妇女婚外而孕,那妇女的丈夫便因此受封为伯爵,并荣升为该省的总督。
在省议会里,于贝尔伯爵与卡雷-拉马东先生是同僚,不过,他在省里代表了奥尔良立宪君主派。他是怎么跟南特一个小船主的女儿结为夫妻的,这始终是个谜。不过他的夫人确也雍容华贵,她还善于交际,技压群芳。据传,她曾得到过路易·菲力普一名王子的爱恋,所以,整个贵族阶层都向她逢迎讨好,她的沙龙在当地要算首屈一指,是昔日风流情致犹存的唯一场所,一般人是难以进去的。
布雷维尔家所拥有的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收入高达五十万法郎。
以上六位是马车上旅客的核心,他们是社会上经济收入稳定、生活安逸平静、有权有势的人士,是信奉宗教、讲究道德的正人君子。
巧得出奇,所有的女客都坐在同一条长椅上,伯爵夫人的旁边还坐着两个修女,她们手里拨着长串的念珠,嘴里在念《圣父经》与《圣母经》。一个是老修女,满脸麻坑,就像劈面挨过一片霰弹似的。另一个身体甚为瘦弱,脸蛋俏丽,但病容满面,胸脯瘪陷,显然她对宗教信仰已经痴迷入魔,使她情愿以身殉教并幻想超凡入圣,以致自己的躯体日渐羸弱消瘦。
在两个修女对面,有一男一女是车上旅客众目睽睽的中心。
那男的颇有名气,人称民主专家科尔尼代,他是所有上流社会人士眼中的危险分子。二十年来,他泡在有民主气息的咖啡店里,不断用大杯大杯的啤酒滋润他那把棕红色的大胡子。他父亲本是一个糖果商,给他留下了一份相当可观的财产,却被他与狐朋狗友吃得精光。于是,他就急不可待地盼着共和国早日再来,以获取他为革命喝了那么多啤酒之后应有的权位。9月4日那天,也许有人故意捉弄他,他真的以为自己被任命为省长了,不料走马上任时,那些在办公室里掌了实权的杂役,却拒不承认他的资格,逼得他立即打了退堂鼓。好在他是个挺好说话的主儿,与世无争,乐于助人,于是,他又以无比的热情,全力组织抗敌守土的防务。他发动大家在平野上挖了一些坑,把附近林子里的小树全都砍倒,在每条大路上都设下陷阱,他对自己这些防御工事甚为得意,认为必奏奇效,所以待敌军一逼近时,他便急急忙忙撤退回城里去了。现在坐在马车上,他想,自己到勒阿弗尔去,要比待在鲁昂更有用,那里正遭普军威胁,很需要构筑新的防御工事。
那个女的呢,是一个被人们称为婊子的主儿。她由于过早发福而闻名,得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叫“羊脂球”。她个头矮胖,浑身圆滚滚的,肥得油脂流溢,连一根根手指也是肉鼓鼓的,只有每个骨节周围才细一圈,皮肤紧绷而发亮,像一串短香肠。她的胸脯丰满挺拔,在连衣裙里高高耸起。她皮肤细嫩,明艳照人,叫人看着就怦然心动,其顾客着实不少。她的脸蛋像一只红苹果,又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牡丹花,脸蛋上部,两只美丽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四周围着一圈又长又浓的睫毛,而睫毛又倒映在眼波里;她脸蛋的下部则是一张媚人的小嘴,两排细牙洁白明亮,嘴唇柔美湿润,简直就是专为接吻而造设的。
据说,她还有许许多多难以言传的媚人妙处。
大家一旦认出了她,那几个正派女士便放肆地交头接耳,评点议论了起来,说什么“婊子”啦,“社会耻辱”啦,等等。虽然是窃窃私语,但声音很高,引得羊脂球不免抬起头来,她把同车的旅客扫视了一圈,目光大胆,并无惧色,且带有挑战的神情。那些人立即都不吱声了,纷纷低下了头,只有鸟先生,还在用不正经的眼光偷偷地看她。
但不一会儿,那三位女士又开始交谈,有这妓女在场,她们突然亲近起来,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亲密的朋友。面对这个无耻的卖淫女,她们似乎觉得必须拧成一股绳,以显示有夫之妇的尊严,因为合法的婚姻从来都鄙视淫行苟合。
那三个男人也同样如此,因为有科尔尼代在场,他们出于保守派的本能而互相亲近了,都以一种蔑视穷人的口气谈论各自的钱财。于贝尔伯爵历数普鲁士军队进攻已经给他带来的损失,还有牲畜被抢、庄稼歉收可能带来的亏空,他说起这些,口气满不在乎,就像亿万富翁那样自信,似乎这些损失只会给他造成一年半载的拮据。卡雷-拉马东先生的棉纺业损失惨重,但他早有防范,先将六十万法郎汇往了美国,以备不时之需,以解燃眉之急。至于鸟先生,他也早做安排,将窖存的葡萄酒全都推销给了法军的后勤部,因此,政府欠了他一大笔款子,这次他去勒阿弗尔就是去取款的。
这三位先生一边谈,一边频频交换友好的眼光。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各不相同,但因为都有钱而感到彼此亲如兄弟,同属于大富豪行会,手一插进裤兜就弄得金币哗哗作响。
驿车行驶的速度极慢,到上午十点钟,还没有走出四法里。有三段爬坡的路,男乘客都是下车步行的。大家开始担心,原定到托特吃午饭,现在看来,天黑以前也难以赶到。每个人都望眼欲穿,但愿能在途中发现一家小饭铺,却不料马车又陷进了一堆积雪,好不容易花了两个小时才脱离困境。
大家都愈来愈饿,饿得心里发慌,却仍然看不到一家小饭铺或小酒店。要知道,一是因为普鲁士军队逼近,二是因为饿狼般的法军部队曾席卷此一地区,附近的店家早都吓得关门停业,逃之夭夭。
只要路旁有农舍,车上的男士都要跑去找吃的东西,结果总是连面包也弄不到,因为农民生性多疑,早已把自家储存的食品都藏起来了,生怕路过的大兵饿红了眼,见到什么就抢什么。
将近下午一点钟,鸟先生公开宣称,他已经饥肠辘辘,支持不住了。大家也都跟他一样,饿得心里发慌,要命的饿劲愈来愈折磨人,他们也就没有半点兴致来说话聊天了。
时不时,有人打个哈欠,紧接着就有人跟着打,于是,大家就轮番打起来,有人张开嘴巴大声打,有人打得文雅些,还用手去捂住往外冒热气的嘴巴,性格、教养与社会地位各不相同,打法也因人而异。
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腰去,仿佛要在自己裙子底下找什么东西,但每次都犹疑一下,看看旁边的人,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身来。每个人的脸都苍白无光,时有抽搐。鸟先生说他情愿付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他老婆做了一个手势要表示反对,随即又平静下来。每当她听说要花钱破费,总是心如刀割,甚至把玩笑话也当真。伯爵说:“的的确确,我是感到不舒服,我怎么没想到带些吃的东西上路呢?”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纷纷跟着责怪自己。
科尔尼代倒是带了满满一壶朗姆酒,他把这壶酒奉献出来,但大家都冷冷地谢绝了。只有鸟先生接受邀请喝了一点,递回酒壶时,他谢道:“还真不错,可以暖和暖和身子,也可以解解饿。”两口酒下肚,他的兴致又上来了,就提议像歌谣里唱的坐小船那样,让大家把*胖的旅客分割吃掉。这话显然是影射羊脂球,对几位有教养的人士来说,这实在是不堪入耳。谁都不去应声附和,唯独科尔尼代笑了一笑。两个修女已经不再念经,双手插在肥大的袖口里,低垂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肯定是在向上天表示她们的痛苦,以答上天赐苦之恩。
三点钟,马车驶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看不到任何村落的影子。这时,羊脂球突然弯下腰去,从长凳底下拉出一只蒙着白色餐巾的大提篮。
相关资料
★莫泊桑之后,实在没有什么短篇小说可言了,不过大狗叫,小狗也叫,我们总还得汪汪汪地汪一阵子。
——契诃夫
★(莫泊桑作品)每一篇都是一出小小的喜剧,一出小但完整的戏剧,打开一扇令人顿觉醒豁的生活窗口,读他的作品,读他笔下的人物,可以是哭或是笑,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
——左拉
★莫泊桑的语言雄劲、明晰、流畅,充满乡土气息,让我们爱不释手,他具有法国作家的三大优点:明晰、明晰、明晰。
——法国著名作家法朗士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莫泊桑(1850—1893),法国19世纪后半期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350多篇中短篇小说,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为突出。1880年,莫泊桑因《羊脂球》而一举成名,震动了整个法国文坛。此后,他辞去公职,笔耕不辍。他在短篇小说上的造诣使他成为一代短篇小说巨匠,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
译者简介
柳鸣九,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
-

24个比利
¥16.4¥39.0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伊豆舞女
¥26.4¥48.0 -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魔山(精装)
¥21.8¥59.0 -

陈忠实短篇小说选萃
¥16.0¥38.0 -

小小小小的火
¥19.2¥52.0 -

魔力的胎动
¥16.7¥45.0 -

无人知晓
¥17.1¥45.0 -

钱德勒短篇侦探小说全集2:找麻烦是我的职业(2019年推荐)
¥14.4¥37.0 -

山月记
¥18.4¥49.8 -

局外人
¥9.8¥35.0 -

春风沉醉的晚上
¥14.8¥40.0 -

悉达多
¥13.4¥28.0 -

我这一辈子:老舍中短篇小说集
¥13.3¥36.0 -

呼兰河传
¥9.9¥38.0 -

魔群的通过
¥21.5¥58.0 -

十日谈-上下册
¥14.7¥37.6 -

偶发空缺
¥20.0¥57.0 -

狂人日记:鲁迅小说全集
¥18.4¥49.8 -

勒索者不开枪
¥14.4¥38.0 -

想我苦哈哈的一生
¥18.1¥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