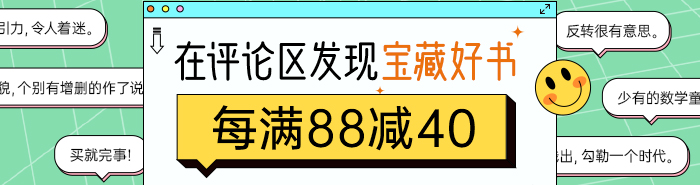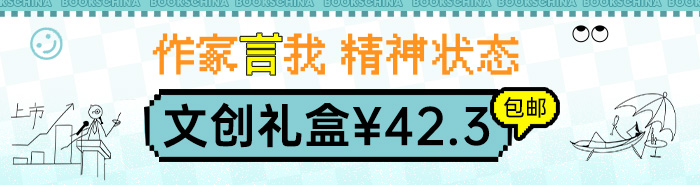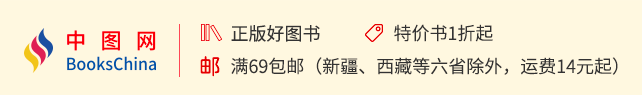- ISBN:9787108061584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249
- 出版时间:2018-08-01
- 条形码:9787108061584 ; 978-7-108-06158-4
内容简介
故居,并不只是一个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更是建筑艺术、家国往事、人格魅力的结晶。作者数年来寻访北京、上海、台北、江南等地的名人故居,通过实地考察,查阅史料,采访后人及亲历者,记述故居的砖瓦门窗、装修布置,及其背后富有时代和性格特色的生活情趣与品位;回眸在“家”这个特殊的舞台,“名人”们不为人知的脆弱和柔情;以老房子为媒介,和宋庆龄、老舍、茅盾、梅兰芳、田汉等曾经的主人进行精神沟通, 作者将建筑艺术、家国往事与故居主人的晚年生活熔于一炉,进而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光影。
目录
百花深处凡人家——丹柿小院老舍故居 001
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头一名/ 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偶然/ 他是很场面的人物/ 趴在床上写作/ 想到河、海,他反倒痛快一点
时过子夜灯犹明——茅盾故居 019
躲进小楼成一统/ 人的一生要走多少路是阎王预定好的/ 房间如手稿 整洁到极致/ 闭门抬笔忆平生
荒芜的田园——细管胡同九号田汉故居 035
安家/“田老大”和“戏剧妈妈”/ 在家中被捕/ 成为大杂院的“文保单位”
难以捉摸的深宅——前海西街十八号郭沫若故居 047
翦伯赞说,你那儿侯门深似海啊/ 红色中国**文人家庭/ 寸心初觉识归途
护国寺四合院与梅兰芳的*后十年 061
登长城、观颐和园、访梅宅/“再思啊再想!”/ 缀玉轩/“旧艺人”/“完人”绝唱
拣尽寒枝不肯栖——林风眠的人生孤旅 075
故乡*伤心 一生执念“劈山救母”/ 北平露锋芒 请齐白石出山/ 诗意栖居西湖 高徒遍天下/
隐居嘉陵江 孕育风眠体/ 独居上海 片刻安宁/ 孤雁离群
从西湖到未名湖,说一声“别了”太沉重——司徒雷登故居 091
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一抹颓墙外,临风待月楼/ “学生的婚礼一般都是在我家举行”/ 北平学运中心/ 盼望以私人身份回燕园过生日/ 归葬西湖
兴风狂啸者的尘世回眸——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鲁迅故居 119
“离租界一百多步之处”的且介亭/ 怜子如何不丈夫/ 月光如水照缁衣/“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陪你抽一支烟好吗?”/“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回不去的呼兰河——萧红故居 151
我家是荒凉的/ 一到后园,立刻是另一个世界/ 后园之外还有更大的地方/ 在玫瑰树下颤怵/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偕隐名山空许约——风雨茅庐郁达夫故居 167
晚霞一抹影澄塘/ 佯狂难免假成真/ 何似举家游旷远/ 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生之地了/
诗人若是住在你的楼上,便是个疯子/ 何处桃源洞里春
徽州阁楼中的胡适本色 187
幽深天井里的沉默房间/ 徽商家庭的兰香书韵/ 忠孝牌坊下的旧式婚姻/ 乡土宗族的荣辱牵挂
梦里不知身是客——蒋宋台北士林官邸 203
从深宫到公园/ 尼克松曾住在蒋介石的书房/ 在官邸夫人说了算/“牛奶洗澡”和“旗袍癖”之谜/ “达令,你要不要去车车”
拒绝回忆 永不卸妆——晚年宋美龄在美岁月 223
“祖母真是位难得的女士”/ 永别台湾/ 我没有回忆录,我也没什么好回忆的/ 打扮上唯一改变的只有高跟鞋的高度
远去的生活艺术——林语堂的阳明山居 235
兼职的设计师与发明家/ 不规则的美丽/ 金玉缘/ 悠闲的哲学
后记
节选
百花深处凡人家 ——丹柿小院老舍故居无论在北平还是北京,灯市口西街都是黄金地段核心街区,东边紧邻王府井,西边是紫禁城护城河。丰富胡同夹在灯市口西街正中, 就像《四世同堂》的小羊圈胡同,“人们若不留心找,或向邮差打听, 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这就是大隐隐于市吧。拐进胡同**户,是老舍的家。一切喧嚣,穿过小院砖砌门楼便自觉收敛,连三月天的沙尘雾霾,遇到满园郁郁葱葱也稍显退散。参观者络绎不绝,脚步都放得很轻,仿佛怕打扰作家的思考、惊落枝头的露珠。逢年过节,这里变得很热闹,老舍纪念馆工作人员按照北京传统装饰小院,组织民俗活动,游客们不像朝拜文豪故居,更像到一位平凡老者家中作客。这应当是老舍自己也会喜欢的纪念方式。当年,他在院中亲手培育了三百盆菊花,上至文人官员,下至送报送奶的工友, 都曾被他邀来品茶赏菊。曹禺写道:“菊,花之隐逸者也。而老舍先生从来不是一个隐士,他是喜欢和朋友们同乐的。”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头一名1949 年10 月,刚刚接到文艺界友人发来的邀请信,老舍就匆匆自美国启程回国。刚做完坐骨神经手术,他是被人用担架抬上轮船的。漂泊半生,老舍为途经的许多城市写下文字,但加起来也比不上故乡皇城根儿。从《骆驼祥子》到《四世同堂》《月牙儿》,他“*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北平在他的笔下,在他的血里。费正清劝他再观望一阵,可是回北京,他等不了。与许多归国名人一样,老舍被新政府暂时安排在北京饭店居住, 夫人和四个孩子抗战期间迁往重庆尚未返京。房间现代化国际范儿, 但写作只能在梳妆台上对着镜子。对老北京人来说,独门独院才有家的味道。“*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1936 年在青岛,他这样满怀憧憬地写道:“像我这样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少小离家老大回,揣着在美国积攒的稿费,老舍想买个自己的房。新中国成立伊始,有产业的人纷纷抛售房屋,价格极低,但全北京没人买。解放区干部、归国文艺人士都听从政府分配,住进宿舍楼或合住大院,“买房置地”似乎不合时势。老舍问周恩来,能否自己出钱买房?周恩来说,你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没问题,你买吧。于是,老舍成为新中国**位获得“特批”可以买房的作家。他赶紧托好友卢松庵和张良辰看房。两人挑中了东城廼兹府丰盛胡同的小四合院。廼兹府大街即今天的灯市口西街,老舍对位置满意, 信任朋友眼光,连看都没有看就定下了。房主开价一百匹布,老舍用五百美金稿费买来布匹换了房。1950 年3 月,夫人胡絜青携儿子舒乙,女儿舒济、舒雨、舒立回京, 简单修葺装修后,4 月,一家人搬进新居。北京人爱在四合院种果树, 图个吉利好看,老舍请人到西山移植来两棵柿子树。柿子圆润火红, 是国画家青睐的题材。胡絜青年轻时就喜欢画画,回北京正式拜师齐白石。三间正房中的东房是胡絜青的画室兼卧室,胡絜青为这间房取名双柿斋,整个新家叫作“丹柿小院”。前半生,老舍住过的地方不下几十处,从1950 年到1966 年,丹柿小院是他一生居住时间*长的地方。小院连房带院占地三百平方米,在四合院中算是规模很小的。郑振铎、高君箴夫妇去祝贺乔迁之喜,看到“狭长的房子有点像列车车厢”;客厅新粉的墙壁因为受潮花糊糊一片,老舍指着墙说,“这是多妙的一幅天然山水画呀”。《四世同堂》里写祁老人十分喜爱自家的小房:“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也值得自傲。”老舍常得意地说:“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头一名!后来好多朋友来过之后羡慕得不得了!连共产党员也跟我学,像赵树理、丁玲。” 当时,北京有两条丰盛胡同。另一条在西四南大街,因明初大将丰城侯李彬府邸在那里,得名丰城胡同,清代讹传为丰盛。而廼兹府原名奶子府,是明代皇子选乳母的地方,后来为了雅致改叫廼兹府, 这里的丰盛胡同得名于天启皇帝的乳母奉圣夫人。西城丰盛胡同宽敞整齐,名气更大,寄给老舍的信件常常错投到那里。老舍去世后,东城的丰盛改了名字,叫作丰富胡同。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偶然在老舍眼里,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像一个古老美丽的雕花漆盒,落在一个勤勉人手里,盒子上的每一凹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一点积垢”。简朴的小院也在他的手里变得精致温馨,处处体现平凡人家的生活情趣。正院一进门是一座木影壁,一般漆红底黑边,老舍请人漆成了草绿、深绿、黄、红、黑五彩影壁。时下初春,两棵柿树刚发新芽不见果实。以往每到秋冬季节,街坊四邻、亲朋好友都会收到老舍夫妇亲自登门送上的“有机柿子”,这是老北京的传统:“送树熟儿”。臧克家记得,那些柿子有方的有尖的,活枝鲜叶,收到他舍不得吃,摆在宜兴泥茶盘上,当作艺术品鉴赏。在伦敦、青岛住小洋楼的时候,老舍*怀念的就是北平“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在丹柿小院,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每一个到过老舍家的人,描述他家的样子,必从满园鲜花说起。1961 年,法国汉学家贝热隆到老舍家做客。谈文学时他们通过翻译人员,有一种公事公办的色彩,谈到花时,老舍兴奋地直接用英语聊起来。十几年后,贝热隆半调侃地回忆道:“单凭这种对鲜花的爱好,在某个时期就可以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就像普通的北京老爷子一样,老舍颇为他的花得意,总想秀给别人看。昙花一现定叫朋友秉烛夜游;金秋时节,菊花开了,更是丹柿小院的盛事,必邀大批朋友轮番饮酒赏菊。老舍夫妇在院中养了多达三百盆菊花,品种近一百,恐怕植物园也不过如此。培植方法是老舍跟他哥哥舒子祥学来的。舒子祥拉过洋车、当过巡警,骆驼祥子的原型就是他。老舍自言,他对花像好朋友似的关切。“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了,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夏天暴雨,邻家的墙倒了, 砸死一百多棵菊,“全家几天都没有笑容”。正房中间是客厅,面积不大,但几把沙发、一张小圆茶几,也够三两知己舒适畅谈。当年贝热隆环视客厅,瓷器、扇子、挂画叉竿, 老舍收集的各式手杖、镀金的球型时钟,无不让他感叹,“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偶然。这位作家把他的生活环境整理得有条不紊,以他写作的那种细腻来布置一切”。老北京人,尤其是旗人,无论贫富,讲究个体面干净。家具陈设, 老舍每天至少亲自擦拭一遍。红木的旧式多宝格和条案上,摆着他淘来的古玩和工艺品。老舍纪念馆副馆长王红英告诉我,老舍先生在“文革”刚开始就去世了,大规模抄家还未开始,这些藏品也就因此大部分保存下来了。可惜的是老舍精心收藏的一百多把名伶手绘扇面,都被抄走,后来被低价出售了。老舍搞收藏,标准只有一个:他喜欢。至于是真是假,完整还是残破,值多少钱,他都不管。郑振铎是海内闻名的大收藏家,与老舍相熟多年不见外,进客厅四处看看瓶瓶罐罐,轻轻说了声:“全该扔。” 老舍一笑:“我看着舒服。” 大圆桌上每日必摆插着鲜花的花瓶,和盛满时令水果的果盘。每天,老舍把水果一个个拿出来擦好,把果盘也擦干净,再把水果摆回去。二十出头时老舍单身在英国,几年没按时吃饭,得了胃下垂和神经性肠炎,不能吃生冷食物,水果摆出来只为好看,闻着清香。墙上的“天然山水画”早已被名家画作取代。老舍**张藏画是1933 年托许地山向齐白石求来的《雏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客厅西墙是老舍“私家美术展”,十天半月换一轮。现在来到故居,可以看到墙上挂的是李可染的《耕牛图》,这是抗战期间,老舍在李可染的重庆画展上购得的。画作右首题字为老舍所拟,齐白石书写:“当时政治教人民置农器,未教人民读农器谱。可染以耕牛为农人之首,真善教人也。”一画荟萃三名家,是老舍纪念馆镇馆之宝。副馆长王红英告诉笔者,这是老舍去世前*后一幅亲手挂上的画。丹青寂寞,迎来许多观赏过客,却再没等到主人归来, 将它摘下收起。他是很场面的人物1950 年6 月,老舍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这个职位的确非他莫属,不仅因为他文学成就高,更因为他人缘好。抗战期间,大后方文人就推举他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如林斤澜所说:“傅雷是个书呆子,老舍先生可不是。他是很场面的人物,有老北京那种外场的本事。什么曲艺、戏曲、书、画界都能交往,在文艺界也如此。” 所谓“外场的本事”,是三教九流都能交往。老舍的客厅并非文人雅士专属的高端沙龙,对待朋友,老舍没有贵贱之分。给老舍按摩治腰腿疼的刘世森回忆道,1954 年秋天一个晚上,老舍带彭真来家里赏菊,刘世森当时并不是正式的大夫,看见领导来了想赶紧回避, 老舍叫住他:“别走哇!这是咱们的市长,见见他好嘛!”于是刘世森就留下一起饮茶赏菊。冬天,刘世森帮老舍把一盆二百多斤重的腊梅搬进屋里,老舍震惊于他的力气,坚持要给他下二斤面,刘世森说吃不了,老舍对保姆说:“不行!给他下二斤!”还嘱咐一定多放炖肉,浇肉汤。作家黄秋耘有段时间常去老舍家帮他起草报告,渐渐发现,小院总有些不寻常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小孩, 一见老舍就像《茶馆》里一样,照旗人的规矩打千儿作揖,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赶紧扶起,请进屋里倒茶递烟,临走再塞点钱给对方, 说是给孩子买点心吃。老舍告诉黄秋耘,这些人有的给行商当过保镖, 有的在天桥卖过艺,有的当过“臭脚巡”,都是他作品中的“模特儿”。“现在他们穷困潦倒,我还有俩钱儿,‘朋友有通财之义’嘛!别见笑, 我这人是有点封建旧思想。”说罢哈哈大笑。《我这一辈子》《断魂枪》, 每一篇传世之作,都是老舍交了真朋友才得来的。老舍家的菜、酒、茶、花,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龙须沟》首演成功,老舍大宴演职人员。按照老北京的规矩,在自家院里搭大棚砌灶,一个大师傅带几个小伙计背着大饭锅来,做了一百多道菜。擅写美食的汪曾祺念念不忘:“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好的芥末墩!”那是胡絜青在老舍指导下千锤百炼的招牌菜。白菜只取心儿,用开水浇,不能下锅焯,焯了就会太烂影响口感;腌的时候码一层白菜,撒一层芥末料;用讲究的容器密封存放几天。不知试验了多少次,才达到老舍要求的标准。老舍很愿意让朋友们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汪曾祺吃到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别处没有,以后再没吃过。酒是“敞开供应”的,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多少喝多少。曹禺坦白,某次受邀来丹柿小院赏菊,他“几杯黄酒到了肚里,竟颓然醉倒在桌下,四座笑声朗朗,朋友们是那样欢悦”。也有很多时候,老舍领客人到家附近下馆子。当初老舍看上丹柿小院这处房,一个重要原因是离王府井老字号和隆福寺小吃近。东来顺、萃华楼、仿膳饭庄,是老舍*常去的店,有次老舍宴请吴组缃, 吴组缃颇感惊讶,店里的厨师和服务员,和老舍见面亲如家人。在萃华楼不用点菜,服务员看人数就能按老舍喜好安排合适的菜单,干炸丸子、糟熘鱼片、芙蓉鸡片、乌鱼蛋汤必点。仿膳饭庄至今在北海公园原址,大门口挂的仍是老舍题写的匾额。趴在床上写作了解老舍的人都知道,老舍好客,上午拜访却是不受欢迎的。他一生保持老北京人的习惯,早睡早起。大多数作家喜欢挑灯夜战,而老舍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是清晨和上午。起床先浇花,得腿病之前, 还要打太极拳,在院子空地练练刀枪棍棒,然后就钻进耳房一直写到吃中午饭,其间唯一的休息是不时出来伺候花。午饭后点上一支烟, 坐在那儿一声也不吭。家人知道他在构思,轻易不和他说话。朋友一律下午登门,若是上午来了,*好自己默默看花。西耳房是书房,与卧室相连。书房极小,只能放开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椅子后面墙厚,老舍别出心裁,请人打了洞,大书橱深嵌其中。背靠书墙,面朝满园芬芳,远胜在饭店对着镜子写作。就在这个斗室之间,他写了《龙须沟》《茶馆》等三十多个剧本,无数散文、杂文和半部《正红旗下》。非解放区的作家在1949 年之后几乎都遇到了转型困境,唯老舍一炮打响,1951 年写了受上下一致称赞的《龙须沟》,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自己并不是完全满意《龙须沟》,他对助手濮思温叹着气说:“对老北京人,他们吃喝拉撒睡在哪儿我都一清二楚;到解放后,可就不行啦,不下去,没有生活啦,戏不够秧歌凑!” 三十几岁时,老舍理想中的卧室应当“有一张极大极软的床。在这个床上,横睡直睡都可以,不论怎睡都一躺下就舒服合适,好像陷在棉花堆里,一点也不硬碰骨头”。在西屋老舍卧室,看到的是一张坚硬的红木床,床帮上镶着有天然水墨纹路的大理石,床屉是棕绳的。因为腰腿病,老舍只能睡硬板,无福享受年轻时期待的软床。老舍去世后,红木床被抄走,所幸遇到明眼人鉴定有文物价值,没有毁坏,“文革”结束后又归还舒家。这张床也算老舍的第二书桌,腰病发作的时候他只能趴在床上写。许多作品的写作过程,于精神和身体上都是艰难痛苦的。陈徒手《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一文中提到,1952 年初,配合“三反五反” 运动,老舍写《春华秋实》,经各级领导审阅指示,修改十二稿,时间长达一年多。1955 年,因为西安抓住一个冒充战斗英雄的骗子, 罗瑞卿请老舍写个戏,这件事本身并不好创作成剧本。从小管老舍叫“二爹”的满族作家赵大年说:“罗可能认为文学就是宣传,这些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老舍也是好面子。”老舍到西安采访,因为坐车时间太长,犯了腰病,回家趴在床上写了《西望长安》。1958 年,老舍因腰疼卧床,人艺导演夏淳来看他,他说:“大家都大跃进,我偏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两个星期之后老舍就拿出了《红大院》初稿,打电话把夏淳叫来,半躺在床上念完了剧本,写的是城市人民公社的故事,其中还有大炼钢铁的情节。就像蓝天野说的,这些戏“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在1956 年秋至1957 年上半年,环境稍宽松,老舍写了《茶馆》。这个剧本是公认的老舍1949 年之后*杰出的作品,出彩的部分仍然是**幕的“旧社会”场景。老舍在那段时间表达过:社会活动太多, 开会太多,希望有充裕的工作时间。他发牢骚说气话:“上午要写作和搬花,就是毛主席叫我开会我也不去。”想到河、海,他反倒痛快一点在各项运动中,老舍的朋友们陆续被批判。老舍像以前一样,请他们吃饭。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不是谁都有勇气做的事。石挥导演并主演过《我这一辈子》,老舍很看重他。石挥被划为“右派”后,情绪低落,来北京办事,躲在小旅馆里不出来。老舍让秘书再三去请,告诉他是在家里见面,石挥这才赴约。丹柿小院一番畅聊后,两人同去萃华楼。老舍拄着拐杖,石挥在大街上模仿起他走路的样子,引得路人围观。这是石挥难得的一次情绪放松。回上海不久, 一代“话剧皇帝”投了黄浦江。1958 年,吴祖光下放北大荒劳改。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是老舍做的媒。老舍叫新凤霞到丹柿小院吃元宵,临走时送她一大摞信纸, 一对永生牌钢笔,嘱咐她“给祖光多写信,一天写一封,信里别发牢骚”。吴祖光成了北大荒家信*多的人。1960 年底,吴祖光回北京,发现新凤霞因生活困难将他收藏的齐白石字画都卖了,他虽深为惋惜,但如此境遇也顾不上许多。临近1961 年春节,夫妇俩在王府井大街散步,迎面遇见手持拐杖的老舍, 老舍一把抓牢了吴祖光说:“我知道你回来了,正要找你,我有一样东西要拿给你看,现在就到我家来吧!”老舍走进里屋拿出一幅画卷, 展开竟是齐白石的玉兰花。他在画店发现画轴签条上写着吴祖光的名字,便替他买了回来。吴祖光问花了多少钱,老舍不告诉他,只应他的要求,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作纪念:“还赠祖光,物归原主矣。” 当年二十出头的王蒙被划为“右派”,他和老舍并不熟,只在几次大会听过老舍发言。王蒙在报纸上看到老舍和外国友人饮酒赏花的报道,“这虽然是文人的一种情调,但在当时的确是政治上的特权”。王蒙又强调,“特权”这个词一点没有批评的意思。“一个文人大模大样饮酒赏菊待客都成了特权,是社会的不正常。”对于老舍本人而言, 这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任务,向外国客人“证明中国作家生活得很潇洒、很有个性”。吴组缃与老舍知交数十年,20 世纪60 年代,他来老舍家喝酒, 听老舍在酒后发过很多牢骚,具体说了些什么,吴组缃不肯多透露。晚年,林斤澜曾几次劝吴组缃写出来,吴说,实话不能写,不写实话没意思,还不如不写。1966 年8 月21 日,老舍在家中和儿子舒乙、女儿舒雨进行了一番谈话。舒雨说起离家不远的王府井大街上,老字号店匾都被砸了, 接着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意儿先收起来。”她指的是客厅多宝阁里摆的那些古董。老舍斩钉截铁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 那是他和子女的*后一次长谈。两天后,1966 年8 月23 日,在孔庙大成门前,在北京文联大院, 老舍遭到毒打。半夜,胡絜青接老舍回家,换下血迹斑斑的衣服,用棉花擦洗他脸上、身上的伤口。老舍躺下休息,一言不发。胡絜青问不出什么,只好回东屋睡觉,睡前把剪刀、皮带全都收起来,以防不测。1966 年8 月24 日,他走出鲜花盛开的丹柿小院,拉着小孙女的手, 拖着长音说:“跟爷爷说,再—见—”然后直奔太平湖。冰心说过,她早有预感,老舍要自杀,一定选择投水。就像《四世同堂》里祁天佑投河前的独白:“想到河、海,他反倒痛快一点,他看见了空旷, 自由,无忧无虑,比这么揪心扒肝的活着要好得多……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 1978 年6 月,在迟来的追悼会上,如同许多没能保留骨灰的人一样,老舍的骨灰盒里,放的是他的钢笔、眼镜等常用遗物,以及血衣残片。特别的是,家人在其中放了几朵茉莉花。老舍喜欢茉莉的味道,茉莉花茶是他每天不可缺少的饮品。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胡絜青搬出丹柿小院,将故居和老舍的遗物、收藏品捐献给国家,成立老舍纪念馆。1999 年,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书房桌上的台历定格在1966 年8 月24 日,一切按照老舍生前的样子布置,跨进小院,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只是这时空中,没有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笔下的场景: 老舍先生在灿烂的秋阳下,挽着袖子给几盆菊花松土。他穿着一件肥大的中式便服,像个老园丁。他见我们进来,放下手里的活儿,拍打了两下手掌,说:“脏,就甭握手了。”然后他迎你走进挂满水墨画的客厅,抱起沙发上的老猫,说:“来客人了, 让开座吧。” 故人寻踪老舍故居: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
作者简介
李鹿,本名李响,原《国家人文历史》主笔,现为高中历史教师。本科、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为新闻学和历史学。多年关注中国近现代史,采访知名专家和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撰写历史普及文章。
-

她们
¥14.0¥46.8 -

树会记住很多事
¥9.5¥29.8 -

安娜.卡列尼娜
¥24.7¥55.0 -

人间草木
¥13.2¥34.8 -

茶,汤和好天气
¥9.0¥28.0 -

几多往事成追忆
¥12.8¥32.0 -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19.2¥60.0 -

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
¥14.4¥45.0 -

到山中去
¥9.6¥30.0 -

哇哈!这些老头真有趣
¥9.6¥30.0 -

瓦尔登湖
¥12.5¥39.0 -

明天照常,小山!托马斯·曼和小狗的山间时光(插图版)
¥13.9¥42.0 -

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
¥11.8¥30.0 -

让死活下去-插图纪念版
¥15.6¥39.0 -

读人生这本大书
¥10.9¥26.0 -

中国小说史略
¥11.2¥35.0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千鹤·碧波千鸟
¥24.0¥48.0 -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16.8¥39.0 -

阿Q正传
¥11.2¥36.0 -

我与地坛
¥2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