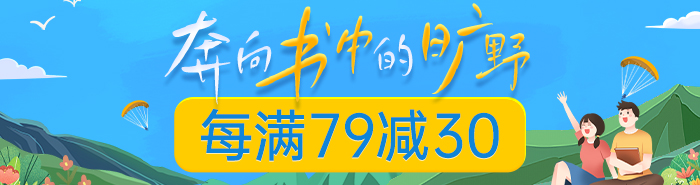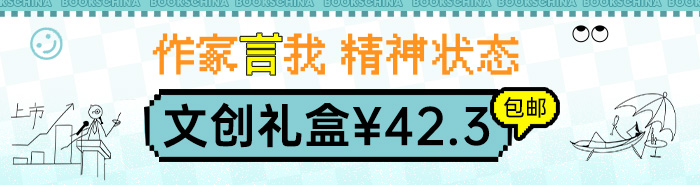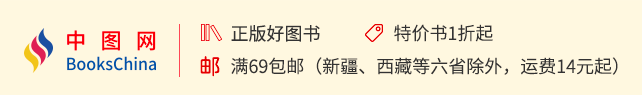- ISBN:9787020155484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210
- 出版时间:2020-03-01
- 条形码:9787020155484 ; 978-7-02-015548-4
本书特色
让中国读者走近茅盾文学奖,让短经典展现中国作家的魅力 荟萃中篇、短篇、散文:一本书读懂茅奖作家 全套21本:呈现中国作家的*阵容 又短又经典,又美又文艺
内容简介
茅盾文学奖自一九八一年设立迄今,已近四十年。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大多在文坛耕耘多年,除了长篇小说之外,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等“短”题材领域的创作也是成就斐然。为更完整地呈现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综合创作实力、艺术品位和思想内涵,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遴选部分获奖作家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的经典作品,编成集子,荟萃成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经典”丛书,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一致好评。 《苍老的爱情》一书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苏童的“短”作品精选集,收录了《桂花连锁集团》《古巴刀》《白雪猪头》《红桃Q》《小偷》《河流的秘密》等经典短篇小说和散文篇目。
目录
目 录
桂花连锁集团
红桃Q
古巴刀
吹手向西
小偷
蝴蝶与棋
水鬼
白雪猪头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骑兵
食指是有用的
河流的秘密
露天电影
过去随谈
八百米故乡
苍老的爱情
南方是什么
沉默的人
沉默,然后看见
节选
苍老的爱情 我相信爱情。历代以来与爱情有关的浓词艳篇读了不少,读到的大多是爱情的缠绵、爱情的疯狂、爱情的诞生和爱情的灭亡。我今天的话题与此无关,是关于爱情的平淡、老迈,说的是一种白发爱情,它不具备什么美感,也没有悬念和冲突,被唯恐天下不乱的文人墨客有意无意地疏漏了,但我肯定这么一种爱情随处可见,而且接近于人们说的永恒。我建议你在左邻右舍之间寻找,而且我建议你排除那些年轻的如胶似漆的爱侣,请将目光集中在那些老朽的夫妇之间,说不定就找到了那一对。 读者朋友能听出来我这里有一对经典。确有经典在此,是我的邻居,现在已经去世多年了。 从我记事起他们就不再年轻了,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我记得那个妻子身材高大,看得出来年轻时候是个美人,而丈夫个子比妻子要略矮一些,但眉目也很端正。许多晴朗的日子里他们出现在街上,妻子端着一盆衣服去井边洗衣,丈夫就提着一只水桶跟在后面;妻子用手拍打阳光下的棉被,丈夫就从家里出来,递上一只藤编的拍子。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们的女儿带着自己的丈夫孩子回娘家,小孩在外面敲门,大声喊叫:外公外婆快开门!门内就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门开了,我看见那对老夫妻的脸,两张笑脸,一张在门的左侧,一张在门的右侧,我惊讶地发现那对老夫妻笑起来嘴角都往右边歪。 但如出一辙的笑容不足以说明老人的爱情。一切都发生在老妇人去世那天。 人总难逃死亡之劫,但老妇人死得突然。是心肌梗死。街上的邻居在为老妇人之死悲叹的同时也为那个做丈夫的担心,说:她这一走让老头子怎么办?老头子能怎么办?他只是默默地守着妻子的遗体,去吊唁的人都看见了他的表情,没有想象中那么悲痛,他只是坐在那里,平静地守着他的妻子,他*后的妻子。到了次日凌晨吊唁的人们终于散尽时,邻居们听见两个女儿再次恸哭起来,他们以为是亡母之痛的又一次爆发。到了清晨,人们看见老夫妻的女儿在家里搭起了另外一张灵床,因为他们的父亲也去了! 这不是我编造的小说,是真事,我所认识的一个老人紧随亡妻一起奔赴天国。女儿说父亲死的时候一直是坐着,看着母亲,后来他闭上了眼睛。他们以为他是睡着了。谁能想到一个人的死会是如此轻松如此自由? 所有的人都为这个做丈夫的感到震惊。是无疾而终吗?不对,依我看老人是被爱情夺去了他剩余的生命,有时候爱情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从此迷信爱情的年轮,假如有永恒的爱情,它一定是非常苍老的。南方是什么 好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一座火柴盒似的工房的三层楼上眺望着视线中一条狭窄的破旧的小街。这是我*熟悉的穷街陋巷之一,也是多少年来被市政建设所遗忘的一条小街——一条没有建设必要的小街,它的一头通往一座清代同治年间修建的石拱桥,另一头通往近郊的某某大队的农田和晒谷场(六七十年代),或者通往新的环城公路和一片新兴的混杂着国有企业村办企业的工厂区(八十年代)。我在午后的阳光中眺望那条小街时,忽然记起我小时候是怎么走过那里去我母亲所在的工厂食堂吃午饭的,我记得桥下的公共厕所,小街从这头到那头的大多数人家的家庭主妇和与我同龄的孩子,我记得他们在路人的视线里匍在餐桌前吃午饭的情景。令我感叹的是好多年过去了,公共厕所还在那里,石子路铺上了水泥,但路面还是那么狭窄而湿漉漉的,人们还是享受着狭窄带来的方便,非常轻易地就可以把晾衣服的竹竿架在对邻的房顶上,走路和骑自行车的人仍然在被单、毛线、西装、裤子甚至内衣下面穿行,这是我*熟悉的小街的街景,紊乱不洁的视觉印象中透出鲜活的生命的气息。一些老人一定已经死了,大多数人还活着,大多数人在小街上养育着儿女甚至儿女的儿女。小街的日常生活一切依旧,就像一只老式的挂钟,它就那么消化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消化着日历上的时间和新闻报道中的事件。它的钟摆走动得很慢,却镇定自若,这钟摆老气横秋地纠正着我脑子里的某种追求速度和变化的偏见:慢,并不代表着走时不准,不变,并不代表着死亡。 那天下午我突然听到了一条南方小街的生存告白,这告白因为简洁而生动,因为世俗而深刻,我被它的莫名其妙的力量所打动: 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描摹我出生的香椿树街,歌颂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子路面,歌颂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歌颂街上苍蝇飞来飞去带有霉菌味的空气,歌颂出没在黑洞洞的窗口里的那些体形瘦小面容猥琐的街坊邻居。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 这是我在那年夏天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南方的堕落》中的开头部分。现在我应该解释它,可我发现我让自己陷入了困境,我在自己的写作中发现了一种敌意,这种敌意针对着一个虚构的或现实中的处所:南方。南方是什么?南方代表着什么?而我所流露的对南方的敌意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首先来自对回忆本身的敌意。人们在回忆之前通常会给自己的回忆规定一种情感立场,粉饰性的美好的戚伤的,或者冷静的客观的力求再现历史的,而我恰好选择了一种冷酷得几乎像复仇者一样的回忆姿态。这是一种偏执的难以解释的敌意。我的所谓南方生活仅仅来自我个人生活与某个地点的关系的机械划定,我的南方是一条横亘在记忆中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街道,而我当时是个孩子。一个孩子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是模糊的,同时也是不确定的,如果说人们对事物的敌意来自此事物对你潜在的或者明显的伤害,我现在却不能准确地描写这种伤害的细节,因此我怀疑这份敌意可能是没有理由的。 所有借助于回忆的描述并不可靠,因此不值得信任,就像我在某篇文章中提及我的一个小学老师,我一直认为我对她的记忆非常深刻,我以为我在还原一个过去的人物,可是甚至她的籍贯和家庭背景后来都被我的其他小学老师证明是错误的,唯一准确的是我对她外形面貌的描述。一个事实有时让你恐慌,可靠的东西存在于现实之中,却不存在于回忆之中,如此我不得不怀疑我的敌意了,这敌意其实也不可靠。我也不得不怀疑我的南方,它到底在哪里,我有过一个南方的故乡吗? 大家所崇敬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恰好有一个美妙无比的短篇小说,名字就叫《南方》。“谁都知道里瓦达维亚的那一侧就是南方的开始。”在这篇小说里,南方是从一个地名开始延伸其意义的,而病病歪歪的主人公达尔曼与他手中的《一千零一夜》以及“南方”形成一个孔武有力的三角关系,支撑着作家所欲表达的所有思想空间。达尔曼来到南方,《一千零一夜》始终无法掩盖残暴的冰冷的现实,在杂货铺里,有人向病中的达尔曼扔面包心搓成的小球,于是一个世界上*不适合决斗的人不得不接受一把冰冷的匕首。 南方的意义在这里也许是一种处境的符号化的表达。 我的南方在哪里呢?我对南方知道多少呢? 在我从小生长的那条街道的北端有一家茶馆,茶馆一面枕河,一面傍桥,一面朝向大街,是一座老旧的二层木楼,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像一个善于取景的电影导演一样把它设置为所谓南方的标志物。我努力回忆那里的人们,烧老虎灶的起初是一个老妇人,后来老妇人年岁大了,干不动了,来了一个新的经营者,也是女的,年轻了好多,两代女人手持铁锹往灶膛里添加砻糠时的表情惊人地相似,她们皱着眉头,嘴里永远嘀咕着发着什么牢骚,似乎埋怨着生活,似乎享受着生活,她们劳动的表情是我后来描写的南方女性的表情的依据。更重要的参照物是一些坐着说话的人,坐在油腻的八仙桌前用廉价的宜兴陶具喝茶的那些人,曾经被我规定为*典型的南方的居民,他们悠闲、琐碎、饶舌、扎堆,他们对政治和国家大事很感兴趣,可是谈论起来言不及义鼠目寸光,他们不经意地谈论饮食和菜肴,却显示出独特的个人品位和渊博的知识,他们坐在那里,在离家一公里以内的地方冒险、放纵自己,他们嗡嗡地喧闹着,以一种奇特的音色绵软的语言与时间抗争,没有目的,没有对手,自我游戏带来自我满足,这种无所企望的茶馆腔调后来也被我挪用为小说行进中的叙述节奏。 可是比虚构更具戏剧性的是事物本身,就是前面所说的这家茶馆,就好像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小说和电影处理一个重要场景一样,茶馆*后付之一炬。一九九○年春天,也就是在我写《南方的堕落》前的几个月前,那家茶馆非常突然而无法补救地失火倒塌了。我回到家乡的时候看见的是一片废墟。我在茶馆的废墟上停留的时候感觉到某种失落,可是我的失落不是针对一座茶馆的消亡,而是源自一个写作蓝本的突然死亡,我的哀悼与其说是一人对一物的哀悼,不如说是一个写作者对一个象征一个意象的哀悼。 如果说那座茶馆是南方,这个南方无疑是一个易燃品,它如此脆弱,它的消失比我的生命还要消失得匆忙,让人无法信赖。我怀疑我的南方到底是什么?南方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对我经常描述的一条南方小街的了解到底有多深呢?我对它的固执的回忆是否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触及南方的真实部分呢? 我的头脑中现在一一闪现的仍然是前面那条小街的景物。很抱歉我要说小街上的另一个公共厕所。这个厕所的历史非常短促,我记得小时候它不存在,它所在的位置原先应该是一块空地,空地后面的人家长年地在那里种一些小葱和鸡冠花之类的东西。有一年厕所出现了。一个简陋的南方常见的街头公共厕所,但是修建得十分匆忙,里面的水泥地面甚至都没有抹平便投入使用了,这个厕所对附近的居民充满了善意,只是无人管理,因此很脏也很臭。这是一个特殊的有着某种危险的厕所,因为它面对着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从小区的高楼上可以清晰地看见如厕人的面貌甚至如厕的姿势,所以对于使用厕所的人和小区高楼阳台上的居民来说,厕所造成了双重的尴尬。而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当我在住所的阳台上眺望小街风景时,我怎么也无法忽略厕所的存在,我的目光注定是不平静的,一种暧昧不洁的观察导致了一种更加难以表述的厌恶感和敌意。这厌恶感和敌意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也因为那间厕所造成了我忠实记录小街风情的一大障碍。所幸的是这厕所也一样不能逃脱它灭亡的命运,不同于茶馆的焚毁,这间不必要存在的厕所后来被人填平了,填平以后又在原址上盖了一间房子。后来我发现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住在那房子里,有时候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从窗户里看见那对夫妇坐在里面看电视。我感到很高兴,这几乎是小街多少年来*大的一次改变了,这改变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是特殊的,我走过那里的时候回想这块空地多少年来的变化,突然发现了类似博尔赫斯的《南方》中的三角支撑:小葱鸡冠花、公共厕所、年轻夫妇的家,这是一个关于小街回忆的三角支撑,由此我依稀发现了我所需要的南方的故事。 可是这是南方吗?我同样地表示怀疑。我所寻求的南方也许是一个空洞而幽暗的所在,也许它只是一个文学的主题。多少年来南方屹立在南方,南方的居民安居在南方,唯有南方的主题在时间之中漂浮不定,书写南方的努力有时酷似求证虚无,因此一个神秘的传奇的南方更多地是存在于文字之中。它也许不在南方。 我现在仍然无数次地走过那条小街,好多年过去以后我对这条小街充满了敬畏之情,这是一只飞雁对树林的敬畏,飞雁不是树林的主人,就像大家所说的南方,谁是南方的主人?当我穿越过这条小街的时候我觉得疲惫,我留恋回忆,我忍不住地以回忆触摸南方,但我看见的是一个破旧而牢固的世界,这很像《追忆逝水年华》中盖尔芒特*后一次在贡布雷地区的漫步,“在明亮的灯光下世界是多么广阔,可是在回忆的眼光中世界又是多么的狭小!”而一个作者迷失在南方的经验又多么像普鲁斯特迷失在永恒与时间的主题中。 瓦尔特·本雅明说得好:“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时间去经历命中注定要经历的真正的生活戏剧。正是这一缘故使我们衰老。我们脸上的皱纹就是激情、恶习和召唤我们的洞察力留下的痕迹。但是我们,这些主人,却无家可归。” 是的,我和我的写作皆以南方为家,但我常常觉得我无家可归。
作者简介
生于1963年,江苏人。著名作家。2015年,长篇小说《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

24个比利
¥12.1¥39.0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伊豆舞女
¥24.0¥48.0 -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魔山(精装)
¥18.9¥59.0 -

陈忠实短篇小说选萃
¥14.1¥38.0 -

钱德勒短篇侦探小说全集2:找麻烦是我的职业(2019年推荐)
¥11.8¥37.0 -

小小小小的火
¥16.6¥52.0 -

魔力的胎动
¥14.4¥45.0 -

勒索者不开枪
¥12.2¥38.0 -

我这一辈子:老舍中短篇小说集
¥10.8¥36.0 -

春风沉醉的晚上
¥12.8¥40.0 -

无人知晓
¥17.1¥45.0 -

悉达多
¥12.0¥28.0 -

想我苦哈哈的一生
¥16.0¥42.0 -

十日谈-上下册
¥12.0¥37.6 -

比利战争
¥11.7¥39.0 -

偶发空缺
¥20.0¥57.0 -

呼兰河传
¥8.0¥38.0 -

大染坊
¥12.6¥39.5 -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神曲(精装)
¥14.4¥45.0 -

山海经
¥20.4¥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