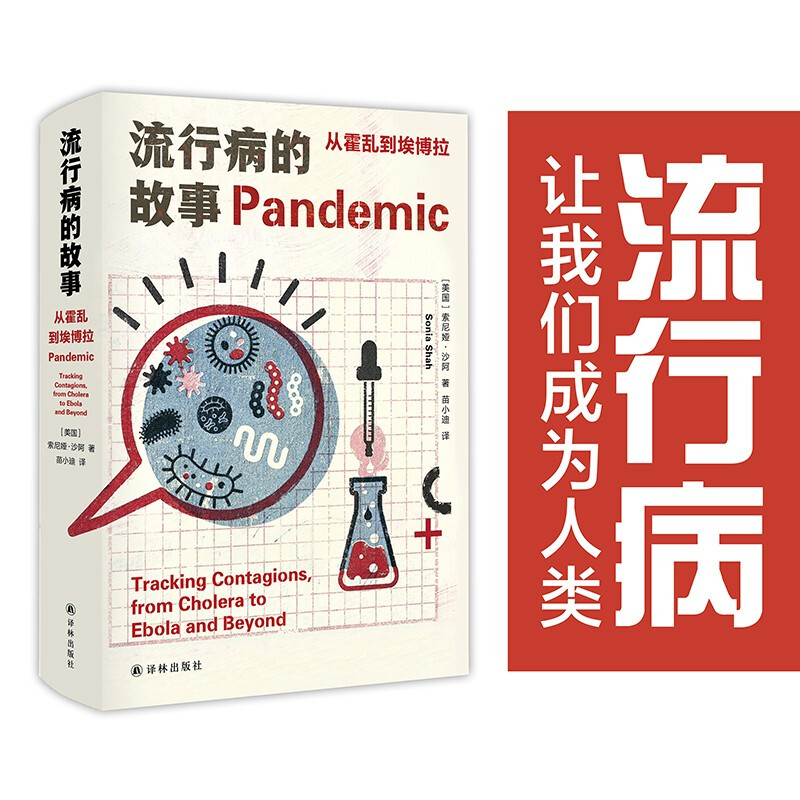- ISBN:9787544787802
- 装帧:一般纯质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436
- 出版时间:2021-11-01
- 条形码:9787544787802 ; 978-7-5447-8780-2
本书特色
1.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严谨的历史考证+靠谱的科学解读=鲜为人知的流行病真相 流行病始终伴随人类的进化历程,无论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基因变异,还是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甚至人们对美和浪漫的认知,都源自流行病的巨大作用。流行病,让我们成为如今的人类。 2.回溯人类与流行病的共存史,解密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就与隐忧 人类为了健康竟曾吸食粪便?早年的纽约、伦敦等工业化城市如何惨痛挨过流行病疫情?在12世纪就成功实施的检疫隔离措施,为何数百年来屡遭抵制?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构建一个速度更快、织网更密的全球疾病监测系统? 3.屡获大奖的科普作家,备受好评的典范之作 本书作者索尼娅·沙阿出身医学世家,曾研习新闻、哲学与神经科学专业,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多年来深耕医学科普领域。《流行病的故事》出版后,入选《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全美科学作家协会奖、纽约公共图书馆海伦·伯恩斯坦奖决选名单,《纽约时报》编辑选择书单。 4.译林出版社“医学人文丛书”:有温度、有关怀的医学故事 《流行病的故事》收录于梁贵柏博士主编的“医学人文丛书”,丛书其他已出版作品包括《重症监护室的故事》《看不见的敌人:病毒的自然史》《公共卫生史》《剑桥医学史》。
内容简介
过去数十年来,我们拥抱着工业化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生活方式,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感受到流行病的存在。然而,我们对流行病的认知充斥着误解、轻视或恐惧。 在《流行病的故事》中,屡获大奖的科普作家索尼娅·沙阿向我们展现了关于流行病鲜为人知的真相,深刻揭示了暗藏在每次疫情背后的气候、社会、文化等因素。流行病侵害着人类健康,有时甚至令国家陷入危机。但另一方面,它也改变了人类的进化轨迹,塑造了人类的行为与文明。 人类与流行病之间的较量将持续存在。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更需要借助科学与历史的力量,全球紧密合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流行病风险做好准备。
目录
微生物的复归
**章 跳跃
在活禽市场、养猪场和南亚湿地跨越物种屏障
第二章 移动
病原体通过运河、蒸汽船和喷气飞机进行全球性传播
第三章 污秽
从19世纪的纽约市到太子港的贫民窟,一股涌动的污物潮
第四章 人群
传染病在全球性城市里的扩张
第五章 腐败
私人利益vs.公众健康,阿伦·伯尔和曼哈顿公司用霍乱荼毒纽约市全记录
第六章 怪罪
霍乱暴动、艾滋病否定主义和抵制疫苗
第七章 解药
对约翰·斯诺的压制,以及生物医学的边界
第八章 海洋的复仇
霍乱范式
第九章 大流行的逻辑
古代大流行:失落的历史
第十章 追踪下一场传染病
重新设想我们在微生物世界中的位置
专业词汇表
注释
致谢
索引
节选
第三章 污秽(节选) 排泄物是病原体进行人际传播的完美载体。粪便从人类体内刚刚排出时,满是细菌和病毒。以重量计算,粪便的10%由细菌组成,每克粪便*多包含10亿个病毒粒子。一个典型的人类个体,每年能产出13加仑的粪便(以及130加仑的无菌尿液),创造出一条富含微生物的垃圾河。除非我们控制和隔离这些垃圾,否则它们很容易就会沾到脚底,贴到手上,污染食物,渗入饮用水中,使病原体从一个受害者传播到另一个。 幸运的是,几个世纪前,人们就已经明白,要实现健康的生活就必须将垃圾与我们自身隔离。罗马、印度河流域与尼罗河谷的古代文明,早已知道如何处理垃圾,使其不至于污染食物和水源。 古罗马人会用水将垃圾冲离他们的居住区,任其在荒郊野外腐烂。他们通过木制和锡制管道网络将偏远、无人居住的高地上的淡水引入城市,这些管道每天都能给一个住户运来300加仑的淡水,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数据,这是现在美国人平均耗水量的三倍。罗马人主要将这些水补给浴室和公共喷泉,但也会用在公共厕所里——大型水沟上方摆着带锁眼形开口的长凳,人们坐在上面如厕,同时一股新鲜的水在他们脚下流动。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用水冲走排泄物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从排出到分解这段关键时期内,不需要安排人手去处理富含微生物的粪便。水就这么把它冲走了,简简单单。但这样做的缺点是会使排泄物移动,由此产生大量被污染的流动水,而这些流动水会污染饮用水源(以及许多其他东西)。既然对新鲜清洁水源的喜爱让古代人建造出了供水管网,那自然也让他们明白了清洁饮用水的重要性。人们会嘲笑那些在未经过滤处理的水里洗澡的人,更别说那些直接喝的人了,他们还遵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建议,只饮用烧开后的水。 不管怎么说,这些卫生措施本应该在任何时代存续,但事实并非如此。到了19世纪,古罗马人的欧洲后代们来到纽约定居,但他们已然遗忘了祖先的良好习俗。他们很容易接触到彼此的排泄物,以至于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物和饮品中都可能含有两茶匙的粪便。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180度的转变与4世纪基督教的兴起有关。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维持了仪式化的卫生习惯,更别提印度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了。印度教徒在每次做完“不洁”行为和每次祈祷后都必须洗澡。穆斯林每天须做五次祷告,而每次祷告前都必须清洗三遍,进出其他许多场合前也必须清洗。犹太人乐于在每次用餐、祷告、上厕所前后洗澡。相形之下,基督教对用水清洁的卫生仪式没有做任何详尽规定,一个好的基督徒只需要在他的面包和酒里洒些圣水,就能让这些食物圣化。毕竟,耶稣本人在坐下来用餐前也是不洗手的。 知名的基督教徒会公开宣扬用水清洁自身乃是表面的、肤浅的、堕落的。有人这么说过:“一副干净的皮囊和一套干净的衣服,装扮的是一个不干净的灵魂。”*圣洁的基督徒会穿着满是虱子的刚毛衬衣,算是世界上*不爱干净的人之一了。果不其然,537年哥特人毁坏罗马水道后,基督教欧洲那些不爱洗澡的领袖们压根就没想重建,或者建造其他精细的供水系统。 到了14世纪中期,腺鼠疫抵达欧洲。基督教欧洲的领袖们和世界任何地方的领袖一样,面对自己无法理解的威胁,他们把责任推给自己*喜欢提及的替罪羊——用水清洁。1348年,巴黎大学的医生们特地谴责了热水澡,他们宣称用水洗澡会打开皮肤毛孔,使疾病进入体内。国王亨利三世的外科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附和道:“蒸汽浴和澡堂子都应禁止,人在洗浴的时候,体表的肉和整个身体都会变软,毛孔张开,有毒的水蒸气便会迅速进入人体内并引发猝死。”他在1568年写下这些话。在整个欧洲大陆,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浴室均被关闭。 既然中世纪的欧洲人对水的日常功用和道德意义都有所猜忌,他们便尽可能少地处理自己的排泄物,并减少喝水的欲求。他们的饮用水直接取自窄浅的井、泥泞的泉和浑浊的河,若水尝起来不太对劲,他们就干脆用啤酒代替原本就很少摄入的水。那些有条件的人则会选择“干洗”。17世纪的欧洲贵族用香水掩盖自己肮脏的身体所散发的臭味,还用天鹅绒、丝绸和亚麻包裹自己。17世纪的一位巴黎建筑师声称:“比起古代人的洗浴和蒸气浴,亚麻织品能更方便地保持身体清洁。”他们会用镶有红宝石的金耳勺从耳中挖耵聍,用镶有花边的黑色丝绸擦拭牙齿,以此避免用水清洗自己。“水是我们的敌人,”卫生史学家凯瑟琳·阿申博格写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接触。” 这种避免接触带来的后果是几百年之中人类与动物粪便密切接触,工业化时代之前的人类完全习惯于这一情况,甚至视之为有益的状态。中世纪欧洲人常年生活在脚下的各种粪便散发的臭味之中,自己排出的还只占少数。他们与充当食物或交通工具的家畜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牛、马和猪排出的粪便要比人类多得多,但人们对在何处储存这些粪便显得更不上心。 至于处理自己的粪便,一些人就直接坐在房间或是屋外厕所里的简易便桶上解决,他们管这叫“茅房”。稍微复杂一点的方法包括在室外或地窖中手工挖坑,有时还会用石头或砖块松散地衬砌(就像建污水池和私人金库那样),可能再安上无底座位或蹲板。如何收集和处理排泄物取决于每家住户的想法,当局几乎未做规定。排泄行为本身在当时并不像现在这般隐秘和羞耻。16和17世纪的君主,比如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会在上朝时公开“放任自流”。 中世纪欧洲人非但没能揭开人类粪便的真相,反而开始思考它的药用功效。记者罗斯·乔治在他所著的卫生史中写道,16世纪的德国修士马丁·路德每天会进食一茶匙自己的粪便。18世纪的法国宫廷侍从们则琢磨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子,他们会吸食“粪粉”,把自己的粪便晒干磨成粉,再凑到鼻子旁吸入。(这样做危险吗?很有可能。但相较于像腺鼠疫那样更迫在眉睫的威胁,这种吸食造成的零星腹泻病例尚没能引起人们的警觉。) 1625年,当荷兰殖民者们在曼哈顿岛南端建立起一个叫作新阿姆斯特丹的小镇时,把这些中世纪思想和卫生方法也带了过去。荷兰人直接就在地面上建造开放式的茅厕,还把他们的排泄物直接倒在大街上,这样“猪就可以拱食,在上面撒欢打滚”,新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官员在1658年这样写道。英国人于1658年控制了这块殖民地,并重新命名为“新约克(纽约)”,他们同样把排泄物储存在所谓“露天粪池”中,也会直接倒在街上。 中世纪的这些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哪怕原本几千来人的小镇已经成了拥有几万居民的小城市。到1820年,茅厕和粪池占据了全城十二分之一的面积,成千上万头猪、牛、马、流浪猫狗在街头晃荡,任意排便。1859年,一位官员抱怨道,纽约的户外厕所与茅厕“污秽不堪,条件恶劣,液体积滞,腐烂物质满溢,流出的污水让人无法忍受”。这些未经处理的污水就这样在公寓的背面和人行道上腐烂数周甚至数月。房东会在地面铺上木板来遮盖这些污物。城市巡视员汇报说,一旦有人踩压这些木板,下面就会挤出一股“浓浓的绿色液体”。 市政府偶尔会雇用私人团队收集充斥街头的动物和人类粪便,然后当作肥料变卖,这一举动令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一跃成为18世纪中叶美国*具生产力的农业县。人们管这种肥料浇灌叫“污水农耕”,这种方式并未持续发展,因为人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隔绝的地方来储存亟待运走的粪便。残留在码头的恶臭堆积物招来了附近居民的抱怨,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恩惠,市政机构倾向于把这种活儿交给私营承包商,这些承包商接了活儿却不干事。 如此,大多数的城市排泄物就这么沿着大街渗透,甚至浸入地里。这些污秽被压缩成“沿着人行道边缘的路堤长脊”,19世纪40年代末的一位报纸编辑阿萨·格林尼这样写道。行人和马就在粪便上践踏,慢慢把它们踩成了稠密的毯状。格林尼在日记里记道,在这层覆盖了整条街道的深厚“淤泥”之下,原本的街道石板“几乎再也看不到了”。极少情况下,城市会把街道清扫干净,当地人看到干净的街道反而会吓一大跳。一位一辈子住在城里的老妇看到新近清扫的街道,发出惊讶的评论,格林尼引用了她的话:“这些石板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原来街道是铺了石板的。真是荒诞啊!” 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市镇依旧沿用中世纪的卫生措施,结果创造出非常适合霍乱疫情暴发的条件。这些地方与欧洲乡村完全不同,后者已经形成了处理排泄物的习惯。在中世纪欧洲人生活的偏远居住点,土层较厚,人口密度低。当他们的粪坑要达到容量极限的时候,可以直接掩埋旧坑,再在旁边挖个新坑;他们把便盆直接倾倒在街道上,但街上本来就没什么人流;排泄物可能会渗入地下,但土壤中各种各样的矿物质、有机物和微生物会捕获并过滤这些污物,使其在进入地下水之前就被轻易分解。 曼哈顿岛上的情况则很不一样,其储存和过滤垃圾的能力十分有限。曼哈顿是一系列岛屿中*大的一座,这些岛屿散落在哈德孙河口,还包括史丹顿岛、总督岛、自由岛、艾利斯岛、罗斯福岛、沃德岛和兰德尔岛。两条微咸的河流从曼哈顿岛两侧流过——西边的是哈德孙河,东边的是伊斯特河;大西洋的潮汐也会拍打岛岸。两条河流正好在曼哈顿岛南端相遇,搅起水底的沉积物,向水层输送营养物质。河口的牡蛎长得很大,一般要切成三块才能食用。(今天,你在下曼哈顿的任何地方往下挖,只要挖得够深,就能发现空牡蛎壳,都是早期的牡蛎盛宴留下的。)尽管本地水域富含水生动植物,但早期的荷兰农民失望地发现,曼哈顿岛的土壤只有三英尺深。这样的土壤是留存不了多久的。在这一层浅浅的土壤之下,是由片岩和福德姆片麻岩构成的断裂基岩。纽约人后来意识到,这种基岩确实能承受住高楼大厦的重量,但也让地下水很轻易也很危险地暴露在排泄物中,因为排泄物被随意堆在地下水上面没多远的地方。新产生的人类粪便渗入薄薄的土层,直抵基岩。岩石的细小裂缝变成了地下“高速公路”,粪液能沿着这些细缝深入好几百码。 这些地理特征使得城市的饮用水补给特别容易被污染。曼哈顿的用水原本就很紧张:包围曼哈顿岛的哈德孙河和伊斯特河的河水太咸,无法饮用;收集雨水作为饮用水也被证明有危险,等雨水滴到居民肮脏的屋顶时已经沾满了灰霾和烟尘,“看起来跟墨水一样黑了,闻到那个味儿你肯定不愿喝”,一个当地居民提到。(早在1664年,饮用水源稀缺就被认为是定居曼哈顿岛的一个严重弊端。*后一位荷兰总督彼得·斯图维森特就抱怨说:“这里连一个水井和水箱都没有。”)岛上唯一一个方便取用的饮用水源是约70英尺深的积水塘,这是一个在后退的冰川上凿出的水壶形小池子。然而,随着城市人口逐渐向北扩张,制革厂和屠宰场之类的有害产业被推到了积水塘边。很快这个小池子就变得“又脏又臭”,在《纽约新闻报》上,一位居民在写给所有市民的公开信里这样抱怨。1791年,市政府购置下积水塘的所有权,卫生官员们呼吁将其完全排干。工人们开凿运河和沟渠,将补给积水塘的各个泉水排干。1803年,纽约市下令对排干了的池塘进行填埋,奖励每个往里倾倒整整一车物品(其实就是垃圾)的纽约人五美分。 在这之后,纽约人只能取用地下水(这些水是从地表渗入地底的),他们在街角挖建了公共水井。井挖得很浅,这很危险。现今的标准是要求井的套管至少有50英尺长,而且要在套管下方再钻一些距离,以抵达未受污染的地下水。19世纪,曼哈顿的水井只有约30英尺深。其中一口井就坐落在纽约*臭名昭著的贫民区五分区的茅厕和粪池之间,这口井通过曼哈顿公司建造的木制管道系统每日向全市三分之一的居民供应70万加仑的地下水。 纽约人其实知道他们的饮用水受到了污染。1830年,一份本地报纸刊载了这样一封来信: 我毫不怀疑,城里许多人胃疼的一个原因就是不纯净乃至有毒的曼哈顿恶劣水源,数以千计的居民每天都频繁使用不干净的水。大家都清楚这种令人厌恶的液体很难入口,所以基本不把它当作日用饮品,但你们要知道,我们社区饮食里的极大一部分都须通过这一可怕的液体作为介质制成。我们的茶和咖啡由水制成,我们的面包里也混合着水,我们的肉和蔬菜是放在水里煮熟的。还好我们的亚麻织品逃过一劫,“没有两种东西”比肥皂与这污糟的水“更不相容”。 “在夏天的周日喝下一杯这样的东西,你受得了吗?”1796年,一家当地报纸这样抱怨道,“等不到周一早晨,你就会开始恶心想吐;城市扩张得越大,这种恶果就越严重。”一位当地医生则留意到,城里的井水一般都会引起人们腹泻,或许可以治疗便秘,这些污水是“来自附近洗涤池(粪水池)的良药”,“其中的某些盐类成分,对某些症状来说是极为有效的”。 1831年,纽约科学院(当时还是自然历史学院)的科学家发现,上游州县的河水每加仑中含有的有机和无机物质少于130毫克,而纽约市的井水几乎是半固态的,每加仑含有超过8000毫克的渣滓。就连曼哈顿公司的一名前任主管在1810年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水里富含饮用者“自己的排泄物,还有马、牛、狗、猫的排泄物,以及其他各种腐化的液体,满满当当”。 当然,纽约人并不知道被污染的水是会传播致命疾病的。但他们清楚水有股怪味,所以不会直接饮用。他们把水加工制作成啤酒,或是在水里加入酒,比如杜松子酒,又或将水煮沸来泡咖啡和茶。这些措施不仅让水更易下咽,也摧毁了其中的粪便微生物,甚至可以杀死霍乱弧菌。20%酒精度的杜松子酒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杀死霍乱弧菌,热饮也可以做到。 不幸的是,纽约人面对的不只是被粪便污染的地下水,地表水也被污染了:拍打堤岸的河水灌入岛内,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形成水坑,甚至灌入人们的地窖。
作者简介
索尼娅·沙阿(Sonia Shah) 生于1969年,美国当代著名记者、科普作家,作品发表于《科学美国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著有《热症:疟疾统治人类五十万年的奥秘》(获得英国皇家学会温顿奖提名)、《人体猎人:在世界上*穷困病人身上进行的新药试验》以及《原油》等。 沙阿在TED所做的关于疟疾的演讲在全球播放超过100万次。她曾受邀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发表演讲,向公众普及科学常识。
-

那颗星星不在星图上-寻找太阳系的疆界
¥8.8¥29.0 -

鸟与兽的通俗生活
¥12.9¥39.8 -

宇宙已知和未知的一切
¥33.5¥48.0 -

物理学家的智性冒险
¥16.8¥56.0 -

我的世界观
¥10.4¥36.0 -

现在有多长
¥17.3¥48.0 -

物种起源
¥10.0¥36.0 -

科学全知道-那些古怪有趣的科学现象
¥15.4¥45.0 -

看花是种世界观
¥16.7¥58.0 -

你一定要懂的化学知识
¥9.4¥28.0 -

走进奇妙的元素周期表(八品)
¥15.4¥45.0 -

趣味代数学
¥14.4¥42.0 -

矿物与岩石图鉴(231种矿物与65种岩石鉴别指南)/含章图鉴系列
¥16.7¥45.0 -

你一定爱读的古怪科学
¥22.4¥49.8 -

新书--老鼠博物学
¥14.0¥36.0 -
![生命是什么/[奥]埃尔温·薛定谔](/Content/images/nopic.jpg)
生命是什么/[奥]埃尔温·薛定谔
¥16.9¥39.8 -

猫咪海洋简史
¥22.1¥49.0 -

时间简史(插图版)
¥17.6¥45.0 -

半小时漫画中国地理
¥25.0¥49.9 -

懒惰脑科学
¥15.4¥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