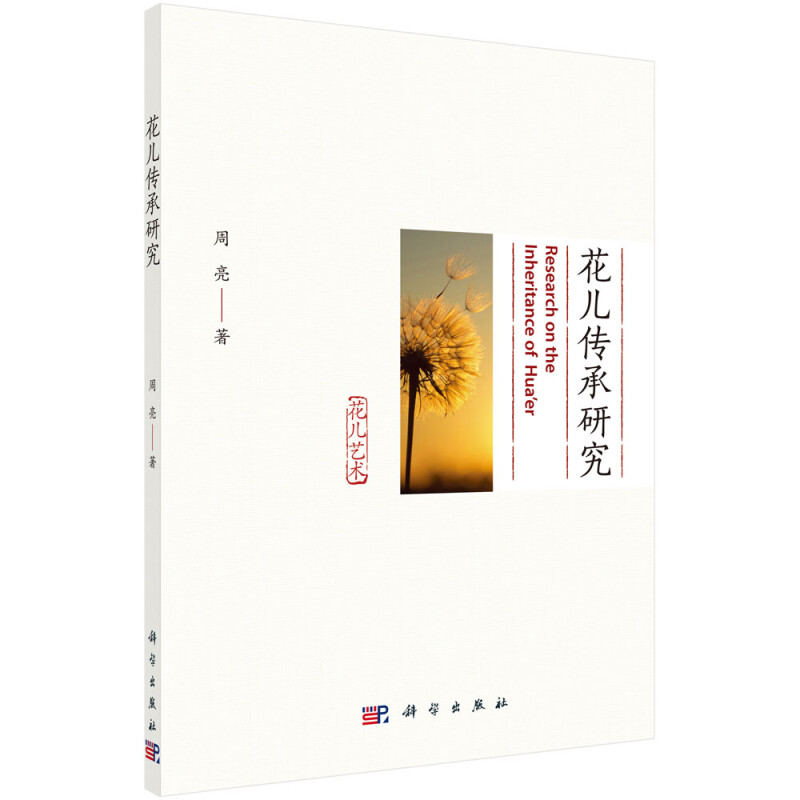- ISBN:9787030706997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192
- 出版时间:2021-12-01
- 条形码:9787030706997 ; 978-7-03-070699-7
本书特色
本书适合传统文化保护研究者、决策者及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者参阅。
内容简介
21世纪以来,如何保护、传承像花儿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持续的文化创新与社会进步,以发挥其凝聚力,成为当代人必须深思的重大课题。 本书采取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切入方向,将研究重心从花儿传承的音乐属性转向社会属性,由此发现支撑花儿这一口口相传文化的核心是“群体”,即群体的存在状态决定传承的兴与衰。基于此,本书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从群体的形成和维系、群体的性质和作用、群体的解体和传承危机、群体重构的条件和契机、传承的复活和未来方向等诸多方面,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途径。 本书适合传统文化保护研究者、决策者及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者参阅。
目录
前言
**章 花儿传承的原生环境 1
**节 传承区域人口稳定 3
第二节 村落共同体的出现 14
第三节 民歌文化流传广泛 23
第二章 花儿传承的驱动主体 33
**节 稳固的花儿群体 35
第二节 活态的创作传唱 47
第三节 自觉的世代相承 57
第三章 花儿传承的历史危机 63
**节 乡土社会的变迁 65
第二节 花儿传唱群体的解构 75
第三节 活态传承的中断 82
第四章 花儿传承危机的文化后果 89
**节 文化诉求的改变 91
第二节 文化传统的改变 103
第三节 文化功能的流失 115
第五章 花儿传承危机的化解途径 125
**节 花儿群体重构的意义 127
第二节 花儿群体重构的条件 137
第三节 花儿群体重构的时机 149
参考文献 159
附录:1979~2021年花儿相关论著分类整理 175
后记 191
节选
**章 花儿传承的原生环境 任何民间艺术的传承都离不开特定的条件,作为起源于河湟的口传文化花儿,离不开稳定的人群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背景。 河湟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会地带,地理结构造成内部区块的相对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离开土地便没有其他出路,只能祖祖辈辈守护在土地上。传统农耕生产的脆弱性迫使农民“抱团取暖”,通过聚居生活的方式抵御各种风险,由此形成原始的自然村落,并逐步发展为内部结构更为紧密的村落共同体。村落共同体作为独立的农村基础组织,在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会有效地将内部成员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每个成员来说,共同体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历世不移的结果是形成一个熟人社会,或者说变成一个不流动的社会。在传统乡土社会里,识文断字的农民数量极少,在文化种类的选择上除了口传文化很难有别的选择,因此在河湟民众中达成了一种默契,文字表达不了的用言语,言语表达不清的用歌唱,歌唱有了把文字和言语融合在一起的功能,在世代继承中成为河湟民众的文化传统。 缺少流动性的村落群体和世代相传的歌唱传统,共同构筑了花儿传承的外部条件。 **节 传承区域人口稳定 口传文化的传承需要人的支撑,没有一定数量的稳定人群作为基础,传承过程始终如履薄冰。河湟作为口传文化花儿的发源地和传承地,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造成人口流动近于停滞,由此形成稳定的人口状态。 一、地理和经济形式特点 河湟地形特点是山川谷地相间,每一块适合农耕的谷地都形成相对独立的空间,这对人口的自然流动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障碍。河湟社会经济在历史演进中经过多种经济方式的博弈,*终进入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村落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不仅有助于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平稳,而且客观上维护了农业人口的稳定。 (一)河湟的自然地理条件 “河湟”是指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作为地域概念的出现,早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就有“乃渡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后又被称为“河湟谷地”或“河湟地区”。 对于河湟所包含的地域范围,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界定,但大体划定在青海和甘肃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谷地和其支流湟水谷地。具体地讲,青海东部(日月山以东)和甘肃西部(包括今天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全境及兰州市部分地区),在地形上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 河湟地区从地理位势上看属于山地高原区,处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边缘和交会地带,境内地貌以中低山、丘陵、谷地为主,地形复杂多样,海拔为1650~4630米。地势呈西南高、东北低的倾斜盆地状态,境内山峦绵延起伏,黄河、大通河、湟水贯穿其间,根据地势的变化及海拔的不同,形成川、浅、脑立体阶地。 河谷地区地势较为平缓,谷地年平均气温为6~9℃,水源丰沛,适宜农耕。河谷以上的浅山地区土质疏松干燥,只宜种植高寒作物。浅山地区以上则为高山地区,海拔的抬升造成气温下降,从而湿润多雨,故植被以低矮的草木为主,适宜畜牧业生产。 河湟地区从宏观上看呈现开放状态,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中原与中国西部的枢纽,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和甘川古道在这里交会延伸。河湟地区从微观上由于受到河谷横切面宽度的限制和周边山地的包围,*终只能被切割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型盆地,难以连片开发集约利用。每一个今天能够成为县市级行政中心所在地的河谷,都可以被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点,这种地理结构造成河湟地区内部区块的相对封闭性。 (二)经济形态的历史演进 河湟地区的经济形态经历了原始农耕经济、游牧经济、农牧混合型经济、农业经济等阶段,早期的农业经济是伴随着人口迁徙发展的,具有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缺少相应的社会基础组织作为支撑,呈现出不完全性和脆弱性,直至明代才形成较为成熟的农业经济,河湟也由此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会。 根据考古资料的记载,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时期,河湟已进入原始农耕经济社会,从各遗址发现的大量生产工具和动物遗骸可以证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很发达。由于气候和人口的原因,在距今3600~2600年的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时期,农耕经济逐渐衰落。到了卡约文化晚期,游牧经济已经完全取代了农耕经济,河湟地区的人脱离了农业定居生活,进入了逐水草而居的移动生活。河湟从此成为游牧部落之间的角逐之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古羌人成为这块土地的主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是河湟农业大开发、大发展的**个鼎盛时期,由西汉开始的河湟农业开发有着强大的内在动力,关系中央集权体系的确立和疆土的开拓。汉武帝时期开土拓疆、西逐诸羌,将河湟纳入汉帝国的版图,为了巩固新拓疆土,在河湟地区实行屯田和移民实边政策。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向河湟移民并开置公田,始为民屯;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统兵进入河湟平定羌乱后,“罢兵屯田”,始为军屯。东汉时期一直没有停止过向河湟地区移民实边,屯田区域由湟水两岸进一步扩大到黄河两岸,大量内地汉族人口进入河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施行了农业水利工程,推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河湟羌人在先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并在与汉族的交流中不断地改变身份,其中一部分人融入了汉族。可以说,两汉以来大力推行的屯田实边政策,对河湟地区的农业开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移民实边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大批汉族人口在河湟安家立业,不仅奠定了农业经济的基础,而且构建出了农业社会的雏形。 东晋十六国时期,河湟地区先后被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秦、北凉所统治,行政建置屡有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人口流失严重,农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全盛时期的开元盛世,河湟的农业经济得到恢复,但随着“安史之乱”后吐蕃对河湟的占领,强制推行“蕃化”政策,农业经济又遭到极大破坏。自吐蕃之后,河湟又经过多次政权更迭,农业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全面恢复。 在河湟农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明代是一个关键时期。明王朝初定河湟后,鉴于河湟地区东接秦陇、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护甘凉的战略位置,将其作为重点经营地区之一。明政府在河湟境内设置卫所大量屯兵,加强军事防御力量,保障政权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为了“养兵而不病农”,达到“强兵足食”的目的,采取兵农兼资、耕战结合的策略,大力推行屯田制度,使移民屯田成为一项基本国策。明朝屯田规模之大,历时之久,都是前朝所没有的。屯田制引发了移民大潮,中原和江淮一带的汉族人口大量迁入河湟地区。据史料记载,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政府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移民活动不仅带动了河湟农业的发展,而且改变了河湟的人口结构,开创并巩固了农业生产在河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相应的农耕社会组织,河湟真正进入了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社会,花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三)平稳延续的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条件下,乡村社会处于一种稳定和均衡状态,这是由小农经济的基本特性造成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农民的生产通常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即所谓的男耕女织,以满足自己衣食的基本生活需要,具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由于生产限于家庭劳动力的范围,所耕种的土地面积也因此受到限制,“又由于它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 ,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可以存在和再生产,所以小农经济具有稳固性的属性。小农经济从表面上看是脆弱的,从自然因素来说,小农经济抵御灾害的能力很弱,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从社会因素来说,战争和内乱造成农民流离失所,正常的生产活动也就无法维持。“小农经济虽然是脆弱的,但却又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只要具备简单的生产条件,很快就可以恢复生产。” 中国历史上一些畜牧经济的民族,如匈奴、突厥等,常常经过一场大的灾荒或战争之后,便一蹶不振很难恢复元气,甚至很快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而农业地区的小农经济,却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衰败后很快恢复起来。 小农经济的这种再生能力不仅体现了一种坚韧性,从长期角度看仍然表现为稳定性。 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带来了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的稳定,社会变迁发生的频率低而且速度缓慢。任何社会都不是静止的,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与原有秩序的冲突,但在小农经济社会中这种社会发展变化相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是很缓慢的,仅仅通过生命周期性就能够适应秩序的演变,并不会明显感受到秩序的变迁。对于农民来说,稳定的生活状态是*重要的,这也是小农经济熏染的结果。河湟位于地理上的高山地区,农业生产一半靠自然、一半靠人力,一旦遇上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就会遭到致命打击,农民对此几乎毫无抵御能力,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灾害肆虐,等待下一个好年成的到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乐天知命的性格。在被自然存在所左右的环境中,农民的生活节奏顺应着农业生产周期,春忙冬闲周而复始。他们祖祖辈辈做着同一件工作,甚至走着同一条路,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以求获得一种平稳的生活,固守于土地,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安宁稳定便是他们追求的生活样式。长期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让农民习惯于安于天命,这种观念延伸到社会生活中便转换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顺从意识。另外,重农抑商政策下所形成的正统文化对农民长期侵染,像紧箍咒一般束缚着他们的观念,使得他们思想僵化,缺乏进取和开拓精神,安于在狭隘的农业简单再生产里转圈子。
作者简介
周亮,汉族,兰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硕士,兰州大学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民族学博士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学博士后,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音乐系访问学者,英国诺丁汉大学音乐系访问学者。主持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的11项课题,出版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10篇,“花儿艺术: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众智慧与独特精神”一文(《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被《新华文摘》2016年9期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16年1期全文转载。个人获省级及以上专业比赛奖励28项,指导学生获省级及以上专业比赛奖励53项。创建并主讲的“花儿”课程获选重量“精品视频公开课”和甘肃省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主持完成的“教学、创演、研究一体化:'花儿'通过高校音乐教育传承的探索与实践”项目获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7年)。被评为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9年)。先后获兰州大学“隆基教学”新秀奖和“隆基教学”骨干奖。
-

古典名著聚珍文库:山海经
¥5.3¥15.0 -

中国文化常识:二十四节气与节日
¥21.1¥49.0 -

经典常谈
¥4.3¥14.8 -

我的童年在台湾
¥12.8¥32.0 -

吾国与吾民-精装典藏新善本
¥13.4¥28.0 -

蔷薇花与十字架
¥14.4¥45.0 -

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16.6¥52.0 -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模样:走进民国大学图书馆
¥14.4¥39.0 -

先民的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经验
¥10.4¥28.0 -

中国馔馐谭
¥11.0¥23.0 -

茶经(黑白版)
¥10.1¥48.0 -

我所不理解的生活-纪念珍藏版
¥11.0¥29.8 -

刘荫柏讲西游(九品)
¥19.7¥58.0 -

敬你一杯烈酒(八品)
¥11.7¥45.0 -

风诗的情韵:李山讲《诗经》
¥17.0¥46.0 -

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
¥11.2¥28.0 -

地理的故事
¥15.0¥47.0 -

解密富春山居图-国宝背后的秘密
¥5.5¥22.0 -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9.8¥25.0 -

中国古代官制
¥9.3¥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