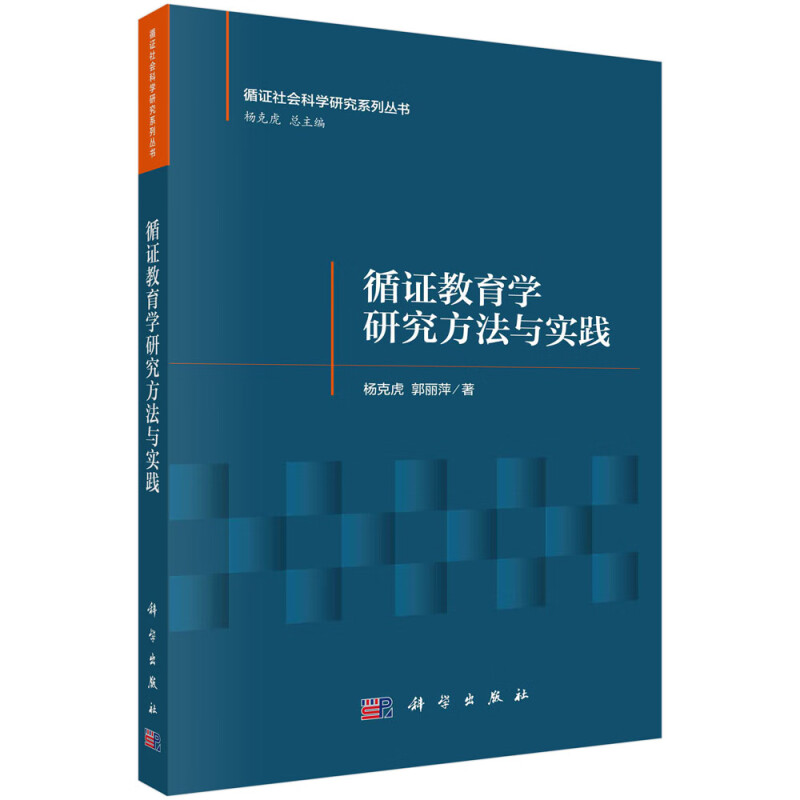- ISBN:9787030744074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B5
- 页数:288
- 出版时间:2023-03-01
- 条形码:9787030744074 ; 978-7-03-074407-4
内容简介
循证教育学是一门将循证的理念与方法运用于教育教学中的学科,其致力于研究教育决策者如何在教育过程中将专业智慧与很好、有效的经验证据整合起来进行决策,以期实现因材施教和科学教学。全书共分为三篇,分别是循证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篇、循证教育学的研究方法篇和循证教育学的案例解读篇。本书由浅入深、简明扼要地就有关循证教育学研究方法的相关主题进行了系统、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能使读者较快地理解和掌握该方法,为读者理解循证教育学的基本思想及如何正确地应用、解释循证教育学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可供教育相关的研究者和教师阅读和参考。
目录
上篇 循证教育学研究方法
**章 循证教育学的基本认识 3
**节 循证教育学的起源 3
第二节 循证教育学的内涵 6
第三节 循证教育学的发展 9
第四节 证据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机构/平台 13
第二章 循证教育学研究方法概述 20
**节 系统评价概述 20
第二节 为什么要进行系统评价 23
第三节 系统评价的易陷误区 24
第四节 系统评价的方法进展 28
第三章 定性系统评价的制作流程 37
**节 确定研究问题 37
第二节 制订研究计划 39
第三节 检索资料 42
第四节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52
第五节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54
第六节 资料分析和结果综合 57
第四章 定量系统评价的制作流程 62
**节 确定研究问题 62
第二节 文献检索、筛选和资料提取 62
第三节 文献质量评估 64
第四节 效应量的选择和合并 71
第五节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78
第六节 异质性分析 82
第七节 发表偏倚 84
第八节 敏感性分析 89
第五章 其他类型系统评价的制作流程 92
**节 系统评价再评价 92
第二节 网状Meta分析 96
第三节 证据差距图 99
第四节 Campbell系统评价 103
第六章 系统评价的质量评价与报告规范 109
**节 系统评价的质量评价 109
第二节 系统评价的报告规范 118
第七章 系统评价常用软件 140
**节 文献管理软件 140
第二节 常用统计软件 152
下篇 循证教育学研究实践
第八章 定量系统评价案例解析 189
**节 基于均值效应量的系统评价 189
第二节 基于二分类数据效应量的系统评价 200
第三节 基于相关系数效应量的系统评价 206
第九章 定性系统评价案例解析 214
**节 主题综合法 214
第二节 Meta民族志 224
第三节 批判性解释综合 233
第十章 其他类型系统评价案例解析 241
**节 系统评价再评价 241
第二节 网状Meta分析 247
第三节 证据差距图 258
附录1 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参考书籍 270
附录2 Campbell教育组系统评价一览表 273
节选
**章循证教育学的基本认识 **节循证教育学的起源 一、从医学“科学化”到循证医学 物理学、化学等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后,成功地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医学领域研究者也效仿成熟的自然科学开始进行医学“科学化”,他们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实证研究,以观察、调查、测量、实验等实证方法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据宋代《本草图经》记载,早在1061年,我国古人就开展了朴素的对照试验以鉴别人参的作用;1753年,苏格兰海军外科医生詹姆斯 林德(James Lind)首次采用对照临床试验进行了柠檬或橙子治疗坏血病症状的研究。自此,医学逐渐从经验观察、理论思辨的方式,转变为以使用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回归分析、判别分析等实验方法为主的研究方式。然而,1972年,英国的内科医师阿奇 科克伦(Archie Cochrane)出版的《疗效和效益:健康服务中的随机反应》(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Random Reflections on Health Semces)—书指出,先前被认为是有效的实践大多缺乏对照试验来支持其有效性。次年,约翰 温伯格(John Wennberg)发现即使针对同一种疾病的治疗,医生的执业方式也存在巨大差异。同期,戴维 埃迪(David Eddy)也发现了临床决策中的错误和证据的空白。 20世纪70~90年代,西方国家医疗卫生的投人持续加大,但国民的健康状况并未得到很大改善。政府官员与民众将矛头指向医生,认为医生的不作为导致了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一方面,医生准人门槛较高的、相对具有封闭性的专业知识体系,使他们拥有超越患者及监管机构的权力。他们可能通过提供不必要的服务,从患者或保险公司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医生可能因为疏懒或知识陈旧,而未采用当前*好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使患者与国家遭受损失。[1]为了加强对医生临床决策的监管,1983年美国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HMO)推出了按病种付费系统(Diagnosis-related Group,DRG)。该系统根据国际疾病分类诊断(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程序,以及患者的年龄、性别、出院状态及并发症的评估进行分组,并以此来确定医疗保险向医院支付的费用。DRG严格地监管医疗进程,要求治疗组尽量使用现有的、*佳的治疗方式,保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治疗疾病。 1990年3月,戴维 埃迪在《实践政策出自何处》(.Pmcticepolices:where do they come/rom)—文中首次提出“循证”一词,并指出“医疗决策要以证据为基础,且要对相关证据进行甄别、描述和分析”。同年,Gordon Guyatt在戴维 萨基特(David Sackett)的指导下,将经过严格评价后的文献知识用于帮助住院医生做出临床决策,产生了有别于传统临床决策模式的新模式,即“循证医学”。循证医学认为:**,要降低医疗费用,就要促使医生放弃提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转而采取*佳的治疗方案;第二,要保证医生采取*佳的治疗方案,就必须要求医生严格遵循现有的“*佳的科学研究证据”进行治疗;第三,要判定科学研究证据是否为“*佳”,就必须将所有的证据,按其方法的严谨程度及结局的好坏程度来进行分级。一般说来,在有证据表明结局相同的情况下,采取的研究方法越严谨,其证据的级别就越高。在当前所有证据中,级别*高的证据就是“*佳”证据,医生就应该采取这种证据所支持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因此,循证医学实际上就是要求医生遵循当前*高级别的研究证据进行治疗,以保证患者获得*佳的治疗效果,从而减少医疗费用与资源浪费。循证医学为医生的临床决策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治疗理论与可操作的实践框架:研究者提供证据;具有良好临床技能的医生运用证据;患者也可以基于证据参与治疗决策,选择自己喜欢的治疗方案,主动地参与到治疗的过程中。循证医学将医学的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分离开来,根据严格的临床研究证据建立治疗指南或医学数据库,要求医生遵循*佳的证据进行治疗。这既保证了医学理论研究的权威,也保证了实践的效果,为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的实践框架。 二、从教育学“科学化”到循证教育学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是欧美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随着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欧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疆界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在教育领域,知识的快速增长打破了学校对知识的垄断地位,学校已不再是唯一获取知识的地方,同时学校教育改革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心。同时,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引发了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欧美学者也对科学的作用、科学研究与教育研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认识。例如,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爱德华 李 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在谈到科学与教育科学的关系时指出:“教育科学,当它在发展的时候,就像其他科学那样,有赖于对教育机构的影响做直接观察和实验,并且有赖于定量的精确性研究和描述的方法。”美国教育家约翰 杜威(John Dewey)认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就是试验的方法,就是将人的行为与人的思考和自然界的事实联系起来,通过解决问题来获得新的知识。科学研究的特点是无论是对新的观点还是对旧的观点,都不是一概推翻,也不认为是*后的真理,只是以试验的态度研究其存在的理由,它可以使研究充满试验气氛,打破垄断和教条的东西。杜威的“问题解决五步法”就是其教育研究理念的具体运用。它包括:设置一个真实的经验的情境,在情境中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收集知识资料应对这个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假设,通过应用检验假设。这一时期,许多欧美学者都坚信,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可靠的基础,教育研究的发展需要依靠科学,依据事实。同时,科学也需要并能够为教育与社会进步服务。[6] 1879年,威廉 冯特(Wilhelm Wundt)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的心理学实验室,将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心理科学”。受冯特的影响,教育研究者在定性、思辨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引人调查法、量表法甚至是实验法等量化研究方法,形成了所谓的“实证教育学”或“实验教育学”,并创建了教育实验室或者心理实验室、实验学校及教育研究学会,这些机构的建立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转变。随后,一些教育研究者在已有认识和建立实验机构的基础上,对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进行实验研究和验证。例如,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非常强调教育测量,被称为“测量运动之父”,他试图对与教育相关的事物都进行精确的数字测量,包括智力、行为变化甚至教育目的。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 比奈(Alfred Binet)重视对儿童的智力测验。经过多年研究,他和西奥多 西蒙(Theodore Simon)提出了运用智力量表进行测验的设想,试图判别正常儿童和智力缺陷儿童的智力状况。这些研究都对当时的儿童研究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推动了欧美教育科学化运动的发展。 1996年,剑桥大学教授戴维 哈格里夫斯在教育培训机构年度讲座中进行了“教学作为一个以研究为基础的职业:可能性和前景”的演讲。他提到,尽管英国政府每年在教育研究上投人5000万至6000万英镑,但其研究对实践的改善几乎没有影响,教师也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益处,教学仍然还不是一种基于研究的工作。同时,他也指出了教师主要从哪几个方面为自己辩护:传统(一直以来的做法)、偏见(我喜欢这样做)、教条(这是做这件事的“正确”方法)和意识形态(按照当前正统的要求)。[7]不难发现,这些理由与医生曾经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相似。除此之外,哈格里夫斯还发现教师与医生的决策有很多相同之处。一方面教师和医生的决策对象都是人,另一方面教育学如医学一样出现了严重的理论与实践分裂的问题。然而不同的是,循证医学兴起后,很多医生在决策时会遵循严格的科学证据,而教师仍然更多依赖于个人经验。[8]因此,受循证医学的启示,他提出了循证教育学的概念,认为教育学也应该像医学一样,让实践严格地遵循研究证据。此后,这种理念影响了整个教育领域,得到了西方学界和官方的广泛认可。 第二节循证教育学的内涵 一、循证教育学的概念 循证教育学(Evidence-based Education,EBE)是一种实践原则,即教育实践应基于现有的*佳科学证据,而不是传统观念、个人判断或其他影响。自1996年剑桥大学戴维 哈格里夫斯教授在教育培训机构年度讲座上首次提出循证教育学的雏形后,国内外学者对循证教育学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凝练,其中美国教育研究与改进办公室的助理秘书怀特赫斯特的定义*为经典。 2001年,怀特赫斯特从两个层面界定了循证教育学的内涵。他认为,循证教育学是在教学过程中,将*有效的实验证据与专业智慧高效整合的一种决策。[w]他将循证教育学划分为两个模块四个核心(图1.1),即专业智慧(个人经验、共识)和实验证据(基于科学的研究成果、实验数据)。 “专业智慧”指个人通过经验获得的判断,增加的专业智慧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有效地识别证据并结合当地情况进行指导。“实验证据”是指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科学为基础的证据,特别是来自教育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与绩效相关的实验数据主要用于比较、评估和监控进展,而基于科学的研究成果是指运用严谨、系统和客观的方法来获得与教育活动及教育政策相关的可靠和有效的知识的研究,在使用前必须评估其质量和相关性。[11] (一)证据的质量 证据的质量指实验设计、分析和逻辑推理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所得的结
-

黄帝内经
¥41.2¥76.0 -

联袂药性赋白话解-国医精粹口袋书系
¥6.3¥18.0 -

外科急救常识图解
¥1.7¥4.0 -

彩绘版国学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精装)
¥24.3¥76.0 -

中草药实用大全
¥18.6¥58.0 -

齐氏医话医案集-(赠光盘)
¥21.6¥40.0 -

本草纲目
¥24.3¥76.0 -

汤头歌诀
¥15.4¥20.0 -

常见急救常识图解
¥1.7¥4.0 -

细胞叛变记-解开医学最深处的秘密
¥17.1¥45.0 -

活幼心书
¥5.7¥15.0 -

临床常用百药精解-国医精粹口袋书系
¥9.9¥32.0 -

格致余论
¥2.3¥6.0 -

脑血管病患者生活指导
¥2.6¥6.0 -

濒湖脉学
¥15.0¥20.0 -

中医珍本文库影印点校(珍藏版):外科方外奇方
¥8.8¥17.0 -

养生大系:名老中医偏方大全
¥18.6¥58.0 -

热锅上的家庭:家庭问题背后的心理真相
¥33.3¥68.0 -

国医大师贺普仁
¥12.5¥49.8 -

图解黄帝内经
¥48.4¥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