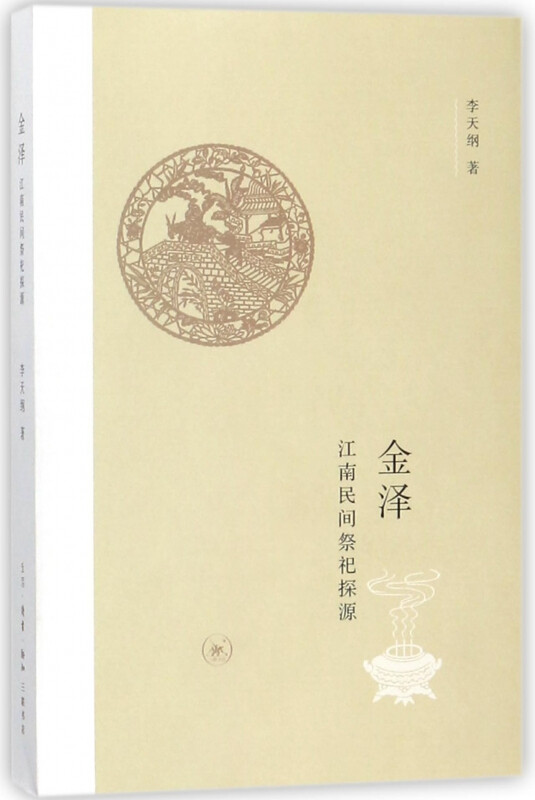
4.9分
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豆瓣8.3分推荐!本土学者探究中国民间宗教活动,不可多得的社科佳作!就其当代转型和改造进程进行了详细考察。

- ISBN:9787108059369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559
- 出版时间:2017-12-01
- 条形码:9787108059369 ; 978-7-108-05936-9
本书特色
《金泽》考察和描述了江南金泽镇民间祭祀现象,剖析了民间祭祀系统与儒教祭祀传统的内在联系,以全球化、现代性为背景,以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为参照,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发生、发展作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
内容简介
《金泽》是一部借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江南祭祀制度的专著。作者李天纲选取上海青浦金泽镇作为主要的研究个案,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调查,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府、州、县、乡、镇等地方志,探究了江南地区官方儒学经典、祭典和民间地方祭祀系统之间的密切关联。
《金泽》主要观察、关注和研究江南地区以祠祀为特征“民间宗教”的历史、发展和演化。作者经过细致的历时性考察,从中提炼出江南地区祭祀及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共性,并由此提出,“从儒教祠祀系统演变出来的民间宗教,才是中国现代宗教的信仰之源”。借此文献、田野和和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性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书中还考察了中国民间祭祀系统的当代转型和改造进程,探讨了转型和改造的趋向等问题。另外,在全书结尾处,作者简要总结了民间祭祀、神祇和信仰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路径等问题。
目录
民间宗教:渊源与反省
全球—地方化时代的信仰
世俗化与都市宗教
金泽古镇:现代的边缘,信仰的中心
江南、上海和世界
上篇 金泽的祭祀生活
**章 市镇祭祀:地方性知识
江南宗教
金泽的祠庙
市镇信仰:空间的发现
回归,抑或内部转换?
第二章 众教之渊:金泽镇诸神祠
东岳大帝:从朝廷到地方
杨震庙:江南草根信仰
刘王庙:蝗神、水神和文神
二王庙:礼失求诸野
五路神:秩祀,淫祀?
城隍神:城市型地方认同
关帝庙:官民共奉的信仰
第三章 祀典:民间宗教与儒教
周孔之教与孔孟之道
祀典与淫祀
洪武改制:汉人信仰的重建
官民合作模式
方志中的祠祀改革
第四章 私祀:民间宗教的秩序化
中国宗教体系
县、镇、乡宗教生活的秩序
中国神祇的分类学
下篇 江南祭祀之源
第五章 佛道兼容:合一的基层信仰
颐浩寺模式:现代性问题
三种佛教:士绅的力量
民众佛教:基层的活力
佛教复兴:都市化革命
第六章 三教通体:士大夫的态度
三教通体
“鬼神之为德”
三教一源
合于民间宗教
第七章 社、会:民间祭祀的结构
市场圈:“施坚雅模式”的修正
祭祀圈:市镇祭祀共同体
庙会与方域认同
香汛:庙会、性别与组织
第八章 汉人宗教的基本形式
汉人宗教的基本形式
魂魄:儒学本体论
鬼祟:民间祭祀之源
血食:祈、报及“祭如在”
焚香:人神沟通之具
设像:非儒教主张
总论 中国的宗教与宗教学
“中国根柢”:江南祭祀的底色
宗教普遍性:傩、巫觋、萨满教
儒家宗教性:中国有宗教
宗教对话:中西会通之具
都市化:宗教的基本与变革
新路径: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与主张
后记
参考书目
节选
江南、上海和世界选择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作为中国宗教研究的田野考察地点,是想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从文本到文本的研读和比较,固然能够抓住一些本质问题,但这样的结论是否和实际生活相关,就是另一回事情。“接地气”是近年来的一句流行语,虽很俗套,却有合理之处。如果一项研究画地为牢,并不试图说明实际生活,无论它有多么强大的理论意义,也不能算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经典研究与民俗考察,文本研读与田野调查,宗教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方法来推动宗教领域的研究,是立项时的初衷。但是,选择金泽镇作为田野调查基地,却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2005年的秋天,偶尔到了金泽镇,正逢“廿八香汛”,发现这里的气氛很是异样,别的地方消失了的宗教生活,这里保存较好。混杂的庙会形式有些可以从儒教、道教、佛教的经典去理解,有的则沾染了现代生活气息。还有,明清以来地方志中记载的神祇、祀典和科仪,在当代老、中、青年的信仰中交错。这样的“活标本”,不是正好可以拿来观察江南和中国的宗教么?从金泽,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及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水乡泽国的金泽镇,地处江南核心地带,这里历来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信仰体系;明代以后,这一地区的士绅、文人、商人、僧侣以及刚刚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经济、文化和信仰网络。这个网络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文化关系,学者们或许应该称之为“早期全球化”(Early Globalization)。在金泽镇,稍作分析,便可以辨别出本土(Local)—地方(Regional)—全国(National)—全球(Global)一共四层关系。江南古镇金泽经过近代上海的牵动,成为世界经济与文化的一部分。地方,不只是江南的,也属于全球。经过明清时期的通商、传教运动,“地方性”(Localities)的含义完全改变了。江南社会初与西方文明有交往,始于17世纪初年。葡萄牙商人进入马六甲海峡以后,中国的大宗商品输出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主,出产地均为江南。天主教耶稣会士用澳门做基地,深入内地,在上海、嘉定、杭州、南京建立以江南为核心的中国传教区。江南人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已经为天主教神父们广泛谈论,仔细研究。[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儒家天主教徒”与耶稣会士的神学对话,可见李天纲编:《明末天主教三柱石论教文笺注》(香港,道风书社,2007年);佛教僧侣与耶稣会士的对话,可见祩宏(云栖):《竹窗三笔 ? 天说》(收入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年);尚未发现道教人士和耶稣会士的对话,而天方教人士对耶稣会士神学理论的回应,可见王岱舆著:《正教真诠》《清真大学》等(西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清初在常熟传教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鲁日满(Franciscus Rougemont, 1624—1676),他的传教区在苏州府的常熟、昆山、太仓等县,常常去松江、上海、苏州和杭州出差。和江南士人一样,他的交通方式以乘船为主。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依靠瞿太素(常熟人)、徐光启(上海人)、李之藻(仁和人)、杨廷筠(仁和人)等开教“柱石”,建立了江南天主教会,就其教区分布范围来看,正好是以淀山湖为中心,把江苏、浙江和今天的上海联系在一起。江南教区的范围,大致以明、清帝国行政区的苏、松、太、常、杭、嘉、湖各州府为主,上海则是江南教区的中心。“上海传教区,它是整个江南省,也许是整个中国*为繁荣的传教区之一。当时有56座可以举行正式感恩祭的教堂,和大约40, 000个教友。”鲁日满神父从常熟来松江、青浦、上海,跨越范围就是以金泽镇为代表的江南地方宗教“信仰圈”。鲁日满有一部《常熟账本》,给我们留下珍贵的资料,说明17世纪的江南天主教教区与传统的民间信仰圈高度重合。例如,他在常熟,记录了清初的物产、物价和其他费用,也记下他去各地出差时的费用。常熟到苏州的路费是260文;常熟到太仓的路费0.40两;常熟到青浦的路费720文;常熟到上海的路费1150文;常熟到杭州的路费1.10两。这里的路费,都是客船运费。每次有所不同,但大致相当。天主教徒、上海巨绅徐光启在青浦朱家角以东的赵行、蟠龙镇经营事业,清初青浦的天主教会活跃。鲁日满来过青浦金泽镇,康熙十四年五月十四日(1675年6月7日)他在嘉兴给一位信徒施洗;二十四日(17日),在朱家角镇给另一位信徒施洗。从嘉兴到朱家角的水路途中,鲁日满必须经过江浙之门户——金泽镇。从鲁日满《常熟账本》看,常熟、昆山、太仓、嘉兴、杭州、青浦、松江、上海一带的天主教信仰圈,和江、浙、沪交界地带的淀山湖民间信仰圈重叠。如以金泽、朱家角镇为圆心,以50公里为半径,既划入杨震信仰,也包括天主教江南教区的大部分。松江府在宋、明以后的经济、文化地位日形重要,与苏州府并称,有“苏松熟,天下足”的民谚。明万历年间学者王士性(1547—1598,浙江临海人)指出:“苏、松赋重,其壤地不与嘉、湖殊也,而赋乃加其十之六。”清初学者顾炎武则有“苏松二府田赋之重”的详细论述。按顾炎武的查证,松江府田赋之“重”,又甚于苏州府。顾祖禹也对明代松江府的重要地位评价甚高,称其“雄襟大海,险扼三江。引闽越之梯航,控江淮之关键。盖风帆出入,瞬息千里,而钱塘灌输于南,长淮、扬子灌输于北,与淞江之口皆辐列海滨,互为形援。津途不越数百里间,而利害所关且半天下。……且居嘉、湖之肘腋,为吴郡之指臂。往者倭寇出没境内,而浙西数郡皆燎原是虞。谓郡僻处东南,惟以赋财渊薮称雄郡者,非笃论也”。青浦县的河湖港汊串通起整个太湖流域和长江沿岸;青浦东境的上海县则依托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与广东、福建、山东、河北各地联通。江南士人重视松江府为“赋财渊薮”,却仍然轻视它“僻处东南”。顾祖禹批驳了这种陈旧见解,他看到上海作为一个通商口岸,正崛起为全中国乃至东亚和世界的交通中心。吴淞江是贯穿松江府全境的主要河流,分为两条水路通往苏州府,一从昆山县境,一从吴江县境,金泽镇即是吴淞江从吴江进入苏州之孔道。“吴淞江,在(苏州)府南,从吴江县流入境,合于庞山湖,转而东入昆山县界。又娄江,在今城东娄门外,亦自吴江县流入,自城南复东北流至娄门外,东流入昆山县境。”吴淞江下游自上海入海,但它的上游并不确定。顾祖禹称:“自唐宋以来,三江之名益乱,东江既湮,而娄江上流亦不可问。土人习闻吴淞江之名,凡水势深阔者即谓之吴淞江。”吴淞江北支因接近长江,淤塞日重,和娄江一样慢慢不可通航,昆山一路渐渐不用。所以,经朱家角镇到金泽镇,再经淀山湖水域入苏州,复经太湖水域去无锡、常州。往下,还可以经练塘、枫泾等镇,进入嘉善、嘉兴等浙江省县份。淀山湖,是苏州和松江的界湖,“淀山湖,(昆山)县东南八十里,接松江府界,亦曰薛淀湖。东西三十六里,南北十八里,周回几二百里。下流注于吴淞江”。淀山湖周边有一连串繁荣的古镇。青浦县境的西部,先有青龙镇的繁荣,后有金泽镇的崛起,明清时期又有朱家角镇的极盛。自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经营太湖东南之广大流域之后,本地就有青龙镇的长期繁荣。“青浦”便是因青龙镇而得名,这里不是一个落后地区。相反,青浦境内的金泽等市镇代表了农业、手工业时代的城市化。现代社会学家定义小城镇,指出在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强劲的城镇化运动。和尼德兰、英格兰等地一样,江南地区的早期城市化,也是借助发达的河运系统实现的。现在的金泽镇,镇区总面积108.49平方公里,其中水面面积达到33.84平方公里,金泽镇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为河、湖、港、汊所占据,仍然是一片水乡泽国。江南在17世纪便已经名扬欧洲,“早期全球化”运动中有上海的踪影。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是近代西方人就近观察中国的**本著作。该书以拉丁、意、葡、西、法、英文出版,17世纪时便流行欧洲,其中对“江南”有突出的描写。利玛窦描写徐光启的故乡上海:“这个省份(江南)的这一地区盛产米和棉,棉可以做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人。[“二十万人”当是笔误,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8年)有同样来源的内容,写作“织工二千余人”,比较切近。]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他省份。这里的人,特别是城里人,都非常活跃,不大稳定,头脑聪明,出过很多学者文人,因而也出过很多大官。他们从前身居高位,现在退休后都很有钱,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府邸里。这里天气温和,可以说明何以这里的人要比国内别处的寿命更长些。在这里,人们不以六十岁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过一百岁。”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对上海和江南的描述,启动了欧美人士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如鱼米之乡、物产丰富、文士众多、人性温和等说辞。孟 德 斯 鸠(Montesquieu, 1689 —1755) 在《 论 法 的 精 神 》(1748年)中,把“江南”阐释成一个“由人的勤劳建立的国家”,他说:“有的地方需要人类的勤劳才可以居住,并且需要同样的勤劳才得以生存。这类国家需要宽和的政体。主要有三个地方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中国的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埃及和荷兰。”孟德斯鸠把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和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荷兰低地国家相比较。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土地肥沃,人口繁庶,曾经是罗马帝国*垂涎的省份;而尼德兰是欧洲中世纪以后*早繁荣起来的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航海、文化、艺术都领先于欧洲,孟德斯鸠写书的时候,荷兰人刚刚经历了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全盛时代。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一样,曾经潜心研究中国。孟德斯鸠“汉学”知识主要来源于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其基调是对江南士大夫文化的赞美。为了获取不同资料来源,揭示中国政体的专制特征,孟德斯鸠和皇家图书馆的福建莆田籍馆员黄嘉略(1679—1716)做过深谈。根据黄嘉略的情报,孟德斯鸠说:“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孟德斯鸠修正欧洲人的中国观,说“中国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关于江南,他说:“(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省份土地肥沃异常,因此给欧洲人一个印象,仿佛这个大国到处都是幸福的。”孟德斯鸠把江南从帝国划分出来,单独处理。在中国,“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只是江南的“政权必须是宽和的”,因为当地人民勤劳,智慧,并不淫逸,“像过去的埃及一样;像今天的荷兰一样”。孟德斯鸠的“江南特殊论”,延续着从马可 ? 波罗到利玛窦,再到杜赫德的话语,把江南夸饰成“人间天堂”。我们完全可以说:17世纪以后,江南社会就进入“早期全球化”。19世纪上海大都市的崛起,只是江南社会早期发展的延续。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继元代朱清、张瑄开辟的“海运”事业,上海再一次“以港兴市”。1843年,上海开埠,中外贸易枢纽从澳门、广州转移到上海,各项新兴事业发展。上海周边地区的社会体系剧烈改组,长江三角洲市镇面临着亘古未有之“大变局”,江南市镇渐次融入现代体制。上海县的法华、龙华镇,宝山县的江湾、殷行、吴淞、真如等近郊市镇,首先被大上海吸附。远郊市镇,如七宝、闵行、南翔、大场、罗店等,也承接了上海的近代产业,更新市镇上的传统产业。金泽镇离上海都会区有60公里之遥,不通公路、铁路,仅仅通过传统水路联系,但是现代大都市的辐射力,仍然无时不刻地传输到当地。20世纪30年代后,学者多用殖民地模式分析上海及江南地区的社会转型。他们根据江南传统市镇对于上海新都市经济的“依附性”,定义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都是如此。果真如此吗?果真是帝国主义的上海,榨干了江南经济、断送了江南文化吗?事实未必如此,可能恰恰相反。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1919—1973)的研究表明,近代上海崛起后,长江三角洲地区依次发展,丝、茶贸易额大为增加。墨菲转引英国茶叶专家福钧(Robert Fortune,1812—1880)的统计,外商在上海采购茶叶,运输费大大下降,只占成本的5%,在广州是70%,以至于“上海的茶叶贸易额大为增长,有更多的制茶商能够由于运费下降而进入上海茶叶贸易的出口市场。它不再是一项小规模的专门化的奢侈品买卖,而是一项因运输路线连续不断而成为可能的大规模贸易”。上海的贸易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生产和出口,将过剩的劳动力,还有荒坡上就可以大量种植的茶树,转化为大量的GDP,销往欧美。茶叶之外,生丝的情况也是如此,“太湖周围地区是江浙产丝区的比较重要的中心。在那里的若干地方,特别是无锡、苏州和湖州周围一带,桑树作为首要的农作物,取代了水稻,在四月和五月初养蚕季节的六个星期里,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忙着养蚕。……几乎所有在这个‘中国’蚕丝地区为外贸而生产的生丝,都在上海经由华商和外商经营生丝出口的商行销售”。上海的对外贸易推动了江南的手工业生产。按墨菲的地理学观点,以及许多经济史学者的看法,现代上海的崛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传统水路交通体系密不可分。近代上海的工商业发展主要借用水路交通,而不是维新思想家呼吁的铁路、公路系统。上海的工厂大都建在黄浦江、苏州河以及无数的支流港汊边上,船只和码头承担了原料和成品的运输,极其便捷。“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货物可以如此轻便而成本低廉地经由水道运输,因而几乎没有为供应上海这样大的城市而采用机械化的运输工具的必要。”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现代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近六成,但沪宁、沪杭两条铁路的运输量,却只占全国的7%,还排除了东北铁路的大量份额。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社会发展主要依靠水道,传统的商业网络和交通系统支撑了现代化。金泽镇是江南市镇由传统到现代,从本土向全球过渡的普通例子。19、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今天,江南社会充满了这样的案例。这种社会转型可以用殖民化的依附性——即传统社会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来解释;同样,也可以用全球-地方化——即全球社会吸附本土传统,建立更加合理的分工体系来说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地方主义和全球主义成为“左”“右”人类思想的两种不同解释,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两种意识形态。事实上,生活本身比任何精密细致的理论体系都要生动,且趋于中间状态,而不是去向两个极端。全球-地方主义(Glocalism)确实是一种可能的模式。19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激活了古老江南的传统生产;江南市镇上的传统经济,如丝绸、茶叶、瓷器、家具等产业,都因为加入了全球贸易得到更大的发展。如南浔、震泽镇的丝绸业,宜兴、景德镇的瓷器业,苏州、杭州、徽州的制茶业,都超越了全国市场,不再只是依附于民族经济,而成为19世纪全球经济的一部分。金泽镇的经济在清代中叶已经加入全球贸易体系。一个例子是长三角的内河运输业。我们看到:长江三角洲的内河船运业,自康熙年间上海设埠以后的沿海航运业,以及鸦片战争后各大洋行、招商局举办的远洋运输业一起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Glocal”(全球的)航运体系。江南的贸易、金融、服务业和外国同行之间,既有激烈竞争,也有密切合作。直到民国后期,金泽镇的水路交通网络一直还在使用,分担着上海到江浙之间的重要航运,维持了金泽镇从明清遗留下来的庞大规模。金泽镇的航运业把上海进口和生产的“洋货”,搬运到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同时,把苏南、浙北的棉布、丝绸、茶叶、手工制品,还有人力、原材料等运到上海,转输到世界。然而,金泽镇的优势产业——传统棉纺织业,在20世纪初开始衰落。长江三角洲市镇经济有很强的内部分工,各市镇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总体上来说,三角洲东部的松江府各县,主要以传统棉纺织业为主,西部苏州府湖州府则以丝绸业为主。上海开埠,江南经济卷入全球贸易之后,丝绸业和棉纺织业有不同表现。丝绸业、瓷器业为江南垄断,日本、印度和欧洲企业,偷师学艺,很晚才有自己的丝绸生产,和中国竞争。在江南经济版图上,金泽镇是棉布业和丝绸业的分界。金泽往西50公里之内,有西塘、姚庄、芦墟、黎里、盛泽、震泽、乌镇、南浔各镇,这里是全球贸易中著名的“湖丝”产区,出口表现非常突出,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今称南浔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因丝绸业的发展称为“巨镇”;金泽往东,青浦、上海、川沙、奉贤、南汇、金山、嘉定、宝山的市镇,都以棉纺织业为主。英国和印度的“洋布”打开中国市场后,有英资、日资、华资在上海大量投资机器纺织业。靠近上海的市镇,如宝山县江湾镇、吴淞镇,上海县七宝镇、闵行镇,转型引入现代产业,和英、美、法租界以及南市、闸北一起发展。金泽镇地处丝、棉产业的边界,离上海又是不近不远,20世纪开始,当洋布挤走土布之后,在传统和现代产业中都没有优势产品,金泽镇衰败了。金泽镇的棉纺织作坊,集中在镇西的下塘街,精益求精,规模效应,这里出现过江南地区*为集中和先进的纺织机械制造手工业。按照金泽镇政府近期出版物提供的资料,“下塘街在清朝中叶,镇民大多纺纱织布,一时很盛,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清末,出现了铁业、木业、竹业的小手工业生产,制造风车、牛车和木犁,为农业服务。此类手工业作坊,大大小小有五六十家,作坊的锯木声和榔头的敲打声,整天‘呯嘭’作响,一片繁华的景象”。按照《金泽小志》的记载,金泽镇纺织机械制造业出现得更早,道光年间已经成型,“纺具,曰车、曰锭子,铁为之。车以绳竹为轮,夹两柱,中枢底横三木,偏左而昂其首,以着锭子,轮旋而纱成焉。到处同式,而金泽为工”。金泽镇生产的铁、木、竹复合材料的先进机械,是江南地区*好的,以至于“东松郡,西吴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来购买,故‘金泽锭子谢家车’,方百里间,咸成谚语”。明朝以降,直至清末,金泽镇不但大量生产花、纱、布,还为整个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提供母机,好像是“江南的兰开夏”“中国的曼彻斯特”。可以说,金泽镇赖以生存的支柱产业是棉纺织业。金泽镇的贸易、商业和运输业,都是以棉纺织业为核心建立起来的。20世纪初,上海崛起了亚洲*大的现代纺织工业——机器织布业。华资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英资怡和纱厂(1895)、民资申新纱厂(1915)、侨资永安纱厂(1921)、民资安达纱厂(1938),还有《马关条约》(1895年)签订后以后大量涌入上海的日资内外棉纱厂次第兴办,激烈竞争。“洋布倾销”使得织造和销售本地蓝印花土布的江南市镇一步步地陷入困境。金泽镇传统纺织业的衰败是注定的,但不是剧烈的。上海的现代化对长江三角洲市镇的冲击波,呈中心扩展的水波状,逐渐蔓延到江浙地区。现代工业对手工业的冲击力,在几十年当中慢慢呈现。固然,和上海毗邻的市镇如江湾、法华镇、龙华镇等,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就开始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风气、语言、服饰、习俗,包括民间宗教形式为之一变。但是,处在远郊的淀山湖周围系列市镇,大约要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真正感受到冲击。以服饰为例,据当地作者陈述,青浦在“民国初年,农村服装都用自家纺织的粗布”,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里传入了‘洋布’,那时的农村妇女开始用士林蓝布制衣,并用浅色布或花洋布滚边,作为上街赶市、走亲访友时的穿着”。可见地处远郊的金泽镇受现代化的冲击,要远远晚于上海的周边市镇。金泽在20世纪衰败的情景,如40公里外桐乡市乌镇籍作家沈雁冰(茅盾,1896—1981)在其作品《林家铺子》里描写的那样。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日资纱厂低价竞争,大量出货。原来销售“老布”(土布)的林家铺子,只能转而销售“新布”(洋布)。其时正逢“九一八”(1931)事变发生,日本加剧掠夺中国,江南各地群情激奋,销售“东洋布”的林家铺子老板很痛苦,林家小姐在学校里也被人歧视。一日,小姐醒来,听到母亲哀叹:“这也是东洋货,那也是东洋货,呃!”但是,江南地区的传统产业很顽强,上海的机器织布业并没有完全扼杀长江三角洲城镇的土布产业。80年代,上海宣传部门在“五一”“七一”“十一”安排文艺调演,来自青浦等郊县的文艺演出队,都会穿着蓝花土布服饰,唱跳挑担、插秧等农作姿态的歌舞。2005年,我们**次进入金泽镇的时候,还看到过一些从周围乡村来镇上的老妇人,穿着蓝印花土布的衣服,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费孝通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关注江南传统经济的倒闭。他描述吴江区震泽镇开弦弓村(西距金泽镇30公里):“村里的家庭纺织业实际上已经破产。我在村里的时候,虽然几乎每一家都有一台木制纺织机,但仍在运转的只有两台。因此,衣料大部分来自外面,主要是亚麻布和棉布。村里的缫丝工业主要为商品出口,并非为本村的消费,只有少数人在正式场合穿着丝绸衣服。”这类描述经常被用来证明江南经济的凋敝。但是,事实上震泽镇的丝绸业通过中外贸易更新换代,改为大机器生产。20世纪30年代至今,苏州和湖州一直是全球*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衰败的只是土布。按经济史研究,在统计1911年以前建立的107个江南市镇中,有40个是1861年以后新建立的,其中8个因为新式工厂的建立而兴起。在上海近郊28个老市镇中,有3个因新式事业而复兴。不幸的是,金泽镇不是传统行业持续繁荣的市镇(如震泽),也不是因新式事业推动而复兴的市镇(如朱家角)。江南的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你死我活的,而是融合生存的。传统和现代结合,地方和全球对接,渐渐发展,慢慢交替,过程温和。事实上,金泽镇的土布和传统纺织机械制造业,一直保存到50年代,直到“解放后,随着农村耕作技术的改革,这些手工业作坊,都进入手工业合作社”。......“文革”以后新一次的城市化浪潮中,金泽镇一直在市、县政府的计划之外。90年代以后,上海市政府把淀山湖作为水源保护地,限制本镇的大型工业开发,不再批准国家、市、区级的工业开发区,本镇旧有的手工业自生自灭,新组建的乡镇事业发展也很困难。在长江三角洲一带,青浦西部区域保持农业格局,青浦东区以及邻近的昆山、太仓、常熟等县级市,都远比“青西”发达,金泽镇的乡镇工业在青浦区排在末几位。2000年,金泽镇的28家乡镇企业,用工1490人,工业总产值33464.9万元,都不算突出。*糟糕的数字是利润额,2000年全镇工业总利润只有95.4万元,只比凤溪镇(负403.2万元)、蒸淀镇(95.1万元)稍高,排在21个乡镇、开发区的倒数第三位。另外,金泽镇的三资企业、个体企业也处于相似的落后水平。[以上统计数字,均见于《青浦县志(1985—2000)》,“工业”。]金泽镇,似乎是一座被遗忘的孤城。但是,金泽位于江南,属于上海,仍然与这个高速变化着的世界紧密相连。
作者简介
李天纲
1957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长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宗教历史和上海地方文化研究。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系主任、利徐学社主任,兼任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
代表作有:《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与意义》《跨文化的诠释经 学与 神学的相遇〉〈明末天主教三柱石论教文笺注〉《历史活着》。译作包括:《中国民间崇拜》《清廷十三年》(2012)。主编〈徐光启全集》《增订徐光启年谱〉〈万国公报文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相伯卷》等。
-

寻味中国
¥10.3¥38.0 -

漫谈中国文化(金融·企业·国学)
¥8.7¥26.0 -

瓢箪鲶闲话
¥9.7¥36.0 -

茶经(黑白版)
¥11.8¥48.0 -

经典常谈
¥5.8¥14.8 -

中国馔馐谭
¥12.7¥23.0 -

三大师谈红楼梦
¥14.4¥45.0 -

跨文化的想象:文献.神话与历史
¥9.6¥30.0 -

我的童年在台湾
¥10.7¥32.0 -

地理的故事
¥12.7¥47.0 -

东北的土灶
¥14.7¥45.8 -

神秘的黑猫
¥16.3¥48.0 -

东瀛印象记
¥11.9¥35.0 -

厕神:厕所的文明史
¥20.3¥39.0 -

蒋凡讲世说新语
¥20.3¥58.0 -

中国读本:经典版
¥14.7¥46.0 -

山里山外
¥15.1¥35.0 -

生活十讲
¥16.0¥42.0 -

中国近代编辑家评传
¥6.0¥14.5 -

古典名著聚珍文库:山海经
¥5.6¥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