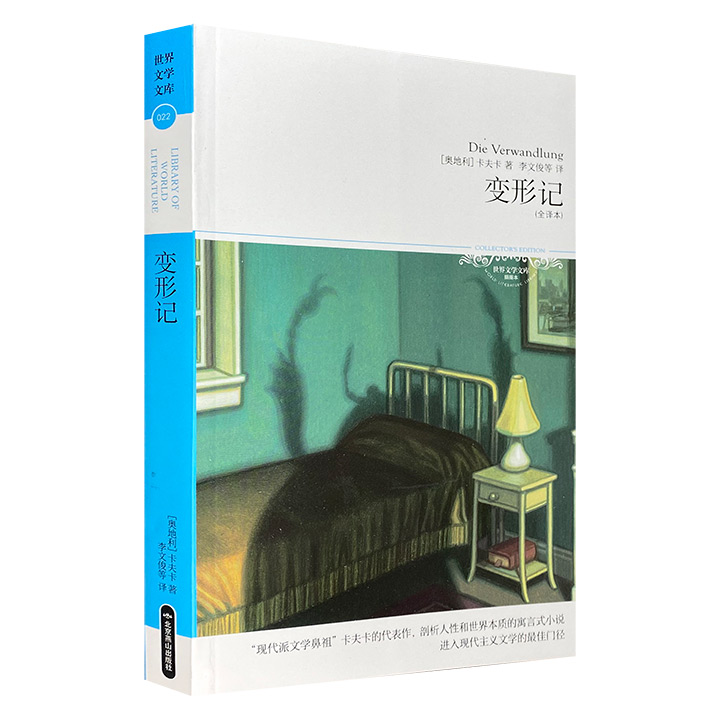
4.9分
包邮变形记 全译本/文学文库022
卡夫卡的作品均采用象征、隐喻、夸张等手法,情节生动,语言简洁流畅,故事怪诞离奇,吸引着不少人孜孜不倦地玩味和研究卡夫卡的著作。

温馨提示:5折以下图书主要为出版社尾货,大部分为全新(有塑封/无塑封),个别图书品相8-9成新、切口有划线标记、光盘等附件不全详细品相说明>>
- ISBN:9787540213183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320
- 出版时间:2019-01-01
- 条形码:9787540213183 ; 978-7-5402-1318-3
内容简介
《变形记》囊括了卡夫卡所有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变形记》、《在流放地》、《在法的大门前》、《饥饿的艺术家》、《乡村教师》、《中国长城建造时》、《一条狗的研究》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它们均采用象征、隐喻、夸张等手法,情节生动,语言简洁流畅;故事怪诞离奇,无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无前因后果,给人以梦幻、神秘、奇特的感觉。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他们在离奇古怪的世界中都有自己的目标,但往往又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卡夫卡的评价及其作品的寓意,学术界历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是这种独到之处,才使人们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玩味和研究它们,才是它们魅力永存的原由。
前言
卡夫卡,其人不可做寻常观。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世界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伟大作家,就其生活经历而言,也许除了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终生未婚之外,可谓是再平常不过了。一八八三年他生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是一个犹太商人之子;小学毕业后升入布拉格一所国立德语文科中学;一九一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德语部,攻读法律,选修德语文学和艺术史;一九六年被授法学博士,翌年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自一九八年起供职于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一九一七年患肺病,一九二二年因病离职,一九二四年病逝,终年只有四十一岁。这便是他短暂而普通的一生,既没有做出什么惊心动魄的英雄业绩,也没有惊世骇俗的举动;既非春风得意亦非穷困潦倒;既非一帆风顺亦非颠沛流离。从形而下来看,一常人也。但若从精神层次来进行观察迥然不同: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痛苦和磨难,孤独和愤懑的内心世界。他在给一度炽烈爱过的女友密伦娜的信中用这样的字句概括了他的一生:“我走过的三十八载旅程,饱含着辛酸,充满着坎坷。”
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他不属于基督教世界,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又对犹太教义持异议;作为一个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是捷克人;作为一个捷克人,他又是奥匈帝国的臣民;作为一个白领人,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资产者的儿子却又不属于劳动者;作为一个职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可作为一个作家,他既无法完全从事创作也不珍惜他的作品。正如他是一个二元帝国的臣民一样,他内心是一个二元的世界,这也就决定了卡夫卡性格上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无归属感,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便成为这样一种性格的衍化物。
犹太民族,斯拉夫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成分混杂于一身,使卡夫卡成了一个多重的无归属感的人,成了一个永远流浪的犹太人,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在致密伦娜的信中称自己是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在另一封同样是致密伦娜的信中,他沉痛地写道:“……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转引自《卡夫卡集》,叶廷芳等译,第三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在这个他认为是莫名其妙的世界里,在他诞生的布拉格,在他的家里,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异乡人。他在敞露心扉的日记里(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写道:“现在,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亲近的,*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这种人生体验和生活感受,不仅流露在他的杂感、书信、日记中,更见于他的作品。《失踪的人》中主人公罗斯曼之在美国,《判决》中主人公本德曼之对父亲,《变形记》中主人公萨姆沙之在家庭莫不如是。在这些艺术形象身上,陌生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表达。
当陌生感成为一个人的主宰时,他便不得不从他生活的世界返回自身世界,这样孤独感便成了一个必然的产物。表现在卡夫卡身上,这种孤独感不仅是在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领域里。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在谈到学生时代的卡夫卡时写道:“……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可是完全不可能与他成为知己,在他周围,仿佛总是围着一道看不见摸不透的墙。他以那文静可爱的微笑敞开了通向交往世界的大门,却又对这个世界锁住了自己的心扉。……却始终以某种方式保持疏远和陌生。”《卡夫卡》,瓦根巴赫着,韩瑞祥译。陕西人民出版社,第六十八页。在青年时期,他渴求爱情,但几次婚约和几次解除婚约表明,他更渴求孤独。在他逝世前三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其说我生活在孤独之中,倒不如说我在这里已经得其所哉。与鲁滨逊的孤岛相比,这块区域里显得美妙无比,充满生机。”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是一种抗拒现实的外化形式,是一种心灵上的需求。他在给他的好友勃洛德的信中说得一语中的:“……实际上,孤独是我唯一目的,是对我的极大诱惑。”《卡夫卡》,瓦根巴赫着,韩瑞祥译。陕西人民出版社,第四二六页。这种生活中和精神上的孤独感必然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来,他的长篇,如《失踪的人》、《城堡》,中短篇如《变形记》、《单身汉的不幸》、《*初的忧伤》,孤独感都是复调式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声部。
在卡夫卡的日记、书信、杂感中读者会一再遇到恐惧这个字眼。恐惧外部世界对自身的侵入,恐惧内心世界的毁灭。正因为他受到恐惧的左右,于是他对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他所遇到的人们眼中正常的一切,他对自己的处境:恋爱、职业和写作,都怀有一种巨大的恐惧。他写道:“我在布拉格过的是什么生活啊!我所抱的对人的这种要求,其本身就正在变成恐惧。”这是他给勃洛德的信中所写的,在给密伦娜的一封信中他在谈到这种恐惧的普遍性时写道:“我总是力图传达一些不可传达的东西,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物,叙述一些藏在骨子里的东西和仅仅在这些骨子里的所经历过的一切。是的,其实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那如此频繁谈及的,现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大事物也对*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卡夫卡把写作看作是自己人生的*大追求,是维持他生存的形式,然而恰恰又是写作使他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写作成了为魔鬼效劳而得到的奖赏,是一种带来死亡的恐惧。他渴求爱情,渴求建立家庭,然而也正是由于恐惧,恐惧爱情和家庭会使他失去自由,影响他的写作而迟疑并几次解除婚约。卡夫卡尊敬和熟悉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把恐惧和绝望看作是对一个破碎和无意义世界的回答,卡夫卡便生活在他认为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而他本人的本质,他自己用了一个词来表述,这就是恐惧。
卡夫卡,其作品不可做寻常读。
卡夫卡仅活了四十一年,从他一九三年开始写**部作品《一次斗争的描述》到他逝世前一九二四年完成的《女歌手约瑟芬(耗子民族)》只有二十一个年头。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始终是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的。他的作品,除去日记和书信,数量并不多;只有三部篇幅并不长的长篇:《失踪的人》(即《美国》1912—1914),《审判》(1914—1918)和《城堡》(1922),且都没有完成;一些中短篇以及也被包括于其内的速写、随感、箴言,如以中文计,也就是百多万字,比起他同时代的一些德语作家,如曼氏兄弟、黑塞、杜布林、霍夫曼斯塔尔等人,其数量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就是这些作品为卡夫卡死后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被尊为现代派文学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因此,我们对他的作品不能做寻常读。
卡夫卡的作品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品,有的评论家称为是寓言或半寓言。也许称之为是寓言式的作品更为确切些,我们无论是读他的长篇还是中短篇,更无需说那些箴言或者随笔了,它们都像是一则寓言,《城堡》中的K,《变形记》中的萨姆沙,《骑桶者》等不都是广义上的寓言吗?但卡夫卡的寓言式作品显然不同于古代的寓言,如伊索的,不同于经典性的寓言,如莱辛、拉封丹、克雷洛夫等人的。其一,卡夫卡不是去进行一种说教,去宣扬一种道德训诫,而是以非理性、超时空的形式表达了一个现代人对现代社会诸现象的观察、感受、表述乃至批判,或者如卡夫卡研究者们所说的:卡夫卡的作品是欧洲危机令人信服的自我表白见海·波里策:《卡夫卡研究的问题和疑难》,载《论卡夫卡》,叶廷芳编,第二一四页。,是“真实的二十世纪神话”见威·埃姆包希:《卡夫卡的图像世界》,载《论卡夫卡》,叶廷芳编,第三六一页。。其二,卡夫卡寓言式作品的多义性。无论是古代的或者经典的乃至现代的寓言都没有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它告诉你的只是一种意义,一个教训,或是道德的伦理的,或是社会的生活的。但卡夫卡的作品通过诡奇的想象,违反理性的思维,不可捉摸的象征,非逻辑的描述有了丰富的神秘的内涵,从而有了多义性和接受上的多样性甚至歧义性;换一个立足点来说,是作品本身妨碍了或阻止了我们去做单一的解释。试想一下,我们不会满足用“仇父情结”或“审父意识”来概括《审判》,同样也不能仅用异化来对《变形记》做终结式的结论。法国荒诞派作家加缪对此有很好的表述,他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一文中写道:“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使读者不得一读再读。它的结局,甚至没有结局,都容许有种种解释……如果想把卡夫卡的作品解说得详详细细,一丝不差,那就错了。”同上书,**三页。我们不能也不应从卡夫卡的作品中去寻求一个终极意义,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结论。不同阶层的读者,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角度(伦理的,道德的,宗教的,社会学的,美学的),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时间场合都会成为解读卡夫卡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我们也不要想一下子就读懂他的作品,也许你读了几遍也感到莫名其妙,一片懵懂,说不出所以然;但是,你在阅读中间,在掩卷之后,你定会产生某种情绪,你的感官必会有所反应:或者惊愕(如读《变形记》),或者恐怖(如读《在流放地》),或者悲哀(如读《城堡》),或者痛苦(如读《审判》);抑或皱眉,沉思,困惑,叹息。总之,你必受触动,必有一得。之后,你不妨再理性地去对它们进行你自己的阐释,绘出你自己的卡夫卡像来。
作家们都是在用自己的笔去构建一个世界,卡夫卡创造的是一个独特的世界。从他的**篇作品《一次斗争的描述》到他的*后一篇作品《女歌手约瑟芬(耗子民族)》,人们都能明显地感觉到,那是一个象征的、寓意的、神秘的、梦魇般的世界;那里面五光十色,有离奇古怪的场景,有超现实、非理性的情节,有象征化的动植物,有异于世俗常人的形象,人物有荒诞的非逻辑的行为举止。无需举他的长篇为例,在这个中短篇选本中,像《变形记》、《审判》、《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致科学院的报告》、《乡村医生》等,每一篇都是如此,然而,恰恰这些在正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不可能发生的,在卡夫卡笔下,借助细节上描绘的精确性,心态上的逼真酷似,特别是整体上的可信性,就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真实,一切都变成了现实,可触摸到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甚至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想想《变形记》中变成了甲虫的萨姆沙,《致科学院的报告》中的人猿,《地洞》中的小动物,他们不就是处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世界中的人类本身吗?这种基于整体上是悖谬和荒诞上的真实都令一向反对现代派的卢卡契大为赞叹,他在《卡夫卡抑或托马斯·曼》一文中写道:“恐怕很少有作家能像他(指卡夫卡)那样,在把握和反映世界时候,把原本的东西和基本的东西,把对前所未有的事物的惊异,表现得如此强烈。”见《论卡夫卡》,叶廷芳编,第三三九页。
卢卡契上面这段话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整体上的非真实性和细节上的真实性截然分开,从而得出如他所说的:“从形式上的特点这一角度看,卡夫卡似乎可以列入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主观地看,他还在更高程度上属于这个家庭呢。”见《论卡夫卡》,叶廷芳编,第三三九页。(重点为笔者所加)卢卡契这篇文章的本意是对卡夫卡从细节上肯定,从整体上加以否定。从实质上来看,卡夫卡笔下的精神世界与经验世界是相互交织的,相互干扰和相互渗透的,甚至达到一种两者之间的界线模糊的程度,精神真实与感性真实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了。这样,就如威·埃坶里希所表述的那样,卡夫卡作品中的“精神之物再也不是在经验之中和一切经验之上游移的不可理解、不可捉摸的东西了……而是作为一种十分自然的真实出现在眼前,但同时,这个真实也突破了一切自然真实的法则。”见《论卡夫卡》,叶廷芳编,第三四七页。现在我们可以说了:卡夫卡不是去复制,去摹写,去映照现实,而是独辟蹊径用非传统、反传统的方式去构建了一个悖谬的、荒诞的、非理性的现实;而这个现实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比自然现实更为真实,能使读者更为悚然更为惊醒,使人对自身和对社会的认识和批判更为深化和强烈。
这里就这个选本做些说明。本书所选均是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其中有些篇目已有译本,在征得译者的同意后收入此书——在此向他们表示谢意,有些则系新译,均据马克斯·勃洛德编,费舍尔袖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七卷本《卡夫卡全集》译出。篇目的排列,无论是卡夫卡生前发表还是在他死后由马克斯·勃洛德整理发表的,一律以写作年代为序,但每篇附有简单说明,便于读者了解。
卡夫卡的作品多已译成中文了,几家出版社都出了卡夫卡的小说集,但把他的几乎全部的中短篇作品都编在一起,出一个单行本,这还是**次。希望喜欢卡夫卡作品的人也能喜欢这个集子。编选和编排上的不完善之处,尚希得到读者的指正。
——高中甫
目录
n一次斗争的描述
n公路上的孩子们
n树
n衣服
n过路人
n倚窗眺望
n乡间婚事筹备
n归途
n揭开一个骗子的面具
n单身汉的不幸
n决心
n判决
n变形记
n在流放地
n乡村教师(巨鼹)
n一个梦
n法的门前
n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
n猎人格拉库斯
n视察矿区
n桥
n豺狗和阿拉伯人
n新律师
n在马戏场顶层楼座上
n陈旧的一页
n骑桶者
n敲门
n万里长城建造时
n邻居
n致科学院的报告
n家长的忧虑
n十一个儿子
n一场常见的混乱
n塞壬们的缄默
n乡村医生
n普罗米修斯
n新灯
n在阁楼上
n城徽
n舵手
n秃鹰
n归来
n小寓言
n陀螺
n初的忧伤
n饥饿艺术家
n一条狗的研究
n放弃吧!
n关于譬喻
n一个矮小的女人
n地洞
n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
n墓中做客
n犹太教堂里的“宠物”
n误入荆棘丛
节选
与祈祷者开始了的谈话
有那么一个时期,我天天都到一座教堂去,因为我爱上的一个少女傍晚都要去那里跪着做半个小时的祈祷,这期间我能安静地观察她。
有一次少女没有来,我不耐烦地向那些祈祷者望去,一个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把整个瘦长的身体都投伏在地上。有时他用全身的力量抓住他的脑袋,把它放到摊在石头上的双掌上,呻吟地摇晃不止。
在教堂里只有几个老年的妇女,她们不时地侧转过她们裹着头巾的脑袋,向这个祈祷者望来。引起她们的注意好像使他快乐,因为在他每做一次虔诚的叩拜时,他都用眼睛逡巡下四周,是不是有不少人在注视他。
我觉得这不得体并决定,等他离开教堂时跟他谈谈,径直地问他,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祈祷。因为自从我到这座城市以来对我来说弄清一切是至为重要的,即使现在我也只是对此感到恼火:我的那个少女没有来。
但直到一个小时之后他才站了起来,扑打他裤子上的灰尘,可弄了那么长的时间,我都想喊叫起来:“够了,够了。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您穿有一条裤子。”他十分谨慎地画了个十字,随后向圣水盆走去,沉着得像一个水手。
我站在圣水盆和大门之间的路上并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得不到解释就不会放他过去的。我咬紧嘴唇,这是为一番讲话所做的*好准备工作,我伸出右脚支撑住自己,同时用左脚尖点地,因为这样做会赋予我一种坚定,这是我常有的经验。
这个人可能责骂我,他向脸上洒了圣水,也许我的目光早就使他感到担心,现在意想不到的是他奔向大门冲了出去。玻璃大门关上了。我紧随其后跑出大门,可是我再也找不到他了。因为那儿有好几条狭小的巷子,交通繁忙。人们熙来攘往。
在随后几天他没有露面,但那个少女来了并又在旁侧的祈祷室的一隅里祈祷。她身穿一件黑色的衣服,它的肩部和背部是透孔的——垂下的衬衣边是半月形状——从它们下边的边缘悬吊着的是剪裁得体的丝绸底托。因为这个少女来了,我很高兴忘掉那个男人。我开始关心起自己,当他稍后又定时前来并按自己的习惯进行祈祷时,再也不理睬他了。
但他路过我身边时总是突然加速匆匆而过,并转过脸去。可相反的是他在祈祷时更多的是望着我。看来好像是他对我很生气,因为那时我没有跟他谈话,他认为,通过那次我跟他交谈的企图,我就是自己承担了义务,这终归是要实现的。在一次布道之后,当我总是在晦冥之中跟着那个少女与他相遇时,我相信我看到了他在微笑。
这样一项与他交谈的义务当然不存在,但我几乎不再有一种跟他谈话的渴求了。甚至,当我有一次跑着到教堂广场时,那当儿钟已敲响七点,少女早已不在教堂,那个男人还在神龛前的栏杆,我仍在迟疑不决。
终于我用脚尖蹑行到门廊,给了坐在那里的乞丐一枚铸币,紧挨着他候在敞开大门的后面。在那儿大约有半个小时长的时间我会使这个祈祷者感到惊讶,这使我感到高兴。但这并没有持续下去。不久一些爬上我衣服上的蜘蛛令我感到十分别扭。并且从教堂的昏黑中每走出一个大声喘气的人,我每次就得躬身,这太讨厌了。
他也来了,我注意到,稍顷之前大钟响起的声音,令他感到不安。在他走出来之前,他必定要用脚尖先是漫不经心地蹭蹭地面。
我站了起来,走前一大步,拦住了他。
“晚安。”我说并用手捅了捅他的衣领,走下台阶,到了灯光通明的广场。
当我到了下面时,他转身向我,这时我还一直在他的后面,于是现在我们就肚皮碰着肚皮,面对面站着。
“您就不会放开我!”他说,“我根本不知道。您怀疑我什么,但我是无辜的。”随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当然不知道,您怀疑我什么。”
“这儿既谈不到怀疑也说不上无辜。我请您不要再谈这类事情。我们彼此陌生,我们的相识决不会比教堂台阶更老,如果马上开始谈什么我们的无辜,那我们会走到什么地步呢。”
“这完全合乎我的意思,”他说,“再说您说到‘我们的无辜’,这就是说,如果我证明了我的无辜,您同样也必须说您的无辜不是吗?您指的是这样吗?”
“非此即彼,”我说,“但我只是因此才跟您谈,因为我有话要问您,您没注意到这点!”
“我想回家。”他说并稍微转了转身。
“我相信。不然我早就跟您交谈了吗?您不会相信,我是因为您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才跟您谈话的。”
“您是否太不坦率了?怎么?”
“难道要再次对您说,这儿不谈这类事情吗?坦率或者不坦率在这儿有什么相干?我问,您回答,然后分手。之后我认为您可以回家,随您多快好了。”
“我们下一次会会不是更好吗?找个适当的时候?也许在一家咖啡馆里?再说您的未婚妻小姐在一两个小时前才离开,您还能追上她,她等您很长时间了。”
“不,”我叫了起来,这声音混杂在从旁驶过的有轨电车的喧嚣之中。“您逃脱不了我的。您使我越来越感到满意。您是一个幸福的猎物。我为自己感到庆幸。”
这时他说:“啊,上帝,像人们通常说的,您有一颗健康的心和脑袋,用石头做的。您把我叫做是一件幸福的猎物,您多么幸运呵!因为我的不幸是一种摇晃不定的不幸,人们能触摸到它,于是它就激起了好奇者的兴趣。因此呢:夜安,再见。”
“好的!”我说道,抓住他,揪住他的右手。“如果您不自愿回答,那我就强迫您。我会跟着您,左边和右边,不管您到哪儿,就是通向您的房间的楼梯我也要上去,并且坐在您的房间里,有个地方就行。您只稍看看我就好了,这是笃定的。我一定坚持下去的。但您怎么会,”我靠近他,因为他比我高出一头,我是对着他的脖颈说这番话的,“——但您怎么会有勇气来阻止我?”
他朝后退去,轮番吻着我的双手,并用泪水把它们弄湿。“没有什么能拒绝您。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想回家,我事前就已经知道了我无法拒绝您。我只是请求,我们*好到那边的小巷子里去。”我点了点头,我们两人就向那里走去。这时一辆车把我们分开来,我停下了,他用双手向我示意,我急忙赶了过去。
但到了那里他并不满意巷子的昏暗,这里边的路灯彼此相隔很远并且几乎都安装到第二层楼那么高,于是他把我带到一幢旧房子的低矮门廊里,上面有一盏小灯,垂挂在木头台阶的前面。
他把他的手帕铺放在一个台阶的平台上并请我坐下:“您坐着能更好地问,我站着能更好地回答。但不要纠缠!”
我坐了下来,因为他把事情看得如此认真,但我必须要说:“您把我带到这样一个洞里,仿佛我们是密谋造反的人,但是我对您只是好奇,您对我只是恐惧,我俩是因此而连在一起的。基本上我只是要问您,您为什么在教堂里这样祈祷。您在那里怎么是这样的举止!像一个完完全全的傻瓜!这多么可笑,对旁观者和虔诚的人说这太不愉快了,无法忍受!”
他把身体靠在墙上,只有脑袋可以自由活动。“不是别的,只是错误,因为虔诚的人把我的举止看作是自然的,其他的人看作是虔诚的。”
“我的恼火是对此的一种反驳。”
“您的恼火——太高兴了,有一个真正恼火的人——只是证明了,您既非属于虔诚人又非属于其他人之列。”
“您是对的,这有一些夸张,如果我说您的举止使我恼火;不,这只是使我感到有些好奇,我一开头说得很准确嘛。但是您,属于哪一种呢?”
“啊,被人注视,我只是觉得开心,就这么说吧,不时把一个阴影投到神龛上。”
“开心?”我问,我的脸绷紧了。“不,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您不要对我发火,我的表达有误。不是开心,对我说来这是一种需要;让人用这样的目光捶打我一个小时是种需要,而与此同时整个城市围着我来转——”
“您在说什么,”对这个小小的说明和下作的做法我大声喊叫起来,我怕沉默下来或者声音微弱无力,“您说的是真的。现在我看到了,上帝作证,我从一开始就猜想到您是什么样的状态。难道这不是狂热的陆上晕船症和一种麻风病?如果它们不是这个样子,您由于纯粹的高烧对事情的这样名副其实的名字感到不高兴,对此不满足,那现在您就赶忙给它们冠上个随便想出的名称好了。只是要快,只是要快!但是您还没有摆脱它们时,您就又忘记了它们的名字。田野里的白杨树,您称之为‘巴贝尔塔’,因为您不想知道那是一棵白杨树,它又摇曳起来,没有名字,于是您就称它是‘诺亚’,他喝醉了就是这样。”
他打断了我:“我很高兴,您说的这些我都不懂。”
我激动起来,快速地说:“您对此感到高兴,正因此您表明了您是懂的。”
“我不是说了吗?人们对您是没有什么可拒绝的。”我把双手放在高一层的台阶上,向后靠去,并用这种几乎不可理解的姿势发问,这种姿势是摔跤运动员挽救自己的*后一招了。“请原谅,但当您把给您的一种解释又重新抛回给我时,这是不公平的。”
他变得勇敢起来。他把双手交叉在一起,使他的身体协调一致,有些勉强地说:“您在一开始就排除了关于公平性的争论。真的,除了使您对我的祈祷方式加以理解之处,我对其他的都不在意。这么说您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祈祷了?”
他在试探我。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是为此而来这里,我当时就对自己说过,但这个人正因此而逼迫我去听他说。于是我只需摇摇头,一切就完满了,但我恰恰在这一瞬间做不到。
这个人面对我微笑。随之他跪倒下来,脸上是一副懒洋洋的怪相,他说:“现在我终于也能透露给您了,我为什么要让您同我交谈。是出于好奇,出于希望。您的目光好长一段时间在安慰我。我希望从您那里知道,该如何对待那些像雪崩一样吞没我的事情,而在其他人面前立在桌上的一小杯烧酒像座纪念碑一样的牢靠。”
由于我沉默不语并脸部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他就问道:“您不相信其他人是这样?真的不相信?那您听我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在一次短暂的中午睡眠之后我睁开了眼睛,我听到——毕生我都弄不清楚——我的母亲用十分自然的语调从阳台上向下问道:‘您在做什么,我亲爱的?天可是太热呀!’一个女人从庭院里回答说:‘我在树荫下吃点心呢。’她们随意交谈,说的也不怎么清楚,好像那个女人有什么要问,我母亲在等着回答。”
我相信我是在被问,因此我把手伸进裤后兜里做出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但我什么也不找,而只是要变化一下我的目光,以表现出我对谈话的兴趣。同时我说,这件事非常引人注意并且我根本就不理解。我也补充说,我不相信它的真实性并且它必然要达到一个固有的目的,而我恰恰看不透它。随后我闭上双眼,摆脱开恶劣的灯光。
“看看吧,鼓起勇气,比如说您有一次同意我的观点,为了告诉我此事,您提醒过我,而且不是出于私利。我丢失了一个希望,我得到了另一个希望。
“不是吗,我为什么应该羞愧——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羞愧——因为我走得不正,走得困难,不是用手杖敲打着地上的石路并且不去触摸在身旁路过人的衣服?难道我不该理由十足地支起领子,端起肩膀沿着房屋蹦跳而过,有时就消逝在广告窗的玻璃里?
“我度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为什么这一切都建造得这么恶劣,致使有些高楼时而倒塌,人们没法找出任何一种表面上的原因。我爬上垃圾堆,问那个我碰到的人:‘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在我们的城市里——一幢新房子——今天这是第五幢了——您想一想吗。’没有人能回答我。
“人们经常跌倒在巷子里并且躺在那里死去。所有的商人打开了他们的门,挂出来商品,敏捷地走过来,把死者抬进一所房子里,随后返回,嘴和眼睛露出微笑,开始讲话:‘日安——天空是苍白的——我卖出了许多头巾——是呵,战争。’我跑进房里,在我多次胆怯地举高弯起手指的手之后,我终于敲响了房东的小窗户。‘早晨好,’我说,‘我觉得好像不久前有一个死人被带到您这儿了。您不愿友好地指给我看吗?’他摇了摇头,好像他不能决定似的,我补充说:‘您要注意!我是秘密警察,要立刻看看死者。’现在他不再犹豫不决了:‘出去!’他喊了起来。‘这个流氓习惯了每天都到这儿转悠!这儿没有死人,也许旁边那家有。’我打了招呼就走了出来。
“但随后,当我穿越一个大广场时,这一切我都忘掉了。当人们出于傲慢建造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广场时,为什么不在广场上围起栏杆呢?今天刮的是西南风。议会塔楼上尖顶描绘出个小圈。所有的玻璃都在发出响声,路灯杆像竹子似弯了下来。柱子上的圣玛丽亚的大衣刮了起来,空气在撕扯它。难道没有看见吗?在石头上行走的先生们、女士们飘了起来。一当风停下来时,他们就站住了,相互间说了些话,彼此躬身致意,但风又吹了起来,他们无法抗拒它,所有人同时都抬起了双足。虽然他们都紧紧地捂住他们的帽子,但他们大饱眼福,扫视四周,什么都不放过。只是我感到害怕。”
对此我说:“您早先讲的您母亲和庭园里女人的故事,我一点也不觉得有趣。不仅仅是因为我听过我也经历过许许多多这类故事,甚至我本人有些时候也参与过。这种事是完全自然的。难道您真的认为,如果夏天我在那座阳台上不会问同样的问题和从庭园里能做同样的回答?一件太平常的事了!”
当我说完时,他好像终于安静下来了。他说,我的穿着很可爱,他非常喜欢我的围巾。我有着怎样一身细嫩的皮肤。这番表白太清楚不过了,无法加以收回。
……
作者简介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欧洲的表现主义作家,其代表作有《判决》《变形记》《审判》《城堡》等。
-

事已至此先吃饭吧
¥17.6¥55.0 -

她们
¥16.0¥46.8 -

中国小说史略
¥11.5¥35.0 -

我是一只骆驼
¥12.5¥32.0 -

瓦尔登湖
¥11.1¥39.0 -

有趣,都藏在无聊的日子里
¥14.5¥45.0 -

一间自己的房间
¥16.4¥32.0 -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15.8¥39.0 -

读人生这本大书
¥8.8¥26.0 -

我的心曾悲伤七次
¥7.9¥25.0 -

一个人生活
¥14.5¥45.0 -

存在的艺术(八品-九品)
¥14.0¥39.0 -

像我这样和生活开玩笑的人
¥16.6¥52.0 -

门
¥14.4¥42.0 -

几多往事成追忆
¥10.6¥32.0 -

2025读书月阅读盲盒——人间烟火收藏夹
¥42.3¥168.0 -

随园食单
¥9.1¥30.0 -

茶,汤和好天气
¥8.8¥28.0 -

夏日走过山间
¥9.1¥30.0 -

到山中去
¥9.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