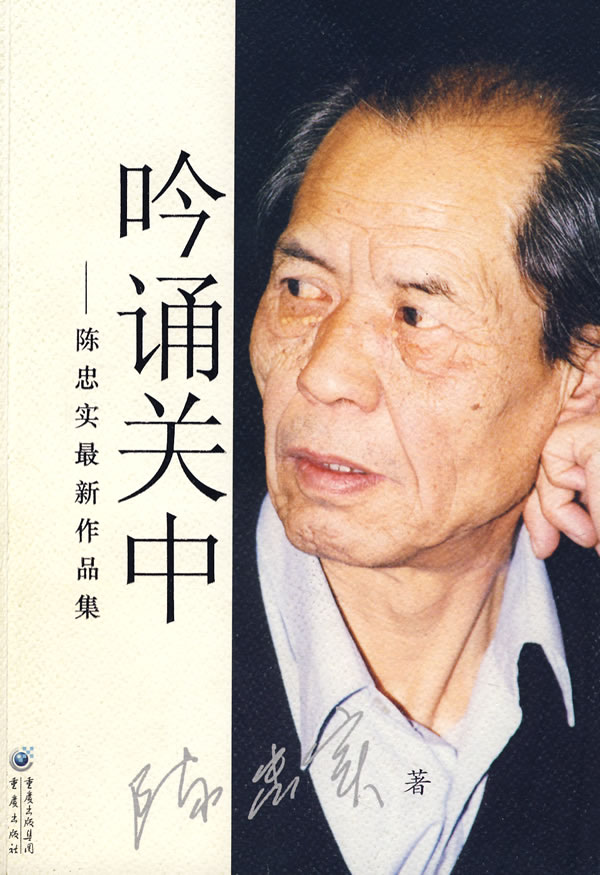了解一个真实的陈忠实
很多年前读过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被先生的乡土情结、民族情思感染,再次读到先生的著作,欣喜中心灵深处泛起极大的震撼,每一篇作品都是先生对生活的记录和思考,但无一不是对这方热土的浅吟高诵。
- ISBN:9787536694651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345
- 出版时间:2008-03-01
- 条形码:9787536694651 ; 978-7-5366-9465-1
内容简介
《吟诵关中——陈忠实*新作品集》收集了作者自2002年至2006年之间所创作的短篇小说2篇、散文、随笔57篇,文论、对话49篇,共40余万字,由于作者近几年未出版图书,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出版本书是为了给关心他、研究他的读者与机构一个交代。
目录
娃的心,娃的胆
——三秦人物摹写之一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三秦人物摹写之二
第二辑 散文·随笔
为城墙洗唾
——辩证关中之一
粘面的滑稽
——辩证关中之二
遥远的猜想
——辩证关中之三
孔雀该飞何处
——辩证关中之四
乡谚一例
——辩证关中之五
也说乡土情结
——辩证关中之六
两个蒲城人
——辩证关中之七
舒悦里的亲情和友谊
永远的骡马市
皮鞋·鳝丝·花点衬衫
从大理到泸沽湖
在好山好水里领受沉重
一把铁勺走天下
第三粒失球致使的摧毁
——老陈看奥运之一
妩媚的回眸
——老陈看奥运之二
失败仍令我敬重
——老陈看奥运之三
为女曲喝彩
——老陈看奥运之四
话说梦游
——老陈看奥运之五
胜者的平静与败者的微笑
——老陈看奥运之六
在河之洲
柴达木掠影
借助巨人的肩膀
——翻译小说阅读记忆
完成一次心灵洗礼
——感动长征之一
黄洋界一炮
——感动长征之二
白鹿回到白鹿原
太白山记
关山小记
也说中国人的情感
再到凤凰山
陷入与沉浸
——《延河》创刊50年感怀
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
也说“抬杠”
陪一个人上原
走过武汉,匆草一笔
半坡猜想
魅力亨利
五月,临近盛事的期待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一
正确的坚定和无知的固执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二
*后才学会射门及其他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三
黑马尚未出现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四
帅气和率性的转移之谜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五
绅士风度和心理赘肉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六
尽享盛宴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七
又一次高潮式的盛宴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八
太过的残酷和太过的轻松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九
经典的防守也精彩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
谁都强,谁都强不起来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一
再看亨利的魅力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二
绝妙的与吓人的
——2006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三
老陈与陈老
娲氏庄杏黄
父亲的树
地铁口脚步爆响的声浪
——俄罗斯散记之一
林中那块阳光明媚的草地
——俄罗斯散记之二
回家折枣
关中有螃蟹
1980年夏天的一顿午餐
第三辑 文论·对话
重新解读《家》,一个时代的标志
——写在巴金百岁华诞
你的句子已灿灿发亮
生活有脉象,我的脉象
——小说自选集新版序
背离共性,自成风景
——陕西名家作品选·序
什么使我钦敬
——读《走进李焕政》
有剑铭为友
关于《开坛》
你的发现,令我敬重
我的关中
心灵的狂欢和舞蹈
关中娃,岂止一个冷字
——读《立马中条》
天性与灵性
令人惊喜的阅读
探索·归结·展示
——在《王蓬文集》首发式上的讲话
灿烂在创造里
——感动葛玮
红烛泪杜鹃血
难以化解的灼痛
——读陈行之新作《危险的移动》
一种气质,鲜嫩和灿烂
——罗贯生山水画印象
思辨的这一声
——读朱鸿散文之感受
敬重宝成
天使或是蜻蜓,翅翼沉重
——读《午夜天使》及其来由
吟诵关中
欷欺暗泣里的情感之潮
仰天俯地无愧生者与亡灵
——感动孔从洲将军
诗性的婉转与徘徊
业已铸就无限
——悼念巴金
陈孝英,让我感到灿烂
气象万千的艺术峡谷
——高峡印象
真实又真诚的叙写
——毛安秦散文读记
别一种情怀
心斋,一个海阔的文学空间
中国乡村形态的智慧表达
——我读《山匪》
筛选自己
少年已知情滋味
——禹治夏诗文印象
我看话剧《白鹿原》
在现实的尘埃中思索与漫游
——序远村诗集《浮土与苍生》
再读《活动变人形》
长庆,鲜活的记忆与激情的书写
印在生命脚印里的诗
——冯在才诗集《曲江吟》阅读印象
人生笔记的笔记
难得一种真实
关于45年的答问
文学的力量
——与《陕西日报》记者张立的对话
关于《白鹿原》及其他
一与《时代人物》周报记者徐海屏的谈话
公安文化及其他
答《解放日报》记者姜小玲问
答《南方周末》记者张英问
和《嘹望东方周刊》记者的对话
我相信文学依然神圣
——答《延安文学》特约编辑周碹璞问
节选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三秦人物摹写之二
柳青终于决定:自己消灭自己。
他已经确定了周密的消灭自己的计划和具体的实施方案。*关键的一点是消灭自己的方式———他决定采取电击。这也许是他唯一能够找到的办法,唯一能够做出的选择。
他尚未被*终判决,却已经生活在和囚犯无异的环境里。这是一排只有顶棚和墙壁的平房,很长很长的一排,没有隔墙。据说这是文化行政管理机关停放自行车的车棚,原先只有三面墙壁,空着的那一面自然十分宽敞,是为着庞大机关里的干部上班来存放车子下班回家时取走车子避免拥挤磕碰的精心设计。现在把敞着的那一面垒起墙来了,安上了一扇门,自行车棚就变成一幢完整的平房了。柳青就被囚禁在这幢屋子里,还有许多他认识或不认识的文艺界被揪出来通称为“牛鬼蛇神”的人。这个被堵上第四面墙壁的房子,不再叫做车棚,很快就有了一个“牛棚”的名字。选择这个房子是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才确定下来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好在没有隔墙,把一群戴着“牛鬼蛇神”帽子的人装进去,通铺大床,一人占一块床板,谁躺下谁坐起谁翻身谁皱眉谁傻笑谁和谁互使眼色都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中,也减少了看管人员的人数和劳累强度。上厕所有人跟着,被单独叫去训话更有监视者;弄一撮毒性剧烈的老鼠药或杀灭害虫的农药是不可能的,亲属都被隔离接触了,无法获得;上吊也是无法实施的,既没有绳子,也没有拴绳上吊的悬梁或可以承载一个人体重的壁钩;刎颈或割断手腕或腿上的主动脉,没有刀子,再说万一一刀割不死再被抢救过来,会有“自绝于人民”的又一桩被认为叛变行为的罪名;唯一能够消灭自己的手段,便是电击———房子里有电,这是**的也不引人注意的照明设备。更关键的是,一触即宣告生命结束,短暂的一瞬就把较长时间酝酿确定的消灭自己的方案实施完成了。
在决定这个晚上就付诸实施的时候,他甚至庆幸自己掌握有*基本的用电常识。这是他久居乡村的意外收获。乡村滞后于城市的生活条件迫使他学会的用电知识。他住在被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写过的终南山下的蛤蟆滩的南沿,那是不太高也不甚陡的一道原坡。那儿有一幢在解放后破除迷信运动中搬掉了泥胎神像的庙院,一番整修以后,他就携妻引子住了进去。站在门口可以远眺终南山壁立突起的群峰,或高或低的峰峦之间绝无雷同的过渡性谷地。终南山几乎终年都被薄雾和烟岚缭绕着笼罩着,只有雨后或强劲的西风扫荡之后,才可以看到清晰的山峰和山谷的面目。眼皮下的蛤蟆滩,不是四季都在变换色彩,而是每天都在神奇地呈现着浓淡深浅的诱人的色彩,乃至清晨午间傍晚都显示着变化。他踏遍了河川的大路小径,麦子扬花和稻子扬花的香味各具魅力,刚刚犁翻的新鲜泥土的清新气味是难以恰当描述的……他在庙院里常常发生的困难却是断电。停电是不可抗拒的,也是心安理得的,他知道国家对农村定时供电是电力尚不充足,他备有蜡烛。有电而因为家里线路故障再停电就让他很不甘心,就难以忍受淌着油的蜡烛的昏暗光亮,就想找电工来检修。电工热情而又耐心,多出于对兼着县委副书记的作家的尊重,毫无可嫌指责之处。问题是他得亲自去找,或让妻子马葳去找。有一段不近的路程且不论,往往找不见人,电工是大忙人也是大活物,不会呆在家里等候用户去找;还有下雨下雪不便出门的时候,还有黑天半夜的不便……随后他学会了接电,知道了开闸关闸,也懂得了火线和地线,尤其明确火线和地线一旦交叉接通,就会发出光明,也会击打死*强壮的生命。现在,乡村生活迫使他学会的*简单的电路技能,可以用来实施消灭自己的目的了。
电灯在这幢被床铺占满的房子里亮着。这些床铺的住户或坐在床沿上阅读毛泽东著作,或坐在小马扎上以床为依托写着读书笔记或交待罪恶的材料,从早晨到下午再到晚上,这是*基本的内容,斗争会揭发会单个训诫,毕竟不是每天每晌都会发生的事。柳青坐在床沿,那双十万个人里也难得挑出的明亮犀利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眼前的读本;这样透亮饱满的光泽却看不见一个汉字,是这些汉字已经与即将消灭的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把遗嘱已经写好。他把死亡的姿势和摆放遗嘱的身体位置都想好了。他把电击的方式也论证确定,用他所具备的*简单的也是*初级的电工技能,一只手攥住火线,把一只脚伸到床下踩住地线,他的身体就在那一瞬间宣告生命的毁灭。这间房子里的电线的线路就裸露在砖墙上,仍然是此前作为自行车棚的原有电线设备,许是来不及装修得稍微隐蔽一点,许是这幢作为牛棚的主宰者疏忽了,结果给企图消灭自己的柳青提供了条件。
他已经躺到床上了。所有人都躺到床上的被窝里了。不管能否预知明天,不管能否进入睡眠,大家都按时钻进被筒里,电灯也按主宰者规定的时间熄灭了。柳青睁着眼睛躺着,左手把那份遗书按在胸脯上。遗书有三句话:
我不反党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
我的历史是清白的
这是我反抗迫害的*后手段
他静静地躺着等待着。等待这屋子里的痛苦着的灵魂暂且忘却痛苦响起鼾声,他就可以伸出右手抓那根早已看好的电线,再伸出左脚踩踏另一根被农村电工称作地线的电线了。他的聚着整个生命活力的眼睛瞅着顶棚,顶棚穿透了,抑或是揭掉了,湛蓝的天幕明晰地波动着银河……
轮到柳青上批斗台了。
他倾情歌颂抒写的终南山下的蛤蟆滩和这村那寨的男女已经陌生了,以庙院安置的家院和书桌也陌生了,*熟悉的场合倒是各种批判斗争的台子,或固有的或临时搭建的或人多的或人少的,走上台再弯下腰接受各种语言的谩骂和栽赃和丑化和打倒踩翻等等,都给耳朵刺出血滴磨出茧子麻木不辨了。无论斗争场面的大小,无论批斗台的高低,柳青唯一不变的是他走上批斗台时的脚 步和姿势,他穿着蛤蟆滩中老年男人穿的对门襟布纽扣黑颜色的棉袄,差别在于布的质料。农民多是自家织布机生产的土布,柳青是用国家配给的布票买来的机器纺织的洋布;头戴一顶被乡村人俗称为瓜皮的无檐帽,执行斗争他的造反派主持人勒令他摘下帽子时,他就从头上一把抓下来塞到棉袄的明口袋里,圆溜溜的光头和阔大的前额就呈现给参加斗争会的所有人。圆脸通鼻,鼻头下的上唇有一排黑森森的短胡须,成为他显著的风景和奇特的标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般都不蓄胡须,但*具风景异质的是那一双眼睛,走向批斗台的时候,从拥挤着人群的呐喊声中的通道走过去,柳青只瞅着脚前的路,两边的人都能在瞬息里敏感那双眼睛泻出的纯净犀利透彻的光亮,混浊的铺天盖地的口号声是无法奈何那一束光亮的。他很单薄,身高不过一米六,体重大约只有七十斤,这样的穿戴这样的体型和体重,很难有雄壮和威武,然而柳青缓慢的步履能产生一种威势……走在他前边的“牛们”已经走上台了。柳青唯一感到不同的是变换了花样的侮辱方式。是的,每次批斗会上,都有新的侮辱被斗对象的花样创造出来。今天,不再是主持斗争会的造反派向参加批斗会的革命群众一一介绍被斗争者的姓名,姓名前肯定要加上诸如“三反分子”“黑帮”等定语。主宰他们命运的人,给每一个被斗争者确定了一个定性的用语,让他们挨个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自报家门自我辱践,给柳青规定了“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作家柳青”的定论,不许少说一字说错一字。
排在柳青前头走上批斗台的被斗争的对象,一个一个都按规定给他们的定性自报姓名了。每个人报完,就会有领呼口号的人在台前挥拳领头呼口号,诸如“打倒××××分子×××”,台下举拳呼应,绝不厚此薄彼。小小的差别也不是没有,某人自我介绍时或有结巴或声音太小,就会被严厉斥责再来一遍。柳青走上批斗台了,被主持者搡戳着呵斥着走到台前指定给他的地点,站定,服从的肢体行为里隐隐透出绝非顺从的意味,也透出无奈里的沉静,倒显示出呵斥着搡戳着他的主持者的狂乱和虚妄。柳青开口了,口齿清晰一字一板嗓门腔调颇为洪亮: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向革命群众报到……
斗争会的主持者顿时愣住了。策划和组织这场斗争会的大小头目们,也都在主次分明的斗争台上的各个位置上愣怔住了。台下拥挤的黑压压的人群也在柳青的话音尚未落定时愣怔住了,台上和台下同时呈现出冷寂这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所造成的心理反应不及时的情状。所有人尤其是台上的那些主宰者,愣怔的同时明白无误地意识到挑战和反抗。出于各种心理需要和生活目的的需要狂欢着“文化革命”的得意者,早已形成接受被批被斗者顺从和讨好的心理状态。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挑战和反抗,把他们惯于接受顺从乞求的心理状态打乱了颠覆了,也把与会者普遍形成的社会性心理扰乱了,于是便出现了潜伏着巨大危险的冷场。
潜伏的危险以铺天盖地的愤怒爆发出来。一记耳光扇到挑战的反抗的作家柳青脸上。扇打这**巴掌的人,无疑是**个从愣怔状态里清醒过来的人,肯定是具有敏锐反应的神经功能的人。随之就有人伸出腿脚到柳青身上了。同时就有几乎挣破嗓门的口号呼喊出来。在台下呼应的口号声浪里,柳青重新站端立定了,依然平视着的眼睛愈加清澈透亮,有一股逼人的冷光,嘴角有血流下来。
开始了一段对话:
“重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柳青。”支持者命令。
“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柳青说。
又一番拳头和脚踢。
“重报———”
“正在接受审查的……”
柳青被打倒了。
这是力量严重失衡的对抗。一个年过五十体重仅有七十斤的作家柳青,面对一帮身强体壮的中年和青年汉子,况且是在狂飙正猛的“文革”风暴之中。然而,无论这些挟裹着“文革”风暴的身强体壮的汉子们如何吼叫,乃至轮番拳脚相向,那个身矮瘦弱的作家柳青说出的话语,他以洪亮的嗓音一字一板口齿清晰地说话时的沉静和自信,也形成十分悬殊的无法构成抗衡的对比。
又一番语言较量展开,“文革”通用的名词叫做“拼刺刀”:
“你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
“我是实事求是。”
“你必须交待你的罪行。”
“从入党那天起到现在,我不敢保证不做错事不说错话不无缺点,我敢保证做到实事求是不说假话。”
“你刚才一直在说假话!”
“我一生都没说过假话。”
“你还在狡辩!重报———三反分子柳青!”
“实事求是不是狡辩。我要是说假话,就是自己打断自己的脊梁。”
再一番拳脚,柳青就不说话了。
……
柳青听到**声打鼾,是从这屋子*东头的墙根下响起来的。从不时响起的出气声的轻重,柳青能判断出来哪种呼吸声是进入睡梦者发出的,哪种呼吸声是正在痛苦不堪的清醒者佯装睡着了的声息。他还得等待。等待里的心境是死样的平静,却浮出马葳的眼睛———这双熟悉的眼睛,瞅着他陪着他从京华首都回到西安,再相跟到蛤蟆滩南沿的庙院里,那是世界上*可依赖的美丽的眼睛,虽然也有不高兴的神光流泻的时候,却不影响依赖和美丽。就在他在台上为“自报”自己是什么的对抗中,在他**次挨打之后重新站定的时候,看见站在台下的马葳的眼睛,那种惊愕那种痛切的神光,像是一种凝固的冰雕,这是相伴相依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眼神。柳青第二次第三次挨打之后再去搜寻那冰雕似的眼神,却只看见亲爱的马葳低垂着的黑发,她没有力量看他了。那一刻,他心里泛起一缕庆幸的欣慰,低头不看是*好的选择,可以减轻折磨。现在,柳青眼前就浮出那双惊愕不堪痛切不堪而凝固为冰雕似的眼睛。
他在心里沉吟,亲爱的马葳啊!你肯定不知道你惊愕恐惧和恨起来的眼睛是怎样感动老夫的心啊!
“我放不了‘卫星’。别人用水笔写字写得快,能放;我写字跟刻字工一样慢,放不了;我给你实事求是汇报,刻字比不得写字快嘛。”
柳青对找他说话的领导说。
柳青坐在领导对面。这是西安南郊的一个别墅式的高级宾馆。四十年代由驻扎西安的国军军长胡宗南修建,接待党政要员的场合,解放后变为开会和休养的招待所了。这里刚刚召开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会,是文艺界知名的写家演家唱家弹奏家耍(魔术)家放“卫星”的大会。中国在一九五八年掀起的大跃进高潮里又兴起放“卫星”,*大的“卫星”是亩产小麦五十万斤,报纸上还配发着一个站立在麦穗上的男孩的照片,随之便潮涌着各行各业争相放出的吓死人的大“卫星”。文艺界不甘落后,各路名家名手聚着气铆着劲到这个招待所放“卫星”来了。柳青不仅不放“卫星”,甚至一言不发。在这样热烈的气氛里,坐着这样一位冰冷着脸色的人,弱智的人都会产生对于大跃进的态度问题的敏感,更不要说这些文学艺术界的人精了。会后,领导就找柳青来谈话。柳青坐下后就解释自己放不了“卫星”的原因。
“可是……你想没想到你不发言的负面影响?”
“实事求是。我只能实事求是。我放不了重量大的‘卫星’。我不能对党说假话说我能放。”
谈话停止了。气氛虽有点滞闷,却不紧张。这位领导和柳青既是同志战友,也是朋友,早在延安革命战争年代就熟悉了,他们当时都是年轻人。他现在是省上的重要领导,柳青是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友谊却不因年岁递增工作性质的差别而改变。或者说,领导叫他来坐坐来谈话,本质用意是替他担着一份心,须知对于刚刚兴起的大跃进运动的态度,往往决定一切职业者的命运,越知名越能干的人越是这样。这几乎已成为稍有政治意识的人的生存常识。柳青能感知领导和朋友的好心用意,又重复一遍:“我是作家,又是党员,我必须对党实事求是地发言。”
“你按你的实际情况,能放多大个‘卫星’就放多大个。你总得表示一下态度嘛!”
柳青浅浅地笑笑。那笑首先给人感到真诚,也掩饰不住(或不作掩饰)内蕴的讥讽:“我到这种场合里整个被吓瓜了,脑子停止转动了。热火朝天……雄心壮志……一个比一个重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把我……吓得快要透不过气来。我正写的那个东西……相比之下……显得小得拿……拿不出手。我表个啥态嘛……没法子表……”
柳青所说的“显得小得拿不出手”的“那个东西”,就是长篇小说《创业史》,正在做*后一遍的修改和润色。
谈话始终断断续续。这会儿又断了。领导的心里是有点复杂,也有点难言之隐。他不仅情感上喜欢柳青,更敬重柳青,敬重他已有的创作成就,更敬重他的人品人格。隐而难言正在这里,在铺天盖地的大跃进的响锣密鼓声中,瞪着两只黑亮透壁的眼睛死盯着别人高声大调表决心放“卫星”,紧闭着一绺黑胡须的嘴唇一言不发的柳青,他首先担心“政治态度”的负面影响和伤害。他和柳青交谈,就是出于战友和朋友的关爱,身居政坛要职的他,习惯性敏感“表态”的特殊意味。他希望柳青避免不必要的负面损害,明天还要继续放“卫星”,还来得及弥补。他已经把话说到这样清楚无误的程度,柳青却仍然在解释他的主意。领导吸起烟来,瞅着柳青一眼,又避开了,漫无目的地眯着眼,沉浸在飘绕的烟雾中。
领导再瞅着柳青的时候,突然睁大眼睛,紧紧盯着柳青的手,提高了声调,惊讶里蕴含着兄长般的关爱:“你的手指头咋成这样子?”
“破了。”柳青轻淡地回答。
“破了?削铅笔割了?”领导很急切。
“都不是……”
“皮肤病吗?”
“也不是。”
领导已经抓住柳青的左手,拉到自己的眼前,左手食指和中指的指甲盖周围,全是一片红肉,没有皮儿了,渗血仍然没有完全凝结,看来令人心头发瘆。领导逼住柳青的眼睛问:“那到底是咋弄的?”
“抠的。”柳青抽回手,平淡地说。
“你自己抠的?”
“别人谁能抠我的手嘛!”
“什么时候抠的?”
“今日个。”
“为什么抠?”
“……”
抠指甲是柳青一种习惯性的下意识动作。在听大报告或参加小讨论会的时候,听到那些令他感动和启迪的话语,抠指头的动作不会发生,因为他的手指捏着钢笔忙于记笔记;只有在听着套话废话狂话假话尤其是胡说的昏话时,他就瞪着黑眼珠抿嘴不语,搭在膝头或夹在两膝之间的手就抠起来了。别人很难发现,膝盖总是在桌子底下,他自己也是不知不觉地习惯性地抠着。不过,抠着也就抠着,并无多大肢体损伤,从来没有发生过把两个指头的皮儿抠光剥掉了这种惨相,他竟然浑然无觉。
这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上午是领导们一个一个报告或讲话,或代表单位表红心。他那时已经开始抠了,不过没有抠破皮。下午是各位诗人作家唱家演家弹奏家耍(魔术)家竞放“卫星”,有诗人说他在多短时间里要写出多少万行诗,有演家说观众喜欢他在舞台上翻跟头,他要把现在的十个跟头翻到八十个跟头……热烈地放“卫星”的大会暂告结束,柳青绷紧到麻木的神经一时还松弛不下来,站起身,离开座位时,才发现右手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抠得不见皮了,竟然没感觉到疼,竟然没有感觉到渗出的血滴把膝盖内侧的黑裤子浸湿了……
领导俯下身轻轻地问:“你是下午开会时抠的?”
柳青平静地说:“这是我的坏习惯,不知不觉就抠成这样子了。老也改不了。”
“噢……噢……噢……”领导转过身,独自微微点着晃着脑袋,走到窗前背对着柳青站住,只见冒烟,不闻话语,再不启发柳青表态了……
一年之后,饥饿便笼罩了蛤蟆滩。在忆苦思甜活动中被作为象征旧中国贫穷的稀糁子野菜树皮等食物,现在摆上了蛤蟆滩家家户户的饭桌。有人嚼着野菜树皮仍不改活泼的天性,哎呀!甭说亩产五十万斤粮,就按一亩地打一万斤,咱们该当干面锅盔操心吃得撑死呀!那么多的麦子跑到哪儿去咧?没有人敢在公开的或正经的场合追问高产的粮食到哪儿去了,更没有人敢追问亩产五十万斤的“卫星”放到天宇里去了,还是把家家户户的粮缸砸粉碎了!那些放过高产“卫星”的农民和决心把跟头从十个翻到八十个的名演家,现在全都不管他们放出的“卫星”跌到什么地方去了,早把心思集中到挖野菜和计算购粮票证上去了,然后依然热情不减地对新兴的口号表态去了。柳青却把心思集中到牛马身上了。无论碗里糁子多么稀,野菜树皮如何难以下咽,蛤蟆滩尚未发生完全属于饥饿而致死亡的人。牛马却大面积死亡,一个村子都难以幸免。在蛤蟆滩只有水车改成电动机械解放了牛马,成为机械化电气化的唯一标志,其余耕地拉车拉磨等重量级的农活儿仍依赖畜力。牛马死完了怎么办?道理不言自明,人都没有正经吃食了,牲畜早在人之前就省去了精料只有麦草了。柳青现在没有抠指头的下意识动作了,整天走村串寨,踏访那些有饲养抚弄牛马经验和绝招的老农民,开始推敲字句编写饲养牲畜的《三字经》,既要通俗———饲养员文化普遍偏低,又要琅琅上口易读易记———有些饲养员缺乏对文学的耐心。柳青把正在写作的《创业史》第二部放下来,牛马占据了他的思维中心……现在来不及追问谁怎么把粮缸砸破了,拯救人和牲畜的性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
作者简介
陈忠实,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陈忠实文集》(5卷),散文集《告别白鸽》等。短篇小说《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作品奖、《立身篇》获1980年《飞天》文学奖,中篇小说《康家小院》获上海首届《小说界》文学奖、《初夏》获1984年《当代》文学奖、《十八岁的哥哥》获1985年《长城》文学奖,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全国1990年——1991年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

快乐就是哈哈哈哈哈 插图纪念版
¥15.6¥52.0 -

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
¥17.5¥49.8 -

西南联大文学课
¥20.9¥58.0 -

十三邀4:“这样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人”(八品)
¥22.6¥58.0 -

她们
¥16.8¥46.8 -

事已至此先吃饭吧
¥28.0¥55.0 -

别怕!请允许一切发生
¥17.5¥49.8 -

战争与和平(上下)
¥32.9¥78.0 -

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41.5¥68.0 -

又得浮生一日闲
¥24.9¥49.8 -

这辈子 :1920-2020外婆回忆录
¥28.4¥45.0 -

平平仄仄平平仄
¥24.3¥68.0 -

宋词三百首鉴赏辞典(文通版)
¥25.2¥42.0 -

山月记
¥27.7¥39.0 -

树会记住很多事
¥9.2¥29.8 -

我生命中的那些人物
¥10.3¥20.0 -

我与地坛
¥20.2¥28.0 -

茶,汤和好天气
¥13.9¥28.0 -

花.猫.幽默家:老舍散文经典全集
¥13.5¥45.0 -

通往天竺之路
¥17.4¥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