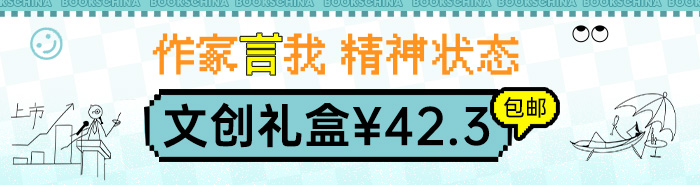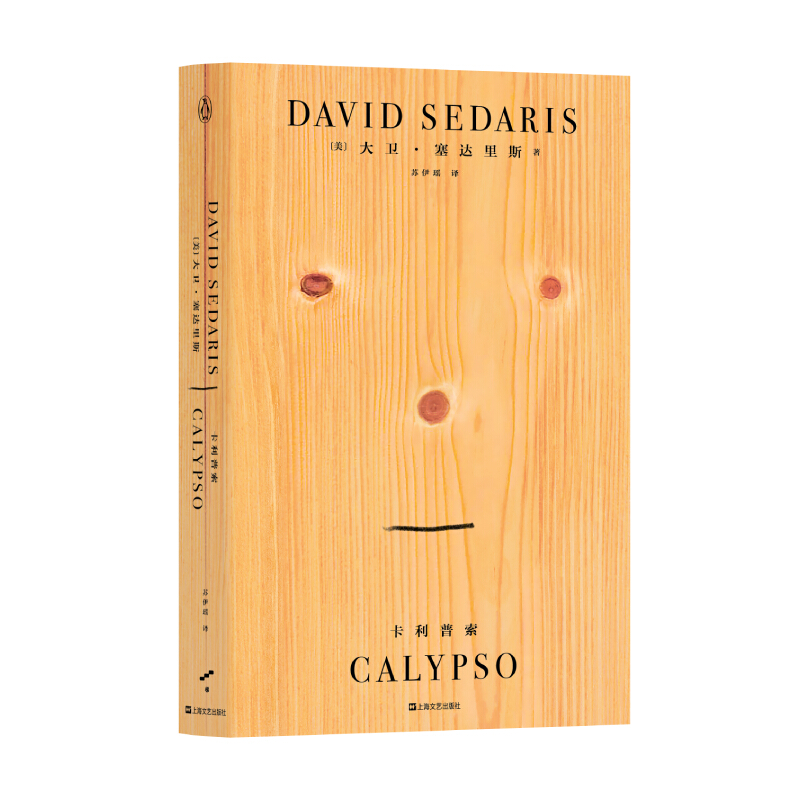
4.9分
卡利普索
豆瓣8.4分推荐!美国幽默作家塞达里斯兼具温暖与黑暗之作,直面中年危机和死亡的诸多细节。

温馨提示:5折以下图书主要为出版社尾货,大部分为全新(有塑封/无塑封),个别图书品相8-9成新、切口有划线标记、光盘等附件不全详细品相说明>>
- ISBN:9787532176076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243
- 出版时间:2020-07-01
- 条形码:9787532176076 ; 978-7-5321-7607-6
本书特色
★ 《卡利普素》是美国幽默作家塞达里斯迄今为止*黑暗同时又*温暖的书,也可能是他*好的作品。在这本书中,年逾六十的塞达里斯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对中年危机和死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别误会:这些故事是非常、非常搞笑的,可以让你笑到停不下来,就像家人才能做到的那样。
★ 这本书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之前作品中那个口齿伶俐的身影,还可以观察到一位年已七句的男人道出他更黑暗的秘密,以及对死亡的思考。大卫·塞达里斯写作的辉煌之处在于,他的精髓,他的气场,就像朵醉人的云,渗透到他的书中,迷住了我们,使他的逻辑成为我们的逻辑。
内容简介
如果你曾经在大卫·塞达里斯那些搞笑又厌世的故事中找到乐子,你可能会猜到这本书在讲什么。但你想的其实是错的。当塞达里斯在卡罗莱纳海岸买下一间海滨别墅的时候,他期待能在这里度过悠长又放松的假期,比如玩玩桌游或者在躺椅上做个日光浴。事实上在“域海”(他给这间度假别墅起的名字)的生活确实如他想象的一样悠闲,美中不足的是,他领悟到一个小烦恼:人真的很难彻底放空自己。
在这本书中,年逾六十的塞达里斯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对中年危机和死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别误会:这些故事是非常、非常搞笑的,可以让你笑到停不下来,就像家人才能做到的那样。塞达里斯的观察力从来没有这么犀利过,他逗笑读者的能力也是一如既往的无与伦比。但本书大部分的段子其实来源于一些郁闷的时刻,当你的身体正在背叛你自己,你意识到在你人生的篇章中,可期待的末来已经所剩无几,更多的是过去的回忆。如果你厌恶海滩,这对你来说就是一本极好的海滩读物。如果你讨厌闲聊,有兴趣听一个关于肿瘤的笑话,这本书你就一定要读。《卡利普素》是塞达里斯迄今为止*黑暗同时又*温暖的书,也可能是他*好的作品。
目录
陪伴
只剩我们五个了
小个子
走出去
家之隔
合身
利维坦
你英语真好
卡利普索
一次低调的求婚
无言
不驯
前任(们)
抱歉
装神弄鬼
我*近抑郁的一系列原因
你为什么不笑?
我还没倒下
灵魂世界
趁着你还在里面,帮我检查一下我的前列腺
科米备忘录
节选
只剩我们五个了 二〇一三年的五月下旬,在我*小的妹妹蒂凡尼五十岁生日的几周前,她自杀了。她生前住在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一个破落区域里的一幢破旧房子中。验尸官猜测,在她的门被撞开、尸体被发现的至少五天前,她就已经过世了。我当时在达拉斯机场,从一部 白色公用电话上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我飞往巴吞鲁日的飞机已经开始登机了,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就上了飞机。第二天早晨,我又上了另一架飞机,飞往亚特兰大,次日我又飞往了纳什维尔,这期间我的思绪一直围绕着我这日益缩小的家庭。我们都会对父母的去世有所准备,可谁会预料到兄弟姐妹的离开呢?我感觉我仿佛失去了一九六八年我弟弟出生时我所获得的身份——那个我一直乐在其中的兄长身份。
以前人们总是惊叹道:“六个孩子!你们可怜的家长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我长大的那个区域里,孩子众多的家庭不在少数,每两家的人数就多到都能配得上一块封地了,所以我也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直到我成年之后,身边的朋友也开始有了孩子。生一两个也就罢了,但一旦超过两个孩子我就受不了了。我和休在诺曼底认识的一对夫妇偶尔会带着三个熊孩子来家里吃晚饭,过几个小时他们离开以后,我会感觉全身心都受到了侵犯。
把这三个孩子乘以二,再减去有线电视的帮助,这就是我的父母当年要面对的局面。不过现在没有六个孩子了,只剩下了五个。“而且你不能跟别人说‘以前有六个’,”我对我姐姐丽萨说道:“那样会让别人感觉不舒服。”
还记得我几年前在加利福尼亚遇到过一对父子,我问他们:“家里还有别的孩子吗?” “有,”父亲答道,“有三个在世的,还有一个克洛伊,十八年前,她还没出生就离开我们了。”这太不公平了,我记着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毕竟,我是说,你让人怎么接这个话啊。
和大多数四十九岁的人比起来,甚至和大多数四十九个月大的孩子比起来,蒂凡尼的东西都少得可怜。但她依旧留了一份遗嘱。遗嘱中,她明确表示禁止我们——也就是她的家人——拥有她的遗体或是去参加她的追悼会。若是我们的母亲还在,她一定会说:“你们自己都好好琢磨琢磨吧。”
得到消息的几周后,我的妹妹艾米和一位朋友驱车前往萨默维尔,从蒂凡尼的房间中整理出了两箱子物品,其中有:家庭照片——大部分都被撕成了碎片,附近便利店里的意见填写表,笔记本,收据条。一张放在地上的床垫就是她的床,现在已经被拿走了,屋里还装上了一架巨大的工业通风机。艾米当时拍了几张房间里的照片,于是我们剩下的这几个人,或是单独,或是几个人一起,就开始对着照片寻找线索:一个缺了几斗抽屉的梳妆台上的纸盘子,写在墙上的一串电话号码,一堆色彩各异的拖把柄像香蒲一样被排列在一个涂成绿色的大桶里。
我妹妹自杀前的六个月,我曾组织大家一起去了北卡罗来纳州海岸附近的翡翠岛,一起租了一栋海景房度假。我们全家以前每年夏天都会去那里度假,但母亲去世后我们就再没去过了,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去,而是因为以前一直是我母亲张罗度假的事,更重要 的是,以前一直是她出钱。在我的弟妹凯西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栋拥有六间卧室和一个小游泳池的房子。我们一周的租期从六月八日开始,那天是周六,我们抵达时,一位女快递员正站在房子的汽车道上,拿着七磅重的海鲜,说是朋友们送来的慰问礼品。她把包裹递给我们时说:“里面还有卷心菜沙拉呢。”
过去,每当我们家在外面租住度假小屋时,我和姐妹们会像小狗聚在食物周围那样兴奋地围在门前。爸爸一打开门,我们就会立马冲进房子占领房间。我总是会挑面朝大海的那间*大的卧室,而每次我开始拆行李时,我的父母就会走进来告诉我这间房是他们的。我爸会说:“你小子以为你是谁?”然后,他们两个就会住进来,而我总会被打发到所谓的“女仆房”。这类房间永远都在一层,基本上就是一间阴冷潮湿的简易房,紧挨着停车的地方。房间里也没有能上到二楼的楼梯,导致我每次都得从外面绕到正门,常常像一名乞求进屋的乞丐一样敲响房子锁住的大门。我的姐妹们会问:“你想干吗?”
“我想进屋。”
“真有趣,”丽萨会对其他几人说道,她是我们中年龄*大的,其他几个会像信徒一样围在她身边,“你们听见了吗?像是有什么在哀号。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呢?一只寄居蟹?一只小海参?”通常情况下,我们六个孩子中的等级划分是*大的三个对*小的三个。丽萨、格蕾琴和我会像仆人一样使唤另外三个,十分管用。但一来到海边,一切就变了,变成了楼上对阵楼下,也就是所有人对我一个。
但这次不同了,因为是我出钱,我可以选择*好的那间卧室。艾米住在了我隔壁,我的弟弟保罗、他的妻子和他们十岁的女儿麦迪住在了艾米的隔壁。能看见大海的就只有这三间。其他人比我们来得晚,就只能在剩下的几间里挑。丽萨的房间和我爸的房间都面 朝街道,格蕾琴的房间也是,而且她的房间是为残疾人设计的。房顶上吊着电动滑轮装置,为的是帮助穿着特殊装备的瘫痪病人上下床。
不同于我们小时候住的度假小屋,这栋房子没有女仆房。因为这片社区里的房子都更新也更豪华一些。传统的海岛房都是脱离地面、由支柱支撑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岛房会将底下的空间也填满。人们给这些房子都取了海滩风的名字、涂上了海滩风的颜色, 但大多数建于一九九六年弗兰飓风之后的房子都有三层高,而且看起来几乎和乡村别墅差不多了。我们这栋房子很大、通风很好,厨房的餐桌能坐下十二个人,而且拥有不是一台而是两台洗碗机。房子里挂的装饰画也都是和大海有关的:海景和灯塔,每幅画的天空中都有几只V形的简笔海鸥。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幅刺绣写道:老开贝工不死,只是凋零。旁边的圆形时钟上,所有的数字都堆在底部无法辨认,好像这些数字没被粘上似的,数字的上方印着:管他呢?
从此以后每当有人问时间,我们都会这么回答:
管他呢?
我们来到海边的前一天,之前格蕾琴提交的蒂凡尼的讣告登上了《罗利新闻观察报》,讣告中称蒂凡尼于家中平静安详地离开人世,这让她听起来好像已经很老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房子似的。但你还能怎么说呢?有些人在报纸的网站上回复了这条讣告,其中有个 人说,他在萨默维尔的一家音像店工作,蒂凡尼生前经常光顾那里。有一次他的眼镜碎了,蒂凡尼就又给了他一副,是她在别人的垃圾桶里翻找美术用品的时候找到的。他说她还给了他一本六十年代的《花花公子》杂志,其中有一幅横跨两个版面的照片页,标题 为“翘臀动物园”。
这让我们大开眼界,因为我们并不是很了解我们的这位姐妹。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曾经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选择远离家庭,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塞达里斯家的一员”的角色中跳出来,成为一个个独立、独特的“塞达里斯”。然而,蒂凡尼从始至终都在远离她的家庭,她也许会答应圣诞节回家过,但到了*后关头她总会有一个借口:她错过了飞机、她必须加班,等等。就连我们的夏日家庭聚会也是如此。我总会说:“我们其他人可都回来了。”我心里清楚这么说很像一个老年人在说教,故意让别人产生愧疚感。
她不回来的话,我们都会很失望,但原因不同。即使你当下和蒂凡尼在闹别扭,你也不能否认她的种种行为很引人注意——她戏剧化的出场方式、她一流的怼人功力,以及她离开后一定会留下的一片混乱和狼藉。她前一天还在扔盘子砸你,第二天她就能拿盘子 的碎片拼出个马赛克装饰物。当她和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产生矛盾后,她会立马和另一个结成同盟。她从没在任何时候跟所有人都合得来过,但她总会和我们中的一个保持联系。在她生命的*后阶段,那个人是丽萨,但在此之前我们都曾成为过她的同盟。
她*后一次和我们一起在翡翠岛度假是一九八六年。“但就连那次,她都提前三天就走了。”格蕾琴回忆着。
小时候,我们在海边的主要活动是游泳,到了青少年阶段,我们全身心投入到了美黑事业中。当人们躺在沙滩上沐浴阳光恍惚出神时,总会产生一种特有的聊天方式和话题,而我对这样的聊天一直尤为喜爱。在我们*近这次旅行的**个下午,我们就在沙滩上铺好了我们小时候用的床单,一个挨一个躺了上去,互相交流有关蒂凡尼的故事。
“还记得那次她在军事基地过的万圣节吗?”
“还有她眼眶淤青出现在老爸的生日派对上那次。”
轮到我时,我开始道:“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她在一个派对上认识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一直在聊关于脸部伤疤的事情,她觉得如果脸上有疤真是太糟糕了。然后蒂凡尼就说:‘我脸上就有一个小疤痕,我没觉得它有多糟糕。’”
“‘是这样,’这个姑娘说,‘如果你长得好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它糟糕了。’”
艾米笑着翻了个身,趴在单子上说:“噢,太绝了!”
我重新整了整我用来当枕头的毛巾,说道:“可不是吗?”如果换成别人,这个故事可能会有点伤人,但对蒂凡尼来说,美貌从来不是问题,尤其在她二三十岁的时候,多少男人全都拜倒在了她的裙下。
“有意思,”我说,“但我不记得她脸上有过伤疤。”
那天我在阳光下待得太久了,晒伤了额头。后来几天,我基本就没怎么再见过沙滩巾了。我偶尔也会在沙滩上出现一下,比如游完泳以后晒晒干,但我每天的主要活动变成了骑行,沿着海岸线来来回回,边骑边思考。我们其余几个兄弟姐妹天生就很合得来,但和蒂凡尼相处总是像工作一样累。通常情况下,我和她在争吵过后总能和解,但我们俩*后一次吵架之后,我真的累了,到她去世为止,我们已经八年没有说过话了。这八年来,我经常会来萨默维尔附近,我也想过要不要联系她,但我从来没有,尽管我爸很希望我能这么做。这期间,我爸和丽萨会跟我汇报:蒂凡尼没有公寓可住了,她残疾了,她住进了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帮她找的房间。也许蒂凡尼和她的朋友们更能谈得来,但我们作为她的家人,只能得到关于她的零散消息。与其说她在和我们聊天,不如说是她在单方面地输出,她会将大段大段的信息量直接输入给你,这些信息时而搞笑,时而锐利,而且经常前后矛盾,让你完全无法联系上下文。在我们还有联系的时候,每当我走进屋, 听见休在电话上讲:“嗯……嗯……嗯……”,我就知道电话那头一 定是她。
除了从蒂凡尼在萨默维尔的家里整理出的两箱东西以外,艾米还把她初三时候的校刊年鉴拿回来了,以下是蒂凡尼收到的同学留言中的一条,这位同学还在蒂凡尼的名字旁边画了一片大麻叶:
作者简介
大卫·塞达里斯是美国著名幽默作家及电台撰稿人,曾获格莱美奖提名。他于1992年因NPR播出他的作品《桑塔兰日记》而声名鹊起。1994年,他出版了**本散文和短篇小说集《桶热》。他后来的四本散文集《裸》、《冰上假期)、《我说漂亮的一天》、《为家人穿上灯芯绒和牛仔布》和《被火焰吞噬》都成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包含本书在内,他已经出版了17部作品,销售总计1200万册。塞达里斯的默大多是自传性的,满是自嘲,经常涉及他的家庭生活。
-

她们
¥15.4¥46.8 -

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
¥20.0¥49.8 -

献给爱与子宫的花束
¥32.6¥59.0 -

十三邀4:“这样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人”(八品)
¥32.1¥58.0 -

读人生这本大书
¥8.3¥26.0 -

我是一只骆驼
¥10.2¥32.0 -

快乐就是哈哈哈哈哈 插图纪念版
¥21.1¥52.0 -

山月记
¥16.8¥39.0 -

雪国
¥23.8¥43.0 -

生活如此多娇(九品)
¥18.2¥48.0 -

唇间的美色
¥30.6¥65.0 -

晚明小品名篇译注
¥10.2¥32.0 -

行者无疆
¥20.6¥42.0 -

中国小说史略
¥11.2¥35.0 -

夏日走过山间
¥9.6¥30.0 -

陆小曼诗:文:画
¥13.5¥45.0 -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16.8¥39.0 -

战争与和平(上下)
¥25.0¥78.0 -

泰戈尔经典诗集
¥8.4¥28.0 -

十三邀2:偶像是生意,是符号,是忍辱负重(八品)
¥23.4¥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