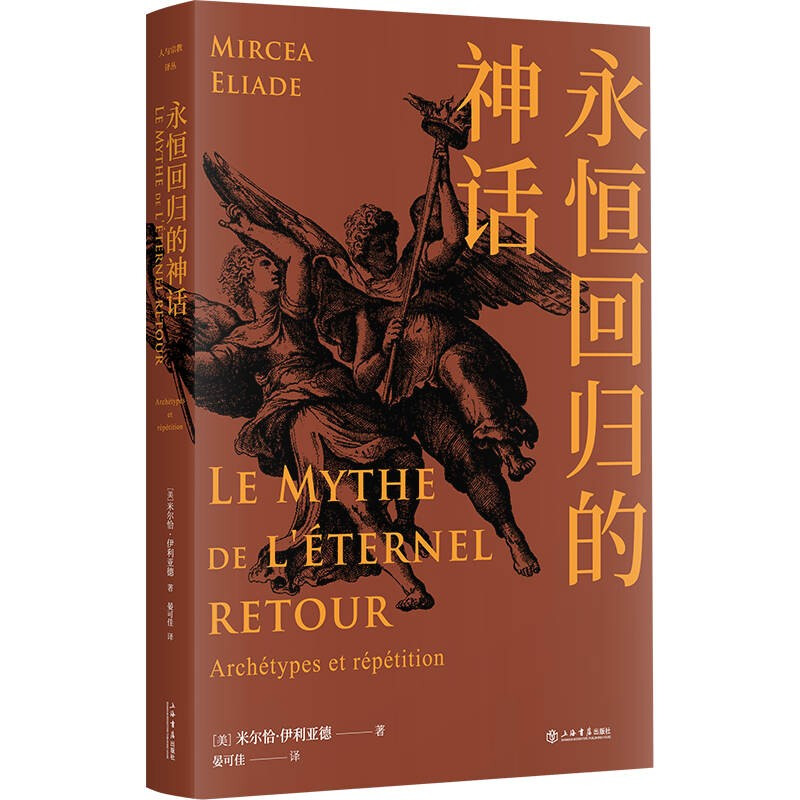- ISBN:9787545820614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155
- 出版时间:2022-03-01
- 条形码:9787545820614 ; 978-7-5458-2061-4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大众·西方宗教历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神话学与宗教学的经典 ·世界著名宗教史学权威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学理论的入门书籍 ·简体中文首版 人的苦难来自何处? 是自然降下的灾厄,必然遭遇的死亡,还是一望无尽的历史? 人如何能超越苦难? 回归神话时代,信仰某种宗教,还是为预设中的美好将来而自我超越? 本书可以命名为《宇宙与历史》,它直指古代社会人类对自身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想象。古人相信自己永恒地与整个大宇宙和宇宙节律不可分割。 本书又可命名为《历史哲学导论》,传统社会的古人与西方现代社会的人类,有着怎样不同的时间观和历史观? 以哲学解读神话与宗教,为现代人的困境提供某种精神方案。
内容简介
本书以传统社会的古人和被打上犹太﹣基督教烙印的现代人对自我存在的不同认识入手,参考了数量惊人的古代文化习俗与学术研究著作,展现原始宗教文化的宗教表达和活动,分析理解其背后的哲学观念。伊利亚德认为,永恒回归的神话及永恒回归的模式,是一切宗教、仪式和神话的一个基本的主体和模式,是初民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一切循环变异现象的神话史概括和总结。理解“永恒回归”模式,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人类存在位置的想象,也有助于为现代人摆脱身处历史时间的困境提供某种精神方案。
目录
前言
**章 原型与重复
问题
疆域、神庙与城市的天界原型
“中心”的象征系统
宇宙诞生的重复
仪式的神圣范本
“世俗”行为的原型
神话和历史
第二章 时间的更新
“年”,新年,宇宙诞生
创造世界的周期性
时间的连续更新
第三章 “不幸”与“历史”
苦难是一种“常态”
被视为一种神显的历史
宇宙循环和历史
命运与历史
第四章 “历史之恐怖”
“永恒回归”神话的残留
历史决定论的困境
自由与历史
绝望还是信仰
参考书目
节选
苦难是一种“常态” 我们在本章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人的生命以及“历史的存在”。正如我们所证明的那样,古人总是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反对历史,将其视为一连串不可逆的、不可预测的、仅具有自发价值的事件。他拒绝接受历史,拒绝赋予历史之为历史的价值——尽管如此,又总是不能将其驱除;例如,他无力抵抗每一种社会结构必然发生的自然灾害、兵荒马乱、社会不公,以及个人的不幸等等。因此,我们有兴趣了解古人如何忍受“历史”;亦即如何忍受降临到每一个人与每一个集体中的灾难、不幸和“苦难”。 对于从属于传统文化中的人而言,“生活”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意味着要与超人间的范本相符合、与原型相一致。因此,生活就意味着要生活在“真实”的中心——正如我**章所特别强调的那样——除了原型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是真正真实的。与原型相一致的生活,相当于尊重“律法”,因为律法便是太初的神显,是彼时启示的生存规范,是由神或神话中的存在所揭示的。正如我们所见,如果远古之人通过重复范式性的行为、借助周期性的消弭时间,那么他就可以和宇宙的节律和谐相处;甚至我们可以说,他融入到了这些节律之中(我们只需要记得,日、夜和四季、月亮的盈亏、夏至和冬至等对他有多么“真实”)。 在这样的生存架构之下,“苦难”和“痛苦”究竟所指为何?当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经历,因为无可避免,所以只能“忍受”,就像忍受例如恶劣的气候一样。不管其本质或表因如何,他所受的苦难总有意义;它和某个原型相对应,即使并不总是如此,但至少和他并不反感的秩序相对应。我们已经说过,与古老的地中海伦理体系相比,基督教的一个优越之处就在于它赋予苦难以某种价值:它将痛苦从负面的状况转化成具有“积极的”灵性内涵的经验。这个主张是成立的,因为它将价值赋予苦难,甚至在痛苦中找出有益的特性。但是,即使前基督教的人不刻意寻求苦难,不会赋予其价值(只是极少数例外),也不将把它当成具有净化与提升灵性的工具,他们从来不认为苦难毫无意义。当然,我们所说的苦难是指作为历史事实的一个事件,或由于自然灾害(洪水、干旱、暴风)、人为侵犯(纵火、奴役、屈辱)、社会不公等所带来的苦难。 如果说这些苦难可以忍受的,那是因为它的发生,既非平白无故也非随心所欲。举例说明是多余的;它们随处可见。原始人看见赤地千里、一片荒芜,牛因瘟疫被扑杀,孩子生病,自己又高烧不止,打猎总是背运,他知道这些事件并非偶然,而是受到某些巫术或者魔鬼的影响,祭司或巫师拥有对付它们的兵器。因此,面对灾害,原始人和整个社团都会这样去做:他找来巫师消除巫术的魔咒,或找祭司祈求诸神保佑。如果祭司或巫师的干预没有结果,那么,利益相关的团体就会想到在平时几乎完全忘记的至上神,供上祭品,向他祈祷,“天神啊,不要带走我的孩子;他还年轻,”火地岛的游牧部落赛尔克南人(Selk’nam)如此祈祷。霍屯督人(Hottentots)则哭泣道:“祖尼-哥安(Tsuni-Goam)啊,只有你知道我是无罪的!”暴风雨来了,塞芒族(Semang)俾格米人用竹刀划伤他们的小牛,一边将血洒向四面八方,一边喊:“塔派登(Ta Pedn)啊!我不再冥顽不灵,我要赎罪。请接受我的亏欠吧,我要赎罪!”[ 亦可参见拙著《宗教史论》,第2章,第53页以下的例子。]此外,顺便提一下,我们在《宗教史论》里详细探讨过一个观点:在所谓原始人的崇拜仪式里,只有到了*后关头,在祈求诸神、妖怪、巫师来消除“苦难”(旱魃、霖雨、灾难、疾病等)而没有结果后,作为*后的解救办法,至上之天神才会出手干预。只有到了这种地步,塞芒族俾格米人才会忏悔他们所犯下的罪过,这种风俗,作为解脱痛苦的*后手段,我们在其他民族那里也时有所闻。 与此同时,应对“苦难”的巫术-宗教的每一个时刻,都清楚地表明苦难的意义:苦难来自敌人的巫术活动、破坏禁忌、闯入禁地、神灵发怒,或者——如果所有假设均不成立,那么——苦难就也许就来自至上神的旨意或愤怒。原始人——正如我们下文就要看到的那样,其实不单单是原始人——无法想象一种毫无缘由的“苦难”;[ 我们再次强调,从反历史的民族或者阶级的观点来看,“苦难”等同于“历史”。甚至时至今日也可在欧洲的农业文明中看到这个等号。]它总是缘起于个人的错误(如果他相信那是宗教上的错误)、或邻人的恶意(如果巫师发现了其中的巫术活动);“苦难”的背后,总有某种过失,至少有某种原因,可以从那个被遗忘的至上神的意志中分辨出来,*后还是被迫向祂求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苦难总是变得可以理解,因而也是可以忍受的。原始人用各种巫术-宗教的手段和“苦难”作斗争——但他在道德上忍受苦难,因为它并不荒谬。“苦难”的关键时刻是在它出现之际;苦难只有在找不到原因时才令人烦恼。一旦巫师或祭司发现引起儿童或动物夭亡、旱灾不去、淫雨不断或猎物消失的原因,“苦难”就变得可以忍受了;苦难自有其原因、意义,因此苦难可以纳入一个体系而得到解释。 我们前文关于原始人的讨论,几乎完全适用于所有远古文化的人类。自然,解释受苦受难的神话母题各有不同,但解释本身随处可见。大体而言,苦难被视为偏离“规范”的后果。毋庸赘言,此规范随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各不相同。但在我们看来,关键在于,在远古文明的架构里,受苦受难在任何地方都不是被视为“盲目的”、毫无意义的。 印度人很早就精心构造了一套宇宙的因果律,“业”的概念,以解释实际发生的事件与个体生命的苦难;同时用以说明轮回的必然性。从业的观点着眼,苦难不仅有意义,而且有积极的价值。个人今生的苦难不但是应当忍受的——因为它事实上是前生所犯罪恶与过失的必然结果——而且应当是乐于接受的,因为只有通过此种方式,才能消解并清偿压在一部分个人身上并决定他来生之轮回的业债。依据印度人的构想,人生下来时即带着债务,但他还拥有结下更新债务的自由。人的存在就是一长串的欠债与还债,只是其间的账目并不总是清楚的。一个人只要不是完全缺乏智力,就会冷静地忍受降临在他身上的苦难、悲伤、打击,以及种种不公,因为这些都是偿还其某个前生尚未清偿的债务。自然,印度人很早就寻找到了某种途径,将自己从这种为业力法则所决定的无限的因果链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些解决方法,并不能抹杀苦难的意义;反而是强化了此种意义。和瑜伽思想一样,佛教也确立了一切皆苦的原则,并且提供了一套具体而彻底的方法,从一切人生赓续不断的苦难中得到解脱。然而,和瑜伽思想一样,佛教以及实际上印度各种解脱法门,对于痛苦乃是一种“常态”,从未有过片刻的怀疑。至于吠檀多派(Vedânta),则认为苦难只是“泡影”,因为整个世界就是泡影;人类受苦的经验以及世界本身都不是本体意义上的实在。除了唯物主义的顺世派(Lokāyata)和斫婆派(Chārvāka)——它们认为“灵魂”和“神”都不存在,避免痛苦、寻求快乐就是人给自己确立的惟一合乎理性的目标——以外,整个印度都认为,痛苦——不论其本质如何(宇宙的、心理的或历史的)都有明确的意义与功能。因为业力使任何世间事物都按照因果律而生灭。 即使远古时代的世界未曾提出像业力这样明确的概念,去解释痛苦的“常态”,我们处处却可以发现一种相同的倾向,即赋予苦难与历史事件一种“常态化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并非要去讨论这种倾向的所有表现方式。我们几乎在所有地方都会遇到这样(主宰着原始人的)古老的观念,将苦难归结于某种神意,或者是其直接干预所致,或者是允许其他鬼神的力量介入导致苦难的产生。欠收、干旱、敌人劫掠城市、丧失自由或生命、各种灾害(流行病、地震等)——均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用超越的或神的经纶来解释或说明。是不是被征服的城市神灵的神力不及获胜的军队的神灵;是不是整个社群,或者只是某个家庭,在某个神灵的仪式上犯了过失;是不是符咒、恶魔、疏忽或诅咒在起作用了——个人或集体的苦难总有理由。有了理由,就能忍受。 不仅如此。在地中海-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的苦难很早就和神的苦难连在一起。之所以如此,是要赋予苦难以一个原型,而这个原型再使这些苦难得以实在化、“常态化”。在整个古代东方世界,到处可见反映坦木兹受苦、死亡和复活神话的雕像和其他各种形象,此种场景的遗迹甚至留存到后基督教时代的诺斯替派。在此我们只想提醒诸位,坦木兹的受苦和复活为其他神灵(如马尔杜克)的受苦提供了范本,而且无疑地,每年还为国王所仿效(因而也是重复)。民众的哀恸和喜悦,以纪念坦木兹或任何其他宇宙-农业神之受苦、死亡和复活,深深印在了东方人的意识里,这个事实被大大地低估了。而这个事实既和死后复活的预感有关,也和坦木兹受苦带给每个人的安慰有关。只要人们还记得坦木兹的故事,任何苦难就都可以忍受了。 这样的神话故事提醒众人,苦难不是*后的结局;死亡之后便是复活;*后的胜利可以消弭和超越每一次失败。这些神话与前一章所述月亮的神话显然具有相似之处。在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坦木兹或任何其他相同的原型解释了“义人”所受的苦难——换言之,苦难变得可以忍受了。神——以及常常“义人”、“无辜之人”——并无过犯却饱受苦难。他受尽羞辱,遭到鞭笞,鲜血淋漓、囚禁在“深坑”,也就是地狱里面。在这深坑里,大女神(Great Goddess,在后世的诺斯替派文献,又称“信使”)前来探访、鼓励他,使他复活。此种关于神灵受苦受难的具有慰籍作用的神话,过了很久才从东方诸民族的意识里淡出。例如,威登格伦教授(Widengren)相信,它还存在于摩尼教或曼德教的原型里面,[ 参见Geo Widengren,King and Soviour,II(乌普萨拉,1947年)。]当然,在希腊-东方的文化发生融合的时代,它多少必然会发生变化,产生若干新的价值。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个神话场景表现出一种极为古老的结构,它即使不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至少也是在形态学上起源于月亮神话,而月亮神话的古老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已经看到,月亮神话对全部生命提出了一种乐观的观点:万物循环往复;死亡必然伴随复活,必然伴随新的创造。坦木兹的范式性神话(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诸神亦然)亦认同这样一种乐观主义:不仅个体的死亡可“得救”;他的苦难也同样可以。至少,和坦木兹神话一脉相承的诺斯替派、曼德教和摩尼教也说明这一点。这些派别认为:人本身必须承受和坦木兹同样的命运;跌入“深坑”、“给黑暗王子为奴”,被信使唤醒,带给他即将得救、获“解救”的福音。由于文献不足,我们不可将同样的结论沿用到坦木兹身上,但我们不妨相信,他的故事与人类的故事相差无几。因此,祭祀仪式获得巨大“成功”是和所谓的植物神不无关联的。
作者简介
米尔恰·伊利亚德(1907—1986),世界著名宗教史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伊利亚德早年在文学创作上颇有声名,其罗马尼亚语小说《孟加拉之夜》《没有青春的青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二战结束后至1955年,伊利亚德一直居住在法国巴黎,这期间他的宗教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以法文形式出版了一系列宗教著作:《永恒回归的神话》《神圣与世俗》《宗教思想史》《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瑜伽:不死与自由》《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术》等。这系列著作几乎涵盖了20世纪所有宗教的重要研究领域,使他成为一名蜚声国际学术界的宗教史家。1956年伊利亚德到美国任芝加哥大学宗教系主任和教授等职,与同事将芝加哥神学院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宗教史研究中心。
-

哲学家的狗:一本让人捧腹大笑的超萌醒脑哲学书
¥16.9¥49.8 -

生如蚁,美如神:怎样平凡而有诗意地过一生
¥19.6¥58.0 -

伦理学与经济学
¥8.2¥20.0 -

谈修养
¥7.0¥20.0 -

心灵的平和之美
¥15.4¥45.0 -

中华圣贤讲什么
¥18.2¥26.0 -

理想国-精装典藏版
¥21.4¥68.0 -

生命的所有可能
¥18.7¥52.0 -

新事论
¥8.5¥22.0 -

论好运(八品)
¥16.4¥48.0 -

一种人生观
¥19.1¥42.0 -

中国哲学小史
¥20.6¥49.8 -

道家哲学研究-(附录三种)
¥5.2¥18.0 -

脑海中的声音:自我对话的历史与科学
¥15.7¥49.0 -

《老子》注评
¥4.8¥11.0 -

生育对话录
¥14.3¥39.0 -

王阳明心学的智慧
¥10.0¥36.0 -

西南联大哲学课
¥18.4¥58.0 -

孟子通讲
¥20.1¥59.8 -

谈美
¥5.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