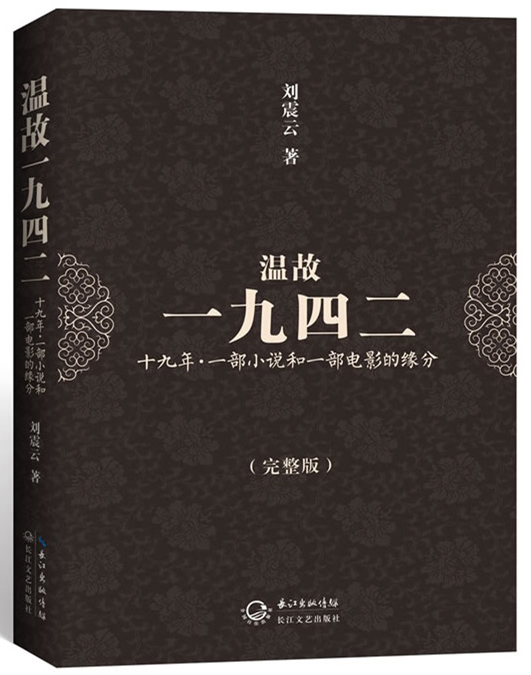
4.4分
包邮温故一九四二

温馨提示:5折以下图书主要为出版社尾货,大部分为全新(有塑封/无塑封),个别图书品相8-9成新、切口有划线标记、光盘等附件不全详细品相说明>>
屁股决定脑袋
随手买的这本书,也不知道会讲什么。读了后才知道原来是大旱饥荒,记得之前看的一本《平原上的歌谣》也是这样的故事。自古以来富庶丰饶的中原大地,遇到灾难也是首当其冲的啊。电影没有看过,原以为只是刘震云的小说,没想到还有剧本,从零散的采访到行云流水的故事原来是这番推导。蒋所关心的事谁大谁小,不论是谁也是屁股决定脑袋啊。
- ISBN:9787535452481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208
- 出版时间:2012-12-01
- 条形码:9787535452481 ; 978-7-5354-5248-1
本书特色
《温故一九四二:从《温故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二》(完整版)》是作者刘震云和导演冯小刚唯一独家授权的小说和电影故事完整版作品,也是首次面世的刘震云电影版《一九四二》。 刘震云的小说为调查体,简洁而不着一笔作者态度,却准确还原了1942年中国的大时代环境。极为苛刻却慧眼独具的王朔,对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不吝赞誉,力荐给冯小刚。冯小刚说:“我一口气看完,使我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从此“把一九四二烙在了心上……” 电影故事经19年打磨,数易其稿,炉火纯青。书中冯小刚长序为难得一见的“惊世之言”,详尽记述了《一九四二》问世的艰辛与坎坷,极具震撼力!
内容简介
《温故一九四二》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作家刘震云的首部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能不为人知的、关于饥饿的故事。
刘震云形象地说:1942年河南因旱灾饿死的民众,相当于在那里建了三座奥斯维辛!冯小刚说:“二战时,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在1942年,中国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刘震云为此写了一本书,我在1993年看到,非常震撼。”
当年旱灾、蝗灾使粮食颗粒无收,哀鸿遍野,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刘震云为重温那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小说,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记述者。
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19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电影故事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电影故事比小说更直观,甚至更具文学性,电影中未拍或删掉的镜头在书中都予以保留。也由此看到刘震云获茅奖力作《一句顶一万句》前身的影子。
前言
不堪回首 天道酬勤(摘录)
冯小刚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的王朔还是小王,震云还是小刘,我还是小冯。我们仨同龄,五八年的,风华正茂。
一个夏天的午后,小王把小刘的《温故一九四二》交到我的手上。
小王说:推荐你看震云新写的一个中篇,调查体小说。
我一口气看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
这篇小说在我的心里开始发酵,逢人便说,念念不忘。
隔年,在南郊京丰宾馆一个扯淡的大会上,遇到震云,我提议把《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电影。那时我刚刚拍完根据震云小说《一地鸡毛》改编的电视剧,我还没有拍电影的经历。
震云的回答是:不急……容我再想想……
之后一晃几年过去。这期间,我和震云、王朔还有梁左成为莫逆,隔三岔五包上一顿饺子,凑几个凉菜,说上一夜的醉话。酒中也多有提及《温故》的事,但也都是虚聊,小刘没有实接过话茬。
时间走到2000年。新年的一个晚上,小刘来到我家。饺子就酒,几杯下肚,小刘郑重对小冯说:我今天来,是想把《温故一九四二》交给兄长,此事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今天我仍清楚记得震云那义无反顾的表情。天渐白时,我们喝光了家里所有的啤酒,那一夜小刘把《温故》托付给了小冯,也把一九四二烙在了我的心上。
2002年项目正式启动,那时我已与华谊兄弟签约,中军中磊横下一条心拿出三千万投拍《温故》。在当时,对于一部国产文艺片来说,这个预算就是一个接近于自杀的天文数字。
我们在北影的一间小平房里开了论证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它是部好小说,同时也一致认为它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专家们散去,小冯和小刘蹲在小屋外的树荫下,小刘问小冯:这事还做不做?我说:做。小刘说:人们习惯只做可能的事,但是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思不大,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义就不同了。小刘又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笨人;聪明的人写剧本知道找捷径,怕绕远怕做无用功,善于在宾馆里侃故事,刮头脑风暴;笨的人写剧本不知道抄近路,*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看似无用功,却能够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对小刘说:我们肯定不是聪明人,就走笨人的路吧。
接下来的三个月,小冯和小刘携小陆、老韵、益民还有孙浩,一行六人先后赴河南、陕西、山西,又赴重庆、开罗,行程万里。在路上,我们见到老东家一家,瞎鹿花枝一家,见到了东家的女儿星星,赶大车的长工栓柱,见到了八岁的留保和五岁的铃铛,见到了伙夫老马,见到意大利传教士托马斯?梅甘,他的中国徒弟安西满,也见到了委员长和那位让委员长头疼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见到了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李培基;见到了寒风中蓬头垢面的灾民,背井离乡一路向西的逃荒队伍,见到了他们悲惨的命运;更重要的,也意外地见到了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幽默。
半年后,震云捧着热腾腾带着油墨香味的剧本,用他的河南普通话给翘首以待的我们读了整整一个下午。
捋胳膊挽袖子,中军拍板,干!
剧本送去立项,不日被驳回。理由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
散了散了,下马,该干吗干吗去吧。
…… ……
目录
不堪回首 天道酬勤 冯小刚
小说:
温故一九四二
电影:
一九四二
节选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
“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
“没死的呢?”
姥娘:
“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
“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
“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
“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
“饿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
“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
“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
“大旱后起蚂蚱!”
我:
“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
“饿死许多人!”
我:
“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
“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为穷人辩护:
“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
“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
“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
“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
作者简介
刘震云,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县。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小说素以下笔辛辣和关注民生为特点。
曾创作长篇小说
《故乡天下黄花》
《故乡相处流传》
《故乡面和花朵》(四卷)
《一腔废话》
《手机》
《我叫刘跃进》
《一句顶一万句》
《我不是潘金莲》等;
中短篇小说
《塔铺》
《新兵连》
《单位》
《一地鸡毛》等。
《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

莫言的奇奇怪怪故事集
¥19.0¥59.9 -

悉达多
¥13.0¥28.0 -

死魂灵
¥14.0¥48.0 -

本森小姐的甲虫
¥15.9¥55.0 -

失去一切的人
¥16.6¥52.0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12.9¥39.8 -

罗生门
¥15.9¥36.0 -

面纱
¥16.9¥49.8 -

1984-插图珍藏版
¥9.9¥29.8 -

鼠疫
¥12.6¥38.8 -

2025读书月阅读盲盒——我独钟意命运角落的人
¥42.3¥168.0 -

我这一辈子
¥13.2¥38.0 -

重生
¥12.9¥39.8 -

2025读书月阅读盲盒——经常作案的朋友都知道
¥42.3¥168.0 -

烟与镜
¥15.4¥48.0 -

山海经
¥18.0¥68.0 -

未来的最后一年
¥16.9¥49.8 -

月亮与六便士
¥10.9¥38.0 -

我是猫
¥13.0¥46.0 -

守夜
¥20.4¥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