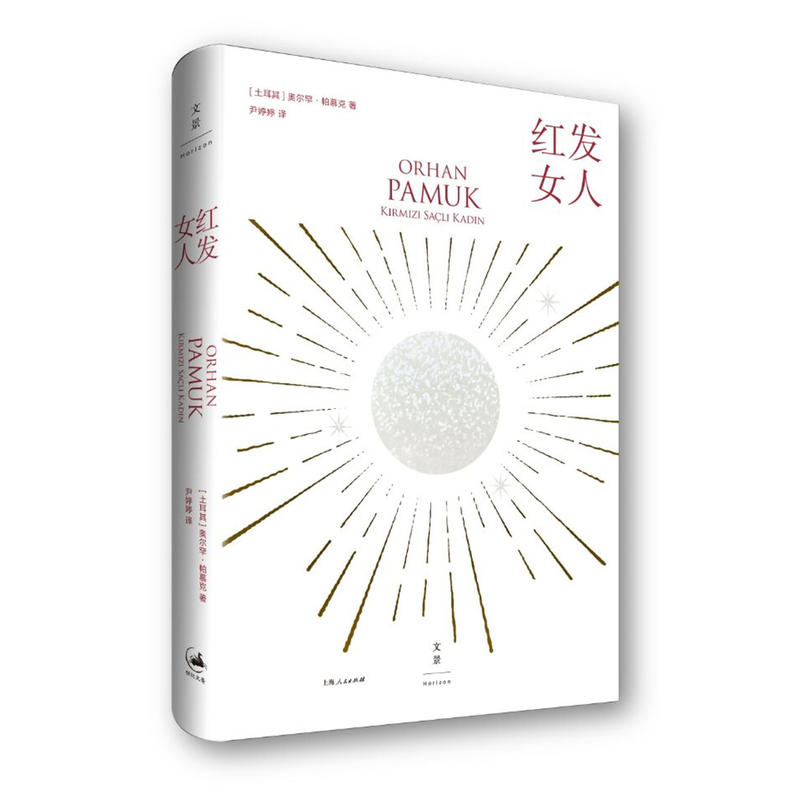
4.9分
包邮红发女人(带有尾货标记)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举重若轻之作,帕慕克首次尝试“写一部更短的小说”,尽管这个故事已经酝酿了三十年——它始于1988年夏天,帕慕克在住处附近遇到的一对情同父子的挖井人。

温馨提示:5折以下图书主要为出版社尾货,大部分为全新(有塑封/无塑封),个别图书品相8-9成新、切口有划线标记、光盘等附件不全详细品相说明>>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欧洲杰出的小说家。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文。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 ISBN:9787208150164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302
- 出版时间:2018-04-01
- 条形码:9787208150164 ; 978-7-208-15016-4
本书特色
封面或封底有特价贴纸,为出版社处理库存书标记。
十六岁的高中生杰姆在暑假来到伊斯坦布尔郊区的恩格然小镇,跟随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挖井。因为长期找不到水,劳作变得格外枯燥。不过,马哈茂德师傅和杰姆也渐渐变得像一对父子那样亲近。
就在这个夏天,一位红发女人短暂地出现在杰姆的生活中。因为一次意外事件,杰姆仓皇逃离小镇。在未来的三十年里,他不断地阅读和寻找两个古代传说。他发现,这些古老的故事仍然在神秘地牵引着自己的命运。
三十年后,杰姆已成为建筑公司老板,过上富足而平静的中年生活。他再度回到了恩格然,并发现了他试图忘记的一切……
内容简介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举重若轻之作,帕慕克首次尝试“写一部更短的小说”,尽管这个故事已经酝酿了三十年——它始于1988年夏天,帕慕克在住处附近遇到的一对情同父子的挖井人。
☆ 掘井取水的过程,也是向着记忆的幽暗深处一路挖掘的旅程。失去父亲、做了挖井学徒的少年杰姆,在多年以后渐渐变成一个衣食无忧的商人。他平静的中年生活之下,却埋藏着不为人知的过去。直到有一天,他试图遗忘的往事终于将他吞没。
☆ 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是宽容我们的一切,还是教会我们服从?或许,在尝试了所有的自由之后,我们只想重新寻找一个意义、一个中心,一个能对自己说“不”的人。
☆ 获2017年意大利兰佩杜萨国际文学奖。
目录
第二部
第三部
节选
A
三十几年前,也就是20 世纪80 年代上半期,我们在一座小城市演出。一晚,剧团和地方政治团体的一群人在一起吃吃喝喝,长桌的另一端是个跟我一样红头发的女人。一时间,所有的人都开始讨论起两个红发女人同坐一桌的巧合。他们问着诸如概率是几分之几,是否会带来好运,预示着什么的问题。
“我头发的颜色是天生的。”桌子那头的红发女人说,既像是抱歉,又带着得意,“你们看,就像天生红头发的人一样,我的脸上,胳膊上都有雀斑。我的肤色白,眼睛也是绿的。”
所有人转向我,看我如何作答。
“您头发的红色是天生的,而我的红色出于自己的决定。”我立刻回复道。
我并不总是这样对答如流,但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对您来说这是天赐禀赋,是与生俱来的命运,对我而言则是自主意识的选择。”
我没有继续下去,以免在座各位认为我傲慢自大。因为,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嘲讽和愚蠢地发笑。倘若不回答,沉默就将意味着我甘拜下风:“是的,我的头发是染的。”那样他们既会误解我的性格,还会认为我是个胸无大志的模仿者。
对我们这种红头发的后来者来说,头发的颜色意味着被选择的个性。一次染成红色后,我终生都致力于此。
二十五岁上下,我还是个现代的广场戏表演者,一个激愤但快乐的左派,而非从古老神话和传说故事中挖掘警世意义的舞台剧演员。持续三年的地下恋情,*终以年长我十岁的情人的离弃而终结。他是个有妇之夫,一个英俊的革命分子。然而我们在一起激昂地读书时,多么浪漫,多么幸福!事实上,我既生他的气,也理解他。因为我们的地下恋情曝光,组织里认识我们的每个人都对我们的事指手画脚。他们说这会引起妒忌,结果对大家都不好。与此同时,1980 年发生了军事政变。一些人转入地下,一些坐船去了希腊,又从那里逃往德国成为政治流亡者,一些进了监狱遭受酷刑。大我十岁的情人阿肯也在这一年回到了妻子和孩子的身边,回到他的药店。而我讨厌的图尔汗——因为他看上了我,还诋毁我爱的人——则了解我的痛苦,并且对我非常好。于是我们结婚了,认为这样对“革命者家园”来说也是好事。
不过跟另一个男人谈过恋爱这件事成为我丈夫的心结。他认为自己因此才会在年轻人中没有威信,但却无法指责我“轻浮”。他并非像我已婚的情人阿肯那样是个迅速坠入爱河又轻易忘却的人。因此,他开始难以装作若无其事。他想象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对他奚落挖苦。不久之后,他指责“革命者家园”的同伴不作为,跑去马拉蒂亚组织武装斗争。我就不讲他在那里试图唤醒的同胞们是如何揭发这个闹事者,以及我丈夫是如何被宪兵堵在溪边挨打的。
短短时间内,生命中这第二次重大失去让我对政治更加冷淡。有时想着,不如回自己的家,回到退休的省长父亲和母亲身边,却下不了决心。回家,就不得不承认失败,也不得不远离戏剧。找个能让我加入的剧团已非易事。与普遍观点相反,我想演戏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戏剧。
我留了下来,于是,正如奥斯曼时期赴前线与伊朗作战有去无回的骑士们的妻子们,没过多久我嫁给了图尔汗的弟弟。事实上,与图尔加伊结婚,鼓动他成立流动民间剧团是我的主意。就这样,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出乎预料地幸福。继两个失去的男人之后,图尔加伊的年轻、孩子气、牢靠似乎成为一种保障。冬天,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的左派协会的大厅,在无法称之为戏剧舞台的会议室里演出,夏天就去朋友邀请的镇子、度假城市、军队驻地和新建的车间及工厂周边支帐篷。在饭桌上同时出现我们两个红发女人,是这岁月的第三个年头。这之前的一年,我才把头发染成红色。
事实上,作出这个决定并非出于我身材高挑的考虑。“我想给头发彻底换个颜色。”那天,我对巴克尔柯伊的中年社区理发师说,但脑子里连颜色也没想好。
“您的头发是棕色,染黄色适合您。”
“把我的头发染成红色,”我临时起意,“这样会很好。”
我染了一种介于消防车的颜色和橙色之间的红色。非常醒目,不过包括我丈夫图尔加伊在内,身边没有一个人反对。或许他们想,这是为即将演出的一部新剧做准备。我还注意到,他们把红色头发诠释为我从接二连三的不幸感情中一路走来的结果。那时,他们对我很宽容:“她做什么都不为过。”
从他们的反应中,我渐渐明白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原版和模仿是土耳其人热衷的话题。自打酒桌上另一个红发女人傲慢的否定之后,我不再去理发店用人造染料,开始从市场亲手称重购买指甲草自己染发。这就是跟天生红发女人相遇的结果。
我特别留意来剧场帐篷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率真敏锐的年轻人和饱受孤独的士兵,对于他们的敏感和幻想诚挚地敞开心扉。他们比成年男人能更快区分颜色的色度,假与真,真情实意与胡话连篇。假使我没有用亲手调制的指甲草染料染我的头发,或许杰姆也不会发现我。
他注意到我,于是我也注意到他。我喜欢看他,因为他太像他的父亲。紧接着,我发现他迷上了我,还观察我们住的房间窗户。他很腼腆,我可能是被这一点所感动。不知羞耻的男人让我害怕。我们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人。无耻是能够传染的,因此在这个国家我时常感觉仿佛要窒息。大多数人希望你也能不知廉耻。杰姆斯文、腼腆。他来剧场看戏的那天,走在车站广场上,他一说出自己的身份,我就明白了他是谁。
我错愕不已,不过似乎潜意识里我早已知道他是谁。我从戏剧中学到,在生活中被当作偶然所忽略的东西其实都有某种意义。我的儿子和他父亲都想成为作家并非简单的偶然。三十年后,在这里,在恩格然,和我儿子的父亲相遇并非偶然。我的儿子也跟他父亲一样饱受没有父亲的痛苦并非偶然。我在戏剧舞台上哭泣多年后成为在生活中锥心痛哭的女人并非偶然。
1980 年军事政变后,我们的民间剧团也转变态度,为避免陷入麻烦,淡化了左翼色彩。为吸引人们进帐篷,我从《玛斯纳维》 [1],古老的苏非派故事和传说,《霍斯鲁与西琳》《凯莱姆与阿斯勒》 [2] 中截取感人场景和对话用作我的小段独白。不过我们取得的*大成功,是改编自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故事里热泪盈眶的老妇人的独白。这是为土耳其电影写悲情剧的一位剧作家老朋友的建议,他说:“不论何时都受欢迎而且抓人心。”
在模仿电视广告用来插科打诨的表演过后,那些惊叹于我舞动的肚皮、短裙和长腿从而振奋起精神,说着下流话,或立刻爱上我,或陷入性幻想的所有无耻的男人(甚至包括那些叫嚷着“打开,打开”的*肮脏的人在内),每当我在舞台上发出苏赫拉布的母亲塔赫米娜看到丈夫杀死儿子时的尖叫,顿时陷入一片深沉可怖的寂静。
就在此时,我先是幽咽地,紧接着开始撕心裂肺地恸哭。哭泣时,我能够感受到自己在人群中的力量,我为把自己全部生命奉献给表演感到幸福。舞台上我穿着开衩的红色长裙,戴着老式珠宝,腰上束着军用宽腰带,手腕上戴着那个年代的手链。当我在舞台上带着母亲的悲痛哭泣时,深刻感受到在座的男人们内心的颤抖,眼睛的湿润和罪恶感的沦陷。从打斗伊始鲁斯塔姆抓住儿子的动作里我便明白,大多数年轻、愤怒的乡下佬们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置身于苏赫拉布,而非强壮、专横的鲁斯塔姆的位置,直觉告诉我,他们其实在为自己的死流泪。不过为了让他们能够为自己而哭,首先需要他们的红头发母亲在舞台上毫不遮掩地哭泣。
我也目睹,在经历所有这些深刻的痛楚时,相当一部分崇拜者的眼睛盯在我的嘴唇、脖子、乳房、双腿,当然还有我的红色头发上,哲学的痛苦与性的欲望正如古老神话中那样彼此交织。看到自己成功地通过每一次转动脖颈,每一个全身跃动的步伐和每一个眼神,既向观众们的理智和情感,又向他们年轻的肉体呐喊,这样的时刻是美妙的,但我不能常常经历这样的时刻。有时,一个年轻男子大声哭泣传染了其他人。彼时,一人鼓起掌来,我的声音含糊不清,双方争执起来。有几次我看到帐篷里人群的疯狂,放声号哭者与暗自涕零者,鼓掌者与咒骂者,起身叫喊者与默默端坐观看者相互攻击。大多时候我喜欢并渴望这种兴奋和激情,但又惧怕群体的暴力。
不久,我找到另一个剧目,可以与塔赫米娜哭泣的一幕相媲美。先知易卜拉欣,为向真主证明自己的忠诚准备割儿子喉咙时,我既扮演了在远处默默哭泣的女人,又扮演了手拿玩具羊而来的天使。不过这个故事里没有女人的位置,我没能感染观众。之后,我重新改写了俄狄浦斯的母亲伊俄卡斯忒的话用作独白……儿子误杀父亲的故事不会激发太多热情,但作为一种观念而引发关注。或许,如此足矣。倘若我从未讲述后来儿子与红发母亲同床共枕就好了。今天我可以说,这带来了厄运。图尔加伊警告过我。然而,不管是他,还是彩排中问“大姐,这是什么呀?”的送茶人,抑或暗讽“我不喜欢这个”的主管优素福,我都充耳不闻。
1986 年在居杜尔镇,红头发的我扮演了俄狄浦斯的母亲伊俄卡斯忒,独白中讲述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儿子上床,我发自肺腑地哭泣。**天,我们接到恐吓,第二天半夜,剧场帐篷烧了起来,我们立刻赶到那里好不容易把火扑灭。一个月后,在萨姆松海边的贫民区附近搭的帐篷,就在我演绎俄狄浦斯母亲的独白后第二天早上,便遭遇了孩子们雨点般的石子攻击。在埃尔祖鲁姆,慑于愤怒的民族主义青年们对“希腊剧”的指责和威胁,我没能踏出旅馆半步,帐篷则有勇敢正直的警察们保护。我们正思忖,或许乡下人对直白的艺术还没做好准备时,在安卡拉的进步爱国者协会里散发着咖啡和拉克酒味的小舞台上,我们的剧上演还不过三次,便以“违背人民羞涩和质朴的情感”为由被叫停。在我们的国家男人们彼此*常说“操你妈”这样的脏话,检察官的判决不可谓不合理。
二十五岁左右,我还爱着我儿子的爷爷阿肯时,跟他探讨过这些话题。我的情人半诧异、半难为情地回忆并笑着对我重复男人们在初中、高中、军队里学到的我从不知晓的脏话,说声“恶心!”,继而展开“女人受压迫”的大话题,说到达工人阶级的天堂,所有这些肮脏就都会结束。我应该耐心,为革命支持男人们。不过,千万不要以为我会进入土耳其左派有关男女不平等的话题。我结尾的独白不仅仅是愤怒,同时也应当是诗意的和优雅的。我希望我儿子的书里也能有这样一种气质,人们在书中也能感受到在舞台上看我表演时的这种情感。是我建议我的恩维尔写一本书,把我们的经历编成故事,从他的父亲、爷爷开始讲起。
事实上,为了不让我的恩维尔丧失掉内心的善良和人性,不学习男人的丑恶,我想过小学阶段不送他去学校,自己在家教育。图尔加伊对我的这些幻想不屑一顾。我们的儿子开始在巴克尔柯伊上小学后,我和图尔加伊就放弃了戏剧,在迅速普及的译制片中做起配音。那些年我们去恩格然的理由是瑟勒· 西亚赫奥卢。即使左翼的、社会主义的热情褪去,我们仍旧跟老朋友见面。很多年后,他让我们在恩格然再次见到了马哈茂德师傅。
我们的儿子恩维尔喜欢听挖井人马哈茂德师傅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拜访他,他家后院有一口非常漂亮的井。马哈茂德师傅靠着在**口井里找到水后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建设中挖井发迹,他早年间买的地皮迅速涨价,因此过得很宽裕。恩格然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带着一个孩子的漂亮寡妇,她的丈夫去了德国再没回来。马哈茂德师傅接受了这个孩子,作为父亲尽职尽责。恩维尔和这个孩子——名叫萨利赫——成了好朋友。我费尽心思想让萨利赫喜欢上戏剧,却没能成功。不过我的年轻剧团成员大多都是我从恩维尔的朋友,恩格然的青少年中挑选的。因为恩维尔,我得以时常踏足恩格然。戏剧的热情是可以传染的。这些孩子大多在马哈茂德师傅家里出入。马哈茂德师傅在散发着金银花气味的自家院子里也挖了一口井。为避免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掉下去,他在铁制井盖上加了挂锁。但我还是会走到二层小楼的阳台,看着后花园对孩子们喊道:“别靠近井!”因为古老神话和传说中的事情*终会在你们身上应验。你读得越多,对那些传说越是笃信,它就越是灵验。事实上,因为你听到的故事会在你身上应验,所以才称之为传说。
是我带头把马哈茂德师傅从井里弄了上来。前一晚,我的高中生情人在喝了一杯库吕普拉克酒,笨拙地跟我做爱让我怀孕后(我们俩谁都万万没想到会这样)向我倾诉了一切(用他的话说)。说他的师傅十分为难自己,他想回家,回到母亲身边,他不相信井里能出水,他留在恩格然不是为了打井,而是为了我。
第二天中午,在车站广场看到他手里提着小行李箱、惊慌地跑向火车时,我脑子乱极了。来帐篷看我演出的一些男人不仅仅是爱上我(短暂的一段时间),更被极端的嫉妒迷了心窍。
我哀叹,很可能再也见不到杰姆了。他很少对我提到他的父亲,或许打那天起他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我们也将坐下一班火车离开,但我不明白杰姆为何突然像罪犯般仓皇地逃离恩格然。车站的人群中有手里提着篮子前来赶集的农民和孩子。之前一天的晚上,图尔加伊在学徒阿里的帮助下找到马哈茂德师傅并把他带来看戏。马哈茂德师傅来到帐篷静静地观看演出,彬彬有礼。我们的人也知道阿里不再是学徒,雇主也停了工钱。我们感到奇怪,派图尔加伊去了上面的平地,火车也错过了。然后,就像古老神话中讲的,我们一起去了井边,向下看,之后被我们放下井的阿里把半昏厥的马哈茂德师傅弄了上来。
他们把师傅送进医院。后来听说折断的锁骨还没完全愈合,马哈茂德师傅又开始挖起井来,至于他找谁当徒弟,谁资助了他,这些细节不得而知,因为我们的剧团也离开了恩格然。我想要忘记在那里跟一个高中生在戏剧的意犹未尽中发生了一夜情,想要忘记其实我爱的是他的父亲,但那份爱也已经冷却。还不到三十五岁,我就了解了男人的骄傲、脆弱和他们血液里的个人主义。我知道他们会杀死自己的父亲,也会杀死自己的儿子。不论父亲杀死儿子,还是儿子杀死父亲,对于男人来说是成就英雄,而留给我的只有哭泣。或许我应该忘掉自己知道的这些,去别的地方。
[ 1 ] 《玛斯纳维》: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哲理训言长篇叙事诗集。
[ 2 ] 《凯莱姆与阿斯勒》:著名的土耳其民间爱情传说。
相关资料
“一部非凡的作品……它几乎是用痛苦的力量深度剖析父子关系……结尾部分的转折,让读者感觉仿佛自己刚刚从深井中上来,骤然进入令人目眩的光线。”
——《卫报》(The Guardian)
“我们可以把《红发女人》读作有关当代土耳其的寓言:伤痛和渴望,让人们选出了一位专制的领导者,而这一过程又带来许多沉重的危险。”——《卫报》(The Guardian)
“这本书充满了悲悯和地方色彩,它描绘了一个男孩走向男人的历程,也记录了土耳其如何走向不可逆转的转变。重要的是,这本书激荡着思想。帕慕克强调,我们固然应该不断质问过去的记忆,但并能否定或埋葬它。历史——个人的、想象的、真实的——呼唤着我们去回忆、去更好地思考……多元复杂的记忆力量在这本书中吟唱。”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它的结尾让你想立即从头翻开这部书再看一遍。”
——《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红发女人》比帕慕克*著名的作品都更短一些,并且有意写得更为简洁清晰——小说的叙述者知道自己并非作家,而只是一个建筑承包商。以往的复调叙事被一种强有力的、迷人的清晰所取代……弑父和杀子的主题回响在意外的或不经意的谋杀情节之上:它们探索着那些缺失的代际关系——这是悲剧的,但也是必然的。世代之间的变化,巧妙地呈现在伊斯坦布尔本身由现代化带来的、往往是恶劣的变化中。”
——《旁观者》(The Spectator)
“他是卓越的故事编织者,能够敏锐地捕捉社会变迁对个体心理的影响,并能够以克制优雅的文风包纳表层之下不可克制的激情。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屠格涅夫,这位19世纪俄罗斯的肖像画家……引人深思、充满诱惑并且完美地节制。”
——《华尔街日报·欧洲版》(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帕慕克以大师手笔对比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寓言的力量和现实的不可抗拒……像以往一样,帕慕克将沉重的题材处理得十分轻盈,而结局是如此令人迷惑和美丽。”
——《书单》(Booklist)
“帕慕克巧妙地将传说故事和历史时期编织在一起,表现出标签式的互文性和跨时代性……尽管包含着父子冲突,但《红发女人》更多的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它一方面宣示了这些人物弑父般地抛弃传统、进入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另一方面,随着家庭暴力的展示,它将维持父权秩序的国家暴力隐藏起来。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在精心的组织下,它让我们深思,这些不同的观念如何共存。”
——《洛杉矶书评》(The LA Review of Books)
作者简介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欧洲杰出的小说家。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文。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60多种语言出版。
-

莫言的奇奇怪怪故事集
¥19.0¥59.9 -

悉达多
¥13.0¥28.0 -

死魂灵
¥14.0¥48.0 -

失去一切的人
¥16.6¥52.0 -

本森小姐的甲虫
¥15.9¥55.0 -

2025读书月阅读盲盒——我独钟意命运角落的人
¥42.3¥168.0 -

罗生门
¥15.9¥36.0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12.9¥39.8 -

1984-插图珍藏版
¥9.9¥29.8 -

鼠疫
¥12.6¥38.8 -

2025读书月阅读盲盒——经常作案的朋友都知道
¥42.3¥168.0 -

烟与镜
¥15.4¥48.0 -

重生
¥12.9¥39.8 -

月亮与六便士
¥10.9¥38.0 -

我是猫
¥13.0¥46.0 -

面纱
¥16.9¥49.8 -

未来的最后一年
¥16.9¥49.8 -

山海经
¥18.0¥68.0 -

我这一辈子
¥12.4¥38.0 -

倒悬的地平线
¥13.6¥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