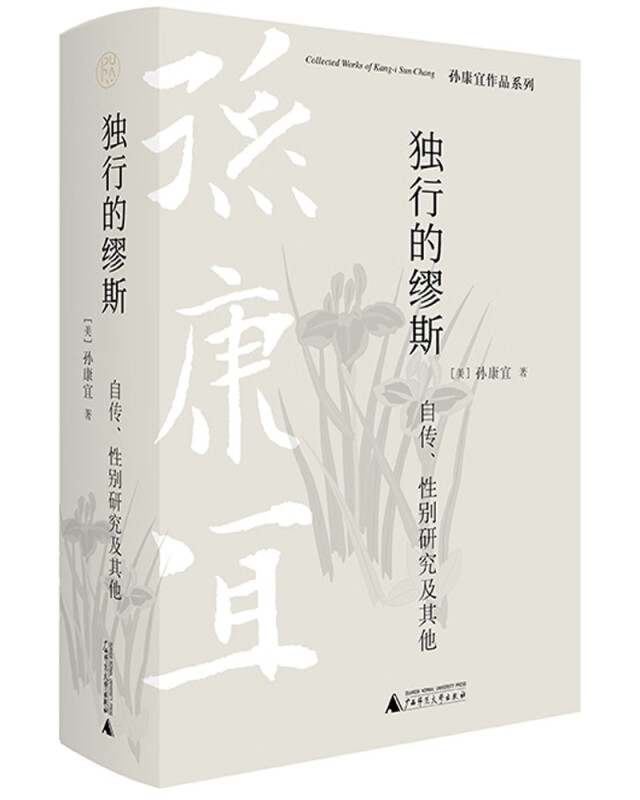
孙康宜作品系列独行的缪斯:自传、性别研究及其他

- ISBN:9787559847966
- 装帧:一般轻型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704
- 出版时间:2022-08-01
- 条形码:9787559847966 ; 978-7-5598-4796-6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大众本书卖点 孙康宜先生多年来一直关照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擅长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阐释中国传统诗词别树一格,可读性极强。该书是一本自传与性别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合集,作者详细追述了求学、治学经历,涵盖了学术文章、随笔等作品。 编辑推荐 耶鲁大学献给孙康宜教授的荣休致敬辞: 孙康宜教授,台湾东海大学文学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自1982年起任教于本校。孙教授您是中国古代文学专家,精研诗学,并于比较诗学、文学批评、性别研究、文化理论、美学等领域创获丰硕。您勤于著述,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8 部英文专著(含编辑)、30部中文著作,以及上百篇学术论文。您早年的英文专著《词与文类研究》《六朝诗研究》《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使您晋升为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权威之一,也为您赢得世界性的赞誉。令人欣羡的是,这些为人称道的起家之作仅是您成果累累的学术之旅的开端。 除了个人的英文专著及大量的中文著述外,您还编纂了多种对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论集:您与魏爱莲(Ellen Widmer)教授合编《明清女作家研究集》,让我们得以认识众多此前明清默默无闻的女诗人的作品。您与苏源熙(Haun Saussy)教授合作,出版《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辑译了自汉朝至20世纪130多位女诗人的代表作。您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合力编纂了在中国文学研究场域中堪称别树一帜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这是一部涵盖3000年、明白易晓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学者专家获益良多,一般读者也喜得入门津梁。这林林总总的著述,为学人、读者打开了进入中国文学世界的大门,惠人良多。 在此向您致敬之际,还要特别提到您艰难的人生路途,以及您的克难、超越精神。您在《走出白色恐怖》一书中忆述,在时局动荡之时,令尊携家口自北京迁居台湾,四载以后,因白色恐怖遭国民政府逮捕,自此身陷囹圄,长达10年。令尊入狱时您才6岁,您俩再见到面时您已16岁。与此同时,您的祖父留在中国大陆,历经亲人离散之苦。您熬过了这些磨难,*后来到美国,开始了另一段漫长的、曲折的人生之旅。您先是取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及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终于本国*优秀的学府之一获得博士学位。 您在本校长期任教,并在行政工作上贡献良多,如您曾担任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研究所主任。您在教学上成就杰出,曾获颁 DeVane 教学研究奖章。众所周知,此一由全美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耶鲁分会所颁授的教研奖项乃本校至高荣誉之一。 在此,为您以中文或英文著述,在文学、学术上所做的重大贡献;为您作为学者及教授为耶鲁大学做出的竭诚奉献;也为您感人励志的人生经历——从一个备尝艰苦的小女孩,浴火重生而终成首屈一指的学者、教授,以及在本校社群中深受爱戴的一员——“耶鲁”向您致上*挚诚的“谢谢您”! ——耶鲁大学(严志雄 译)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自传与性别研究及其他的合集。自传部分,主要收录有《张我军、张光直与我们家》《虎口余生记》等篇章,除了自述家世和幼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外,还详细追述了求学、治学经历。性别研究及其他部分,主要包括《中国文化里的“情”观》《道在何处》《在爱字交会》《何谓男女双性》等篇章。在对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中,孙康宜惊喜地发现了男女两性间的互补与合作的独特文化现象,纠正了西方性别理论一味强调“差异观”的偏颇。
目录
辑一 走出白色恐怖 / 001
序言 从吞恨到感恩
——见证白色恐怖 / 003
作者自序 / 014
**章 张我军、张光直和我们家 / 018
第二章 “二二八”的联想 / 028
第三章 6 岁 / 033
第四章 雪中送炭恩难忘 / 042
第五章 探监途中 / 049
第六章 父亲的故事 / 054
第七章 母亲的固守 / 058
第八章 出狱 / 063
第九章 骨灰的救赎 / 069
第十章 在语言的夹缝中 / 078
…………
辑二 性别研究及其他 / 205
中国文化里的“情”观 / 207
关于女性的新阐释 / 213
20 世纪90 年代的美国女权主义 / 225
《花花公子》的常春藤盟校风波 / 235
何谓男性“自我认同”的危机? / 238
我看江青自传 / 244
周蕾论中国现代性 / 253
“末恋”的风行意义 / 256
贝多芬的“永远的爱人” / 262
今夏,你看过“冬天”没? / 265
《霸王别姬》里的情痴 / 270
爱在何处? / 274
…………
辑三 访谈录 / 617
《南方周末》朱又可采访 / 619
附 录 / 637
《孙康宜作品系列》校读后记 / 639
节选
性别与经典论 —从明清文人的女性观说起 不久前,我曾在台湾讨论过如何建立文学经典的问题,*后终于选出了30部经典作品。在一篇题为《看!以台湾为中心的文学经典》的文章里,诗人陈义芝曾说,经典的建立乃是人文价值的建立。同时,他讨论到如何突显台湾文学的主体性问题。至于选择经典的方面,他也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7本新诗经典的作者全是男诗人,蓉子、林泠难道不能相与颉颃?”这就牵涉到评价经典的准则问题,也把我们引到了性别问题来了。而这两个息息相关的题目也正是目前欧美世界文学批评的研究重点。 性别与经典的问题始于人们对于多元文化的关注。所谓“多元”就是从不同的性别种族和族群来重新评价各种文化的表现和传统。多元文化的新趋势很大程度是受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影响,以及现代社会日趋复杂而多元的自然反应。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有关文学经典的重新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陈义芝所说的“不可能毫无争议的问题”。在当今文学研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经典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有改写的必要,因为所谓的“传统经典”并不能代表人们的“普遍经验”(universal experience)。这样的挑战的声音自然引发出一连串有趣的问题,例如:怎样的作品才能成为文学经典之作?经典之作的可读性如何?评定文学经典的美学标准为何?经典之作和次等作品的分别何在?一部经典之作应当涵盖人类的普遍经验,还是代表特殊人群的文化意识? 许多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女性主义批评家先提出来的。她们多数认为经典的形成完全是出于权力的运作;是独霸的夫权制提高了男性作者的地位,贬低了女性作家的成就。但另外有一些批评家却认为经典的形成与权力或政治无关。总之,这一方面的争论不少,也无形间促成了大家对经典的兴趣。 自从研究明清文学以来,我一直对性别与经典论的概念感兴趣。我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300年间,就有2000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而当时的文人不但没对这些才女产生敌意,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是女性出版的主要赞助者,而且竭尽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经典化。明清文人这种维护才女的现象实在很特殊,至少与19世纪的英国很不相同。当时英国产生了许多女性小说家,但男性批评家基本上对她们抱着敌视或嘲讽的态度。是什么原因使得明清文人拥有如此特殊的“女性观”?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今天把性别与经典论放在明清文人文化的上下文中来进行讨论。 这里所谓的“文人文化”是相对于当时的实用文化而言的。在这个文人文化中,其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文人普遍地向往女性文本。在某一程度上,这个现象也是当时文人厌倦了八股文及其他实用价值的具体反映。他们大量整理女性文本,为女诗人出版各种不同的选集,使得妇女诗词顿时成为热门读物。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女性研究”其实是明清文人对理想女性的向往的一种产物。他们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边缘处境,一方面也对被历史埋没的才女赋予极大的同情。所以,当时许多文人不惜倾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诗人的作品。从政治上的失意转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了当时的风气。例如,明末清初一本女性诗集—《红蕉集》的编者邹漪就说:“仆本恨人,癖耽奁制,薄游吴越,加意网罗。”所谓“恨人”就是怀才不遇、内心感到不平的文人。他们从收集女诗人的作品中得到安慰及成就感,以至于其爱才心态无形中成了一种“癖”(也就是英文所谓的obsession或addiction)。所以,邹漪说“癖耽奁制”,意思就是说,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女性的作品中。著名诗人王士祯的哥哥王士禄也在他的女性文学选集《然脂集》中说自己“夙有彤管之嗜”,所谓“嗜”就是“癖”的意思。后来,清代的文人也继承了这个晚明的文人传统,例如以提拔女诗人贺双卿著名的史震曾在他的《西青散记》一书中,屡次说自己是个“感慨人”,其实就是“恨人”的意思。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情趣的追求上,完全忽视了功利的考虑。他说:“人生须有两副痛泪,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这些文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才女或佳人,乃是因为他们在才女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翻版。他们同样是一群崇尚美学和爱才如命的边缘人,他们中间有很深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也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所谓“边缘”当然是指相对于政治权力的主流而言的。虽然从政治的权力而言,这些明清文人自认为边缘人或“多余”之人,但从文学艺术的方面来看,他们却常常是一些走在时代前端并向传统经典挑战的主要人物。有趣的是,正是这些边缘文人把一向处于边缘地位的明清女诗人提高到了经典的地位。有趣的是,目前不少西方文学评论家也认为,把边缘引向主流的*有效方法就是不断地强调边缘文学的重要性,不断地扩大文学的视野,而渐渐把边缘与主流合而为一。 明清文人是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女诗人的地位的呢?他们采用的就是这种把边缘和主流逐渐混合为一的策略。首先,他们强调女诗人传统的悠久性及重要性。为了证明这个大前提,他们从*具权威性的经典选集《诗经》说起,他们强调《诗经》里有很大部分的诗歌是女性的作品。例如,邹漪在他的《红蕉集》的序言里就说:“《三百》删自圣手,《二南》诸篇,什七出后妃嫔御、思妇游女。”大意是说,《诗经国风》里的《周南》和《召南》,有70%的诗歌是女性的作品。虽然这样的论点并无实际的根据,而且似乎有把虚构和史实随便鱼目混珠之嫌,但既然这个新的经典论很管用,此后几乎所有文人都沿用这个说法。而且既然《诗经》是孔子编订的经典选集,明清文人也就很自然地把他们整理妇女诗词选集的工作视为重建文学经典的活动了。就如西方文学批评家温德尔哈里斯(Wendell Harris)所说,“所有文本的解释都靠约定俗成的阐释策略来维持”,明清文人所用来提高女性文学的方法就是这种凡事追溯到《诗经》传统的“约定俗成”的策略。 另一方面,明清文人也把女诗人的作品放在《离骚》传统的上下文来看待。例如,1618年蘧觉生编订的女诗人选集《女骚》就反映了这种态度。在《女骚》的一篇序言里,著名学者赵时用强调文学里的“变”的作用;因为自从《诗经》的风雅篇以来,诗歌的风格与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无疑是在说明,文学经典的范围是不断在拓宽的。言下之意就是,女性作品也应当作为新的文学经典的考虑之一。 这样的策略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六朝文学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里所提倡的经典论。在把《离骚》提升为新的文学典范的过程中,刘勰所用的方法正是强调“变”的重要性。所以他说,他撰写《文心雕龙》的主要目的不仅在呈现文之心如何的“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而且还要说明它是如何“变乎骚”的。他所谓的“变”就是创立新的文学准则的意思。在《文心雕龙》里,《离骚》首度被视为纯文学的一种典范,而刘勰特别强调的正是屈原的“变”的文体,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很像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他的《西方正典》()一书中所用来形容莎士比亚的陌生性(strangeness)。 我们可以说,明清文人在提拔女诗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实在不下于刘勰在《离骚》的经典化上所付出的苦心。有不少文人决心要把收集和品评女性作品作为毕生的事业。为此他们想出了许多把女性诗歌经典化的有效策略。其中一个策略就是以上所说的凡事追溯到《诗经》与《离骚》等古代经典的策略。他们不但要显示出一个古老的传统是如何在现代诗人身上(不论是男是女)运作出那般巨大的影响力的,而且也要证明现代诗人是如何创新,因而改变了这个传统,拓宽了文学的视野的。这样的策略其实也是历代文人一向熟悉的文学经典策略,也是比较传统的方式。 但另外一个比较富有创新的策略,确是明清文人的一大发明:强调女性是*富有诗人气质的性别,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本身具有一种男性文人日渐缺乏的“清”的特质。明末诗人钟惺就在他的《名媛诗归》的“序”里把女性的本质和“清”的美学联系在: 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唯清故也。清则慧……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 后来这种把“清”视为女性的属性的言论慢慢地成为明清文学评论中的主流了。“清”被说成是一种天地的灵秀之气,也是女性诗歌优越的主要原因。所以,明末著名学者葛征奇说: 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 编撰《古今女史》(1628年刊本)的赵世杰也说: 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 此外,《红蕉集》(清初刊本)的编者邹漪也曾重复地说: 乾坤之气不钟男子,而钟妇人。 后清朝雍正年间致力于收集女性作品的范端昂更以“高山则可仰,景行则可行”的态度来看待女性作品里的“清”的素质: 夫诗抒写性情者也,必须清丽之笔,而清莫清于香奁,丽莫丽于美女……举凡天地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行,国风汉魏以来之一字一句,皆会于胸中,充然行之笔下……而余终不能忘于景之仰之者也。
作者简介
孙康宜,美国 华裔汉学家。原籍天津,1944 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往 。1968 年移居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荣休讲座教授,曾获美国人文学科多种荣誉奖金,中英文著作多种。2015 年4 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
-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26.6¥38.0 -

世界尽头的咖啡馆
¥18.0¥45.0 -

咬文嚼字二百问
¥9.6¥32.0 -

《标点符号用法》解读
¥6.2¥15.0 -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30.3¥52.0 -

字海探源
¥23.4¥78.0 -

乡土中国
¥14.6¥26.0 -

与内心的恐惧对话:摆脱来自亲人的负能量
¥34.1¥48.0 -

你能写出好故事-写作的诀窍.大脑的奥秘.认知的陷阱
¥9.8¥32.8 -

中国人的精神
¥9.9¥29.0 -

社会学:原来这么有趣有用
¥9.1¥36.0 -

从白大褂到病号服:探索医疗中的人性落差
¥12.7¥39.8 -

焦虑心理学:不畏惧、不逃避,和压力做朋友
¥11.4¥38.0 -

理解生命
¥10.5¥32.8 -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八品)
¥22.4¥59.0 -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12.1¥36.8 -

非暴力沟通心理学 : 用非暴力沟通化解冲突
¥9.0¥36.0 -

上大演讲录(1922-1927卷)(九品)
¥14.0¥52.0 -

那时的大学
¥8.4¥28.0 -

汉字王国
¥11.5¥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