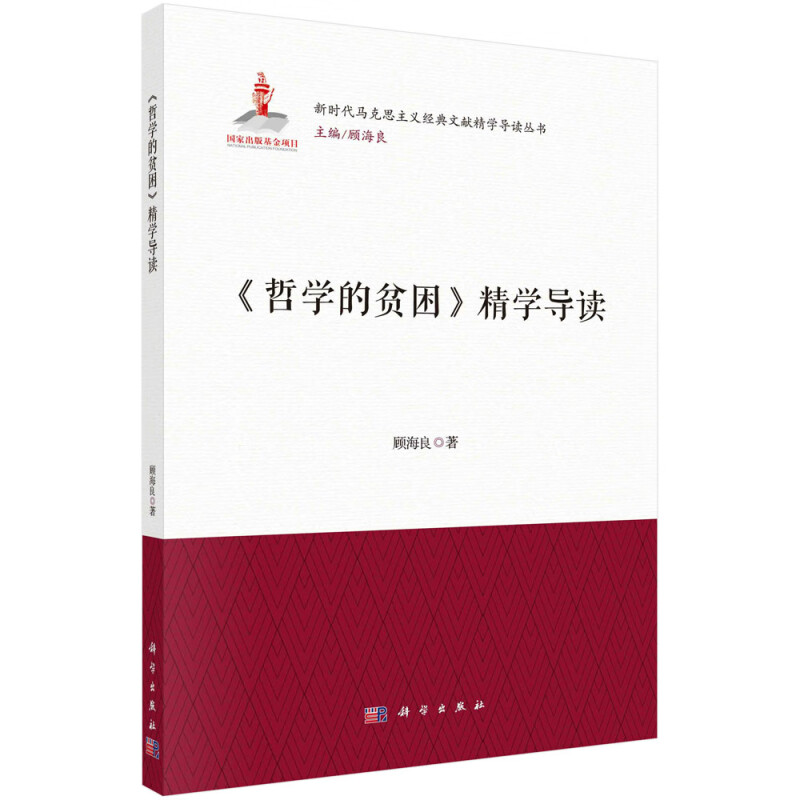- ISBN:9787030730282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206
- 出版时间:2022-10-01
- 条形码:9787030730282 ; 978-7-03-073028-2
内容简介
《哲学的贫困》是1847年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成的一部论战性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进行科学阐释的经典著作。全书在阐明《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写作动因、产生过程、历史地位、主要内容、传播状况的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批判了蒲鲁东唯心主义经济学,科学阐述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同时,本书还深刻挖掘了《哲学的贫困》这部经典著作在新时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可供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共党史党建专业的学生,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目录
**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写作动因 1
一、马克思对蒲鲁东早期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评价 2
二、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出版 10
三、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写作及其意义 15
第二章 马克思“有决定意义的论点”首次阐释 20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的历史观” 21
二、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总体评价 25
三、对现代社会制度关系本质的分析 31
四、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批判 34
五、蒲鲁东政治学说的根本谬误 37
第三章 对蒲鲁东“综合价值论”批判 40
一、对蒲鲁东综合价值论批判的基本立场 41
二、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观点的批判 44
三、对“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观点的批判 47
四、对“价值比例规律的运用”观点的批判 53
第四章 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批判 58
一、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初探索 58
二、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63
三、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评价 68
四、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判 72
五、李嘉图理论的经济思想史意义 75
第五章 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79
一、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本质规定 80
二、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性特征 85
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及其关系 88
四、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与流派 91
第六章 社会经济“进化”的历史与逻辑 97
一、蒲鲁东关于“经济进化”及其“时期”划分的谬误 98
二、关于“分工和机器”理论的批判 102
三、关于“竞争和垄断”理论的批判 107
四、对“所有制或租”理论的批判 110
第七章 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阐释 117
一、综合价值论是工资理论的“陷阱” 117
二、工人罢工、劳动阶级“同盟”与经济斗争 120
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 127
四、《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 129
第八章 马克思对蒲鲁东思想的再批判 135
一、19世纪50年代初对蒲鲁东政治思想的批判 135
二、19世纪50年代末对蒲鲁东经济思想再批判 140
三、**国际期间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 146
四、对蒲鲁东的“盖棺论定” 151
第九章 恩格斯对《哲学的贫困》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坚守 159
一、《哲学的贫困》写作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契合 160
二、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的批判分析 165
三、19世纪60年代后恩格斯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 170
四、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中的理论贡献 174
第十章 《哲学的贫困》在中国的传播和当代意义 180
一、《哲学的贫困》在中国的传播 181
二、《哲学的贫困》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当代新发展 187
三、《哲学的贫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194
四、《哲学的贫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的当代呈现 200
节选
**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写作动因 《哲学的贫困》书名的全称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而撰写的。 《哲学的贫困》出版1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哲学的贫困》出版10年后,马克思开始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哲学的贫困》出版20年后,《资本论》**卷德文**版问世。马克思自己的评价是:《哲学的贫困》包含了“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它与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起,“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 。《哲学的贫困》对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哲学的贫困》特别是其中蕴含的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无论是在科学内涵还是在科学精神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对蒲鲁东早期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评价 皮埃尔 约瑟夫 蒲鲁东(1809—1865)出生于法国边远省份的一个农民与小手工业者家庭。12岁时,就开始独立谋生,当过旅馆雇工、印刷所的排字工人。在中学有过短暂的学习经历,但初中没有毕业就被迫辍学。蒲鲁东勤奋自学,在劳动之余,阅读了他能找到的各种书籍,特别是关于神学、语言学及哲学和经济学的大量著述。1831年,蒲鲁东离开故乡,游历于法国各地,使他对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有着更多的感性认识。 19世纪40年代,法国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社会处在重要的变革时期。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尽管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小手工业生产还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中,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下濒临破产,雇佣工人数量迅速增长,破产的农民和雇佣工人都处在极度贫困和生活状况日趋恶化之中。1825年资本主义**次经济危机席卷欧洲,法国同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工人罢工运动不断兴起。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接连爆发两次工人起义,震撼了法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同时,法国小生产者的大量存在,使得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日渐活跃,在法国思想政治领域占据重要一席,对法国工人运动更是发生着重要影响。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小私有制的立场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维护小私有制的观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蒲鲁东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氛围中形成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和思想的。 1837年,蒲鲁东28岁时撰写了《普通语法论》的小册子;1840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什么是财产?》(中文也译作《什么是所有权?》);1843年,出版了名为《论人类秩序的建立》的哲学著作。在《什么是财产?》中,蒲鲁东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命题,宣扬了当时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1843年10月和11月间,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认为:“这本书用丰富的智慧和真正的科学研究阐明私有权以及这一制度所引起的后果即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这种把智慧和科学研究在一本书中结合起来的做法,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1844年,马克思居住在巴黎,同蒲鲁东开始有交往;1845年初,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同蒲鲁东还有往来。马克思一开始对蒲鲁东《什么是财产?》的某些观点也是抱有好感的。他在1844年底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曾经提到:在《什么是财产?》中,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蒲鲁东始终不同于其他国民经济学家,他不是以限于局部的方式把私有财产的这种或那种形式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而是以总括全局的方式把私有财产本身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 1865年1月15日,蒲鲁东去世。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撰文对蒲鲁东作出“盖棺论定”式的评价。在回忆起1844年间与蒲鲁东交往的情形时,马克思提到:“《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废除’了。” 在对《什么是财产?》的表达形式和思想实质评价时,马克思指出,首先,“蒲鲁东的这一著作在风格方面强健的肌肉还算占优势。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 。但同时,在这一“风格”中仍然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 。在《什么是财产?》中,蒲鲁东尽管向当时政治经济学中“*神圣的东西”提出挑战,对庸俗的资产阶级知性作出毁灭性的评论和辛辣的讽刺,也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深刻而真实的激愤和革命的真诚,但是,“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 。 其次,在思想实质上,马克思认为:“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社会主义者流传给他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在标题上就表现出思想理论上“非常错误”的地方,因为“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 。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来回答,这种批判性分析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 马克思谈到,在1844年间,他同蒲鲁东“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 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马克思这时已经在“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以实现哲学世界观的伟大变革;而蒲鲁东还在受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同黑格尔主义中的合理思想继续背道而驰。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蒲鲁东在思想上的分歧,已经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1846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时,在布鲁塞尔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希望通讯委员会能使“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信联系,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论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 。当时,活跃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德国的W.沃尔弗、J.魏德迈,英国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K.沙佩尔、H.鲍威尔、J.莫尔,英国宪章派左翼领导人G.J.哈尼,比利时的P.日果等,都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邀请积极参与通讯委员会的活动。 1846年5月5日,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蒲鲁东写信,邀请蒲
-

不良情绪应急处理包--孤独感
¥12.9¥30.0 -

快乐就是哈哈哈哈哈 插图纪念版
¥15.6¥52.0 -

不良情绪应急处理包--就是有点不开心
¥12.9¥30.0 -

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
¥15.9¥49.8 -

她们
¥15.0¥46.8 -

不良情绪应急处理包--精神内耗
¥12.9¥30.0 -

西南联大文学课
¥20.9¥58.0 -

姑妈的宝刀
¥9.0¥30.0 -

十三邀4:“这样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人”(八品)
¥35.0¥58.0 -

不良情绪应急处理包--大自然饥渴症
¥12.9¥30.0 -

两张图读懂两宋
¥23.2¥76.0 -

八仙得道传
¥12.0¥40.0 -

战争与和平(上下)
¥23.4¥78.0 -

小说家的假期
¥29.7¥52.0 -

世界尽头的咖啡馆
¥15.8¥45.0 -

事已至此先吃饭吧
¥16.5¥55.0 -

别怕!请允许一切发生
¥21.4¥49.8 -

不良情绪应急处理包--新式“文盲”
¥12.9¥30.0 -

鸟与兽的通俗生活
¥16.3¥39.8 -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19.8¥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