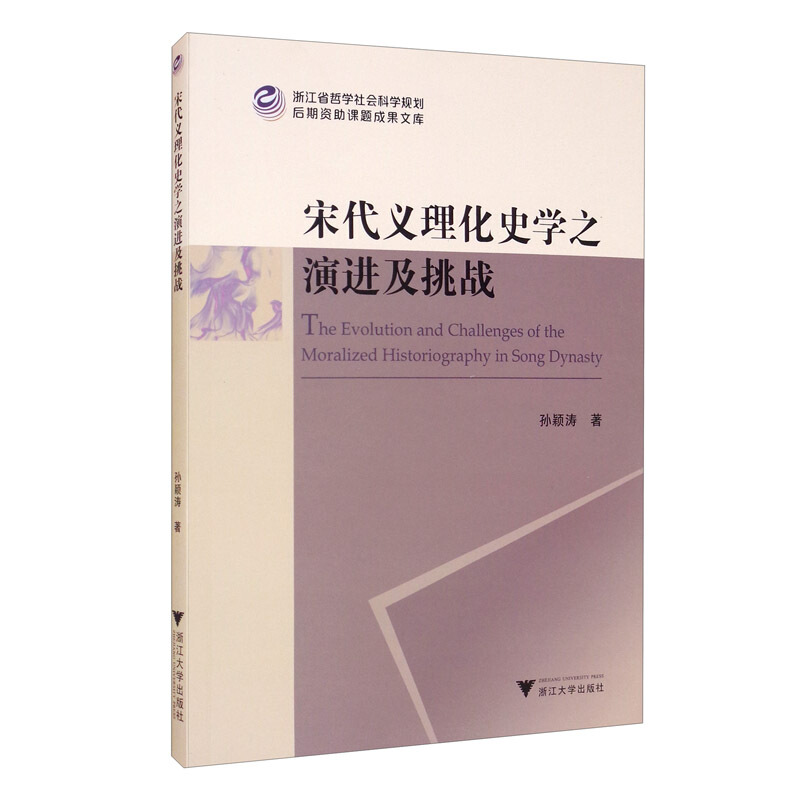- ISBN:9787308210577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24cm
- 页数:224页
- 出版时间:2021-03-01
- 条形码:9787308210577 ; 978-7-308-21057-7
内容简介
本书不局限于从大的学术传统中探究宋代义理化史学发展的动力之源, 而是更注重从宋代文献中发现其固有的时代脉络, 勾勒出其中各环节之间的承续和发展关系, 力图呈现义理化史学在宋代的主要发展轨迹。
目录
**章 《资治通鉴》:新史学典范的内在冲突
**节 《资治通鉴》:史家之史的新典范
第二节 《资治通鉴》内在价值取向的冲突
第三节 小结
第二章 《唐鉴》: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节 范祖禹:在司马光与二程之间
第二节 《唐鉴》与《通鉴》的自觉区隔
第三节 小结
第三章 《读史管见》:理学家之史的奠基之作
**节 《读史管见》与《资治通鉴》
第二节 《读史管见》的正义论说
第三节 《读史管见》的学术地位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资治通鉴纲目》:义理化史学的新典范
**节 《纲目》对《通鉴》正统观的矫正
第二节 朱熹的《春秋》观与《纲目》之编纂
第三节 小结
第五章 浙东史家群体对义理化史学的挑战
**节 吕祖谦对朱熹理学化史观的挑战
第二节 陈亮对朱熹理学化史观的挑战
第三节 叶适对朱熹理学化史观的挑战
第四节 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节选
《宋代义理化史学之演进及挑战》: 直到司马光成功编就《资治通鉴》,创造了史家之史的光辉新典范,而这一史学新典范所表现出的特质,又与义理化史学的追求存在明显的差距,理学家及其追随者于是找到了共同的主要对手和批判对象,义理化史学也随之呈现出前后相继、线索分明的清晰发展路径。 司马光在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多位著名史学家的协助下,充分吸纳了纪传体史书的优点,对传统编年体加以革新改造,创作出《左传》以后*为令人瞩目的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是书继承了实录史学的传统,直笔录事,不轻立论,不仅弃用了褒贬义法,对正统问题也置而不言:除在叙事上卓有成就以外,还聚焦于国家大政,备载谋议,大有裨益于治道,获得世人的高度赞誉,堪称史家之史的光辉典范。 然而,这一新的史学典范因主编司马光的特殊旨趣,实际上承担了儒家文化和专业史学的双重使命,表现出明显的儒门史学的特色。基于自身强烈的儒家认同,司马光将史学限定在儒学门庭之内,认为在求道明道的目标上,史学与经学并无二致。他重视经之常道适用的历史条件,认为史学解决了经之恒常普遍之道在具体时空中的适应性问题,在此基础上肯认史学在求道明道中的重要作用,高度认同史学的鉴戒价值,并以史学实践自觉承担“经之常道落实在具体历史中帝王之一心”的任务。这种儒门史学一旦落入实践层次,便不得不处理理想世界、现实世界、历史世界三个层面的问题,实际蕴含了求道、求治、求真三重价值取向。理想世界、现实世界、历史世界在史学实践中的相互牵涉和彼此限制,也必然造成儒门史学三重价值取向的内在冲突,表现为求道与求治的冲突、求道与求真的冲突。《资治通鉴》所表现出的这三重价值取向的冲突,被理学家程颐、朱熹敏感道破而加以批评,通过这些批评,程颐、朱熹和司马光之间史观的差异也充分展现出来。 求道与求治的冲突,造成在历史人物评价上司马光与程颐(也包括朱熹)的分歧。程颐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基本遵循的是信念伦理,以道德价值为依据而无视功效价值。道德和政治在客观世界中虽然必然冲突,但在程颐进行历史人物评价之时,却是两不相妨,互不干扰。而司马光在求道与求治的双重价值取向之下,无论是在选择遵循信念伦理或责任伦理之时,还是在遵循责任伦理确定愿望和结果的比例之时,都无法避免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或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在在都要于道德价值和功效价值之间权衡考量。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中求道与求治的冲突,在程颐的挑战和对照之下,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 求道与求真的冲突,引起在历史编纂上司马光与朱熹的分歧。朱熹认为,经是求道明道、融会义理的主要根据,史只是理学家以心中既存之义理评断的具体案例。史学固然可以加深对义理的认识,但较之于经学,史学在明道中的角色是很次要的。在卸下史家之史明道的主要责任之后,朱熹格外强调史家之史的真实价值和在真实性意义上史家之史的独立性,希图史家之史建立在全面反映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以更好在历史事实层面辅翼理学家的兼经之史。《资治通鉴纲目》是朱熹上法《春秋》的拟经之作,其性质为兼经之史,为理学家之史,非史家之史。朱熹不以史家自居,其书也不以存史为重,主要是为矫正史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义理上的过失。正因为以道在我,褒贬自任,所以朱熹对史家之史主要以真实性相责备,并不以明道相期许。而司马光作为专业史家,虽能坚守信史的底线,但囿于鉴戒的思想和亦儒亦史的双重身份认同,通过删削重要史实表达政治立场和道德倾向,故其书实际上未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伤害了史学的真实价值,这正反映了司马光在史学实践中求道与求真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 程颐、朱熹的史观具有很大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他们均主张读经明道,将史视为以心中既存之义理断决的具体案例;并且他们都以义理之学自负,轻视史家司马光的义理造诣,不以明道为史家之史的主要功能。因此,尽管程颐由于对《资治通鉴》的介入程度远不如朱熹高,未指出其中删削重要史实一点,但在削弱史家之史明道功能之后,程颐更注重史家之史的真实价值也属逻辑的必然。 ……
作者简介
孙颖涛,曾先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获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思想史。
-

明末农民战争史-修订版
¥18.5¥46.0 -

人类酷刑简史
¥21.1¥59.0 -

你不知道的古人生活冷知识
¥15.7¥49.0 -

中国近代史
¥13.7¥39.8 -

安史之乱
¥30.6¥68.0 -

历史的沸点-两晋十六国的二十张面孔-第二卷
¥15.4¥48.0 -

华戎交汇在敦煌
¥29.9¥58.0 -

正说明朝十六帝
¥16.9¥49.8 -

敦煌学新论(增订本)
¥41.8¥68.0 -

生命之种:从亚里士多德到达.芬奇.从鲨鱼牙齿到青蛙短裤.宝宝到底从哪里来
¥16.6¥52.0 -

中国历史常识
¥16.9¥49.8 -

希特勒死后:欧洲战场的最后十天
¥23.0¥68.8 -

清朝穿越指南
¥15.4¥45.0 -

1956:觉醒的世界
¥19.6¥58.0 -

法国大革命
¥20.0¥56.0 -

无泪而泣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别工作队
¥24.1¥68.0 -

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科技简史
¥7.8¥25.0 -

中国历史:大明王朝三百年
¥21.9¥69.8 -

1688年的全球史
¥28.3¥78.0 -

愤激年代:漫画二战史(1931—1945)
¥19.6¥58.0